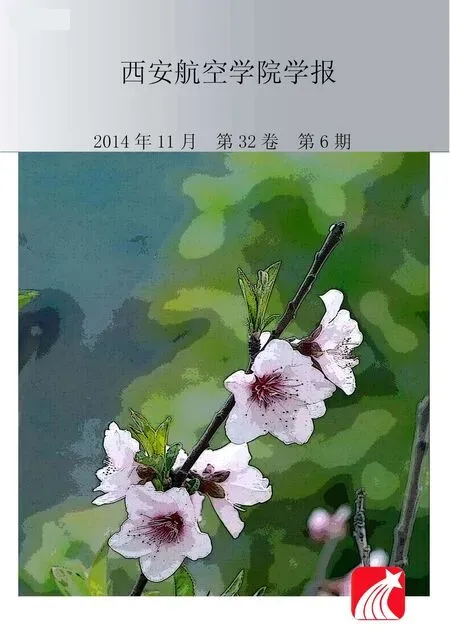以语言和数字的关系为例重新解读萨丕尔-沃尔夫假说
胡剑青
(西北大学 外国语学院,陕西 西安710127)
以语言和数字的关系为例重新解读萨丕尔-沃尔夫假说
胡剑青
(西北大学 外国语学院,陕西 西安710127)
语言和思维的关系是个古老而迷人的话题,从古至今,讨论主要集中在语言和思维是否可分,如果可分,是谁决定谁。在众多观点中,针对萨匹尔-沃尔夫假说的争议颇多。以往对萨丕尔沃尔夫假说的讨论并不少,但如同对语言和思维关系的探讨一样,绝大部分研究显得实证不足。基于前人的研究,拟从具体实例研究,即英汉双语对数字概念表达方面的影响为例,重新解读该假说。
萨丕尔-沃尔夫假说;思维;数字
一、萨丕尔-沃尔夫假说的发展史
单纯从命名上看,“萨丕尔-沃尔夫假说”很容易被人误解成为该假说独属于萨丕尔和沃尔夫两个人。其实,“萨丕尔-沃尔夫假说”是基于大量前人理论研究的基础上,代表着一群学者对语言和思维的关系的相似观点。甚至萨丕尔和沃尔夫两个人从未正式提出过该假说,更未对该假说命名,而是由美国语言学家J·B·Carrol第一次把二人的观点综合起来,称为“萨丕尔-沃尔夫假说”。
自亚里士多德起,思维本体论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在西方思想史上占据主导地位。正如他提出的“口语是心灵经验的符号”,作为一种被动的、简单的语言反映论直至浪漫主义时期,才开始遭遇严峻的挑战[1]。第一个用详实的语料,全面、系统地论证语言和思维关系的人是德国语言学家洪堡特。他认为思维与语言的关系是互动的,“语言从精神出发,再反作用于精神”,每一个语言体系的不同都会形成不同的对于世界的看法[2]。洪堡特的观点深刻影响了美国描写主义语言学的奠基人Franz Boas。正是在Franz Boas的指导下,他的学生Edward Sapir成为出色的北美印第安语专家,对语言现象给予了深切的人文关注。后来,在Sapir的指导下,Benjamin Lee Whorf开始学习霍皮语(Hopi),进而提出了著名的“语言相对论原则”(the principle of linguistic relativity),而这一理论也成为日后形成的“萨丕尔-沃尔夫假说”的核心部分。从最初零散的观点到最后该假说的形成,萨丕尔和沃尔夫为人类研究语言和思维的关系做出了突出的贡献。尽管二人都未曾提出过该假说,但以二人姓名来命名该假说是当之无愧的。
二、对萨丕尔-沃尔夫假说的误读及重新解读
(一)对于该假说的误读
对于“萨丕尔-沃尔夫假说”的解读在学界已形成固定模式并被广泛接受,例如:“以上思想可归结为两点。第一,语言不同的人,有相应的不同的思维。第二,语言决定思维;思维不可能脱离语言而存在。前者被称为‘语言相对论’,后者被称为‘语言决定论’”[3]。从上例中可以总结出学界对于该假说形成的固定模式,即强势说=语言决定论;弱势说=语言相对论。然而,根据沃尔夫的语言相对论原则可知,语言相对论和语言决定论都是该假说的组成部分,并不能简单将该假说一分为二,分成弱势与强势两个部分。
(二)假说的“强势”与“弱势”部分
由此可见,“萨丕尔-沃尔夫”假说的强势部分和弱势部分的划分并非等同于“语言决定论”和“语言相对论”。“语言决定论主要关注的是语言和思维的关系,认为二者是一种具有方向性的因果关系,其中语言是因,思维是果。但就语言在何种程度上决定影响思维,不同人有不同见解。”[4]有人认为语言和思维可以等同,不借助语言的思维是不存在的,这是一种非常强势的语言决定论;也有人认为,语言只是在某种程度上决定思维,他们更倾向于用‘影响’一词替代决定,这可以理解成为弱势的语言决定论[5]。语言相对论旨在强调语言间的差异,强势解读认为每种语言都有自己独特的编码系统,和其他语言的系统没有相似之处;弱势解读认为语言间虽然存在一定的相似性,但在本质上还是相异的。
由此可见,若简单将语言决定论划归为假说的强势部分,将语言相对论划归为该假说的弱势部分,是对该假说的误读。因为无论语言相对论还是语言决定论各自都由两个部分组成,而非对立形成的两个独立部分。
三、英汉语言差异对儿童数字概念表达能力的影响
根据萨丕尔-沃尔夫假说语言决定论弱势部分的观点,语言是在某种程度上影响着人类的思维,而非语言与思维完全等同。这一观点,在以不同语言为母语的儿童习得数字概念时得到了充分的验证。
以汉语和英语为例,许多研究表明,汉语和英语的数字在发音和形态上的差异对儿童数字的概念化及运算能力有着很大的影响[6]。汉语的数字命名更为规范,以1到100以内的数字为例,从1到10为止,汉语和英语较为相似,都是用十个不相同的语音符号来命名这十个数字,然而,从11开始到99为止,汉语对数字命名的规则性优点便开始凸显:从11开始到99为止,汉语对数字命名有一个固定模式,即单位名称和“十个”单位构成,也就是两位数构成模式中无论是十位还是个位的语音符号都来自1到10这十个数字,此处的“十个”单位在表示两位数的命名时已经被固定成为一个代表“十个”这一数字概念的单位,相当于英语中的词缀。在培养儿童形成两位数概念的时候,只需更换“十个”单位之前的单位名称即可表达从11到99之间任何的两位数字。例如,32和55的汉语发音是“三十二”和“五十五”,此时,十位数字的不同仅仅只需更换“十”之前的单位名称即可,而“十”这个“词缀”则被固定下来,个位数则来源于1到10这十个数字,简单易懂。
相比之下,英语的数字命名体系则较为复杂[7]。从11和12开始的两位数的命名与1和2的命名毫无关系。此时,儿童若要在大脑中形成11与12所对应的数字概念则必须发挥记忆力的功能。从13到19之间,英语为这些数字的命名提供了一个词缀“teen”。看似与汉语中表示“十个”单位的“十”功能相似,实际上则为之后的数字习得留下隐患,因为从20开始到99为止,一个新的词缀“ty”取代了“teen”用来在两位数中表示“十个”的意义功能。这无疑增加了儿童习得数字概念的难度。因为在初学阶段,儿童很难区分“teen”和“ty”,很容易出现词缀搭配的混淆。
综上所述,汉语对1到99的数字命名看似分为两个系统,即1到10和11到99,但实际上是一个系统,因为两个系统中无论在概念还是语音上都紧密相连。然而,英语中则较为复杂,分为四个系统:1到10,11和12,13到19,20到99。不仅在发音上不同,拼写上也不相同。以14和40为例,汉语的读音是“十四”和“四十”,英语则是“fourteen”和“forty”,读音不同,拼写不同。所以中国学生比以英语为母语的学生更快地学会数字概念表达,这对于提高运算能力也有很大帮助。
四、结语
本文通过对萨丕尔-沃尔夫假说产生的历史背景的简述,讨论学界对该假说的误读,并简述了对该假说的重新解读,即该假说语言决定论和语言相对论各由两个方面组成。最后,通过英汉两种语言在数字命名上的差异对于儿童数字概念习得的影响,证明了语言对思维的深刻影响,以实例证明了该假说语言决定论的弱势部分。
[1] 亚里士多德.范畴篇 解释篇[M].方书春,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1:12-16.
[2] 洪堡特.论人类语言结构的差异及其对人类精神发展的影响[M].姚小平,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56-66.
[3] 高一虹.语言文化差异的认识与超越[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0:56-58.
[4] 陈光明.萨丕尔-沃尔夫假说:误读与重读[J].西安外国语大学学报,2011(4):21-25.
[5] 梁海英.从语言与思维的角度再论萨丕尔沃尔夫假说[J].甘肃联合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2):33-37.
[6] 刘文宇,王慧莉,唐一源.语言与数字关系研究进展[J].辽宁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2):52-54.
[7] 罗之慧.汉英语言思维方式对比举略[J].咸宁学院学报,2010(4):63-66.
[责任编辑、校对:梁春燕]
Reinterpretation of Sapir-Whorf Hypothesis with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Language and Figure as the Example
HU Jian-qing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Northwest University, Xi'an 710127, China)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language and thinking has been an ancient but fascinating topic discussed by numerous philosophers, psychologists, and linguists. The focus of their discussion is whether language and thinking can be separated, and if yes, which one plays the dominant role. Among the variety of views, it is disputable over Sapir-Whorf Hypothesis. Literature reveals that there were a good many discussions on Sapir-Whorf Hypothesis in the past, but which lacked solid evidence, just like those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language and thinking. Based on the previous research, the article tries to reinterpret the hypothesis from concrete examplesthe impact on figure expression by both English and Chinese.
Sapir-Whorf Hypothesis; thinking; figure
2014-05-23
胡剑青(1989-),男,辽宁阜新人,硕士,主要从事外国语言学与应用语言学研究。
H08
A
1008-9233(2014)06-0055-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