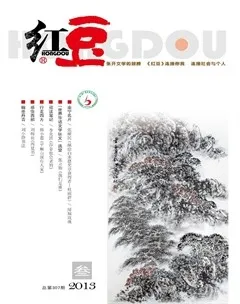器物里的光阴
竹 椅
有些年头了,那两把竹椅,在老家堂前一小片斜照里泛着油红的光,静默安然,看起来就像是一对在尘世里过了半生的夫妻——不,是母女。
是的,那是一对母女椅,在我六岁的时候,它们经由一个扳匠的手进入人间,来到我和母亲的生活。我的母亲是一个乡村教师。皖南多山,大大小小的村子散落在山的褶缝和凹处,仿佛丛林里任意生长的蘑菇。一条山路盘山绕水串连着村子,除天空旋飞的山鹰,没有人能看到路的尽头。母亲就在这样的村子里教着书,从十八岁到五十八岁,用四十年的人生脚步丈量着这条路的曲折与长度。
我是在母亲三十岁的时候出生的,仿佛一个意外,其实是冥冥之神有意的安排:母亲太孤单了,在那样深的山里教着书,一个人,长年累月的一个人,除脚边的影子再也没个伴儿,于是命运就给她派了一个做伴的人——另一个酷似她的小影子。母亲对于我的到来并不喜悦,甚至很懊恼,她已经有了一个尚在学步、需要喂养和照料的男孩子了,没有精力再照料一个更小的婴儿。在我还是颗脆弱的胚芽附着在母亲子宫里的时候,她曾用从山坡上往下蹦跳和挑重担压迫的方法试图摆脱我,摆脱这个给已经够麻烦的生活增添麻烦的意外。只是上天的意志并不以她的意志为改变,秋天的时候,我像熟了的果子从她的枝桠上落到地面。
很多年以后,我仍然频繁地梦见小小的自己走在那条弯来弯去没有尽头的山路上。山路是寂寞的,少有阳光,也少有行人,除正在草丛里生蛋的野雉和在树冠端坐的弥猴,大半天碰不到一个路人。我和母亲大概是这条山路最常见的身影了,每到周末,母亲会挑着担子走在前面,我背着小小的布包跟在母亲身后,从正午走到暮色四合才能到家。家里住着哥哥和奶奶。父亲不在家,父亲在更远的山那边工作。
我和母亲就是在山路上遇到扳匠的。先是听到扳匠的脚步声,那脚步声跟在我们的身后有一阵了,“咚,咚”,每一步都很重,甚至还有回音。母亲把担子换了一个肩头,回头看了看,催着我快些跟上。我也随着母亲的目光回过头,只看到山尖的日头快落下去了,没有看到人影——脚步声是隔着几道弯传来的。我在母亲催促的声音里感觉到了不安,母亲是害怕那很重的脚步么?这条路上经常会有奇怪的声音,隐藏在路边的灌木丛里,鬼鬼祟祟,鬼鬼祟祟,对这些声音母亲并不害怕,母亲说那是野兔和山狸在捉迷藏呢。
当脚步声接近我们身边的时候,母亲终于忍不住把担子从肩上卸下,停在路边,回头对我说,“丽敏往边上站,让让路。”这时我们就看见了一个背上扛着刀、锯、锉之类,高大得出奇的人走了过来。
“是个扳匠。”等那人走过去消失在路弯上的时候,母亲舒了口气。
“扳匠是什么啊?”对不懂的东西我总是喜欢问。
“扳匠就是做竹椅的师傅。”母亲说。
“做竹椅的师傅不是竹匠么?”
“竹匠是竹匠,扳匠是扳匠,不同的。”母亲不耐烦再给我多讲了,把担子放在肩头招呼我快一点,赶着脚向家的方向走去。
长大一些以后我才知道扳匠和竹匠的区别。竹匠是把竹子剖成篾片和篾丝,编制成竹篮、竹篓、竹筛、竹席等日用器物的师傅。扳匠是把竹子剖开后用火熏,再以臂力将熏得微黑冒汽泡的竹节扳弯,弯成九十度直角,以榫销连接,制成竹椅、竹床、竹摇篮等家具类器物的师傅。
后来,我们经常在这条山路上见到那个扳匠,有时是面对面的遇见。扳匠其实有副很和善的面目,喜欢笑,远远地看见我们就憨憨地咧开嘴,有时会指手划脚地比划着什么——原来他是哑吧。遇见的次数多了便仿佛成了熟人,如果顺路,扳匠会帮母亲挑一截路的担子,那么沉的担子一到他的肩头就变得轻了,母亲拽着我,小跑着才能赶得上。
半年后,扳匠扛着他的工具到母亲教书的村子里做事,地点就在教室的隔壁。那教室原是一间老祠堂的房子改成的,老祠堂很大,有三层院落,另两层院落派了别的用场,一层住着八旬的老五保户,一层堆了杂物,并空出一半地方专给外面来的手艺人干活用。
哑巴扳匠不会说话,每天却有很多人围在他身边看他干活,七嘴八舌地评论他的手艺。一只竹椅扳出来,小孩们便抢着坐上去,我总是抢不到,母亲也不让我抢,母亲说女孩子要有女孩子的样子。“女孩子的样子是什么样子?”我问。“就是斯斯文文的样子。”母亲说。
扳匠歇气的时候会走到教室这边来听母亲上课,坐在最后一排的空位子上,那么小的座位坐着那么高大的人,就像一只骆驼卡在小树里,简直有些可笑。扳匠脸上的表情完全不像个大人,有些羞涩,听课的态度很认真,把黑板上的字一笔一划用手指写在课桌上。
扳匠在村子里做了一段日子,临走的时候拎了两把新暂暂的竹椅放在母亲面前,涨红着脸用手比划着,指指小竹椅指指我,指指大竹椅指指母亲,又指着大竹椅的椅背让母亲看,椅背上端端正正地刻着四个字:教书育人。
母亲收下了两把竹椅,拿钱给扳匠的时候却被扳匠狠狠瞪了一眼,扳匠气呼呼地挥舞着手臂,像是自尊心受了很大的伤害,脸都变形了。母亲赶紧收起钱,指着大竹椅上的字对扳匠伸出大拇指,扳匠立刻咧嘴笑了起来,腼腆地低下头。
扳匠走了以后我们就再也没有遇到过他,大概是去了别的地方了吧。皖南有那么多的山,那么多的山路,游走异乡的手艺人不会总是走在一条山路上的。
茶 箩
皖南竹编的日常器物中数茶箩的形状最接近人的形体,有脖子,有肩膀,甚至还有微微隆起的腹部。一只茶箩倚在树下,远远看过去,酷似一个墩实的人在树荫里纳凉的样子。
在皖南,一户人家有几口人,只要数数他家有几只茶箩便知道了。细心一点的凭着茶箩就可以看出这家有几个大人,几个孩子,甚至还可以估摸出这户人家男女的比例,秀气一些的茶箩通常是女人用的,粗壮一些的茶箩自然是男人用的。小茶箩看起来颇像一件可爱的玩具,玲珑得很,模样和大茶箩倒没有什么差异,如同大人具有的肢体器官小孩也都具备,只是大小上的分别。
在皖南一个孩子够得着锅台便可拥有自己的小茶箩。茶箩的脖根上有两个对称的眼,一根粗麻索的两端系牢在眼上便是背带,讲究的人家会用几种颜色的布条编成粗绳——这样的背带又柔软又结实,不会把肩膀磨得起泡。背着小茶箩的孩子跟在大人后面,跌跌撞撞地翻过一座山坞,又翻过一座山坞,茶箩不时地磕着孩子的小腿,猛不丁还会使个绊子,故意把孩子撂倒在开满细碎草花的泥地里。
正月一过,田里的油菜就蹦出了细细的花苞,山上的杜鹃花也在精心地打着苞儿,这时候茶农们便会扛起锄头去挖春山。所谓挖春山,就是给茶山松土,将那刚冒出头的春草锄去,以免它们恣肆地疯长,吞没通往茶山的路径并抢去茶树的养分。等杜鹃花将每一座山头燃得快要窜起火苗来的时候,采茶的季节也就到了。阁楼上闲置的茶箩这时会被请下来,排列在堂前,等着主妇挨个儿抹去灰尘,系紧背带,一副精神灼灼整装待发的样子。
对我和哥哥来说,背起小茶箩上山采茶的日子几乎就是假日,有半个月的时间不用去课堂了,不用背课文也不用理会那枯燥得要命的数学题。我们像两只刚学会奔跑的幼兽,对展开在眼前的大自然新奇极了,兴奋地扑进去,在草地里打滚,在花荫里追着香气的翅膀,大口大口地品尝着春的宴席。
杜鹃花是春宴上的大菜,也是最丰盛的美味,一树挨着一树摆满了整面山坡。人在里面走着走着就迷了路,被施了幻术一般怎么也走不出去,索性采了一大捧杜鹃花在树下躺着吃起来。野草莓是春宴上的另一道美味。野草莓的名字也叫梦子,长在树上的叫树梦子,缀在草尖上的叫地梦子。满山的梦子扑闪着红星星样诱人的光亮,高一声低一声地唤着我,“小敏我在这里,小敏我在这里……”野蔷薇的花骨朵也在春光里扬起粉红的脸来招呼我,但我对它过于精致的花瓣没有食欲,我更喜欢野蔷薇新抽出来的枝条,选那肥嫩多汁的折下,剥去鼓着细刺的外皮,入口大嚼。
四月蜜糖色的阳光晒得人浑身酥软,脸颊像喝了春酒般热得发烫。和我一道上山的哥哥早不知奔到哪个山坞去了,唯有亲密伙伴小茶箩一直跟在身边,我的肚子填得饱饱的了,小茶箩的肚子还是空的,什么也没有,伸着脖子看着我,很饥饿的样子。没关系,等会去父亲的大茶箩里抓几把茶叶就足够喂饱我的小茶箩了。
对于满山乱窜的孩子,大人们并不担心,山野是孩子们的另一座学堂。每一块石头,每一棵树,每一株花草,都是亲切的老师,用它们的形状、颜色和味道教会孩子们自然的知识,并让孩子稚嫩的身体变得敏捷和健壮起来。
也就是几个茶季的功夫,孩子就出脱得和大人一般高了,肩上背的不再是玩具样的小茶箩,换成了新竹篾编的大茶箩。大茶箩伴随的脚步踏在山野里,撩起“咚咚”的回声。茶香馥郁,春深如海,年青的心里向往的春之盛宴也有了更为丰富的味道。
水 桶
当我写下“水桶”这个木质的器物名词时,这个词已然成为过去式了,就像一些在大地上消失的物种,水桶也已从村庄的日常生活中集体消失。
而我仍然记得三十年前,由水桶和扁担的哼唱里开始的生活情景。
鸡叫头遍的时候村庄醒来。父亲就着窗前薄明的曙色起床,轻手轻脚地套上衣服,去堂前把大门打开,把院门打开,折身去厨房,把架在长板凳上的一对青檀木水桶拎起,放在地上,取下挂在墙角的铁勾木扁担,一头勾起一只水桶,挑着出了门,向村头的吃水塘走去。
父亲的这一系列动作没有旁观者,却被睡在床上的我看得清清楚楚。我是通过声音来“看”的。无论多么小心,父亲的动作里还是带出了各种声响——衣服悉悉索索的私语声;木门懒洋洋的哈欠声;水桶与地面“早啊”的问候声;铁勾与水桶把子一路叽咕的哼唱声。
父亲已走出院门,走在伸向村头的石板路上了……我在被窝里翻了一个身,把一只耳朵朝向窗口,微闭着眼睛,在黎明巨大的寂静里继续“看”着——挑着空水桶的父亲还不到四十岁,腰板是直的,脚步轻捷得很,双手一前一后扶在扁担的长铁钩上,像一个走动的“木”字。父亲走到村头了,下石阶,站在幽深的吃水塘边,塘边的大青石上干干的,没有淋漓的水迹——父亲是第一个来挑水的人。
吃水塘是全村挑水吃的地方。村里人洗衣洗碗就在离家最近的河边,吃的水却一定要往村头去挑。吃水塘是村庄的活水缸,不满不溢,也从不干涸。每天早晨村里的水桶大多要来这里朝拜,俯下身去,领取水塘不绝的恩泽。
吃水塘认得村里各家的水桶——每只水桶的肩上都有着主人的名字,名字是毛笔写上去的,再用烙铁烫出漆黑的字印。一对水桶会伴随主人过完一生,直到名字的烙印全模糊了。水桶的两道箍是铁制的,桶把的边沿也用铁皮包着,很牢实。
村里的男孩长到能挑水的身高便算成年。男孩性子急,总是不等水桶装满就拎上来,挑着飞跑,手也不扶铁勾,两只水桶荡秋千般一上一下,桶里的水调皮地晃荡着,跳出来溅湿男孩的裤脚——简直是存心的作弄,一担水挑回家只剩小半桶了,男孩的鞋袜也浸透了水。
挑水在村庄是男人干的活,也有一户人家是女人挑水,这户人家的男主人很早就过世了,所生的孩子又是女儿。这户人家的女儿长到十八岁时,村里的年轻男子便抢着来给她家挑水,一时间,她家的水桶几乎成了被争夺的绣球。
父亲每天早晨要给两户人家挑水——自己家挑三桶,屋后住着的老五保户家挑两桶。父亲给老五保户家挑水的时候,村里开门声就多起来了,石板路上踏踏的脚步声彼此交错,铁勾与水桶叽咕的哼唱也成了多声部重唱。我能在众多的脚步声里辨认出父亲的,父亲落在石板上的脚步有着清新明快的节奏。
鸡叫二遍,父亲挑着最后一桶水回来了,脚步穿过院门、堂前,到了厨房,一只水桶被放在地上,另一只水桶贴着水缸边沿,倾倒,水“哗”地一声冲入水缸,那么大的声响,把薄明的天色一下子冲亮了。接着放在地上的水桶又被拎起,贴着水缸边沿,又是“哗”的一声,如村庄晨曲的高音。
——这晨曲已是三十年前的了,如今的村庄有着什么样的晨曲,我已不知晓,二十岁后我离开了村庄,很少回去。我的父母时常会回到村里住上一阵,他们已经老了,当然不再能挑水。好在自来水管十多年前便接到厨房,世代沿用的木质水桶也就是从那个时候消失的,成为一种生活方式的休止符。
草 鞋
童年在山中打猪草时,经常会在野地里遇见黄土颜色的草鞋,有时是一只,有时是一双或更多,静静地躺在草丛中,看起来有点来历不名的神秘,又仿佛天生就在那里,同它们周围的植物一样,是从乡间泥地里生长出来的。
草鞋确实生长于乡间,属于有着牛脚印的田埂、长满荆棘的山坡、石子尖锐的小径和通往家门的青石板路。一双草鞋走在乡间的路上,就像明月行走在水面,亲密柔和而又宁静无痕。
草鞋的纯植物性使得它具备了谦卑和柔韧的品质,如同那些在大地上劳作的农民,一生与黄土打着交道,隐忍着身体的疾病与疼痛,过着简朴的生活,整个世界就是头顶的那片天,以及脚步所能到达的山顶、河流。
我的伯父就是这样的农民,从八岁就开始了农事的劳作,放牛、打猪草、砍柴禾,稍大一点又开始下田插秧,再大一点就担起了家里所有的农务,年复一年,直至背驼、发白。
记忆里,伯父一直是穿着草鞋、打着绑腿的模样。草鞋是伯父自己打的,下雨天,不能下地干活的日子里,伯父就端一把长板凳放在大门口,一束薄白的光线从门外投进来,刚好够他看清手里的活计。伯父在腰间系一根腰架,横骑在长板凳的一端,另一端则绑着草鞋耙。草鞋耙是铁质的,有五个亮铮铮的长齿,形状像极了猪八戒的铁耙,只不过没有长长的柄,也小巧一些。
打草鞋的草是稻草。秋天,稻子收下来了,把稻草捆成把子垛在田里,晒干后拿回家,储存在柴屋干爽通风的地方,要用的时候就抽出一把。
一把稻草在成为草鞋之前要经历多次的捶打。捶打是为了使稻草的质地变得柔软——又不能用力过猛,这样会把稻草捶烂。熟练的人在捶稻草时会喷上一些水,有了水的润滑,稻草就不易脆断了。
伯父先将捶软了的稻草编成草绳。编好的草绳看起来酷似粗长的麻花辫子,从来没养过长发的我忍不住拿一根围在身上,装扮成长辫子姑娘,两端拿在手里甩来甩去,却被大人一把将草绳夺去,眼睛直瞪着我,做出吓人的样子,好像我做了一件极坏的事,或触犯了什么忌讳。
骑在长板凳上的伯父看起来多么威武,像是骑在一匹俊马上,脸上带着泥土一样安静的笑意,双手在草鞋耙和腰架之间系着的草绳上来回穿梭、编结,动作麻利而轻快,仿佛在弹奏一种古老的乐器,间以捶打的鼓点。
很快,一捆稻草就变成了一串金灿灿的草鞋,挂在伯父身边立着的竹杆上了。为了使之更为结实和绵软,打好的草鞋还得再经历一次捶打——就像一个人的成长,要经历一次次的坎坷才能变得坚韧。
伯父打的草鞋差不多能供半个村子里的人穿用。草鞋很轻,穿在脚上没有丝毫的负担,仿佛另一层皮肤,走在任何一条山路上都不会觉出鞋子对脚的捆绑和折磨,踩在泥田里也不会因为打滑而摔倒。
在那个汽车还没有开进山里的年月,村里有走远路的人就会到伯父家来讨一双草鞋。草鞋送走了很多年轻人,他们或去山外当学徒、做生意,或去更远的地方当兵、读书。草鞋送走的年轻人过了很多年回到村里,一个个都穿着体面的衣服和鞋子,面貌也已经变得认不出,好在说话的口音没有变。
伯父编的草鞋还送走了村里一个个的老人。我是在很多年以后才明白,童年在野地里遇见的那些草鞋是送葬时所穿。送葬的草鞋是不能穿回家的,得在回来的路上脱下来,留在村外,其意思如同“尘归尘,土归土”,一同留下的还有系在腰上的草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