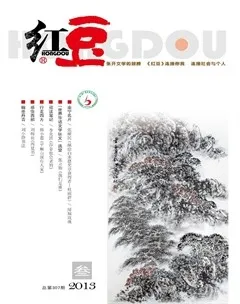岩石上的花朵(外一篇)
你准是见过灌木上的花,也见过草上的花、树上的花、菜蔬叶子上的花。
你见过星星上面开的花吗?我想,你没见过。
那么,你也没见过岩石上开出的花,对吧?
可我告诉你,这回我见到这奇异的花了!它确实开放在岩石上,透明的花瓣仿佛梦一般绽开,比高山雪莲还美,和星星开花一样神秘,像某种预言似地充满召唤的力量……只要你静静地在它身边坐一会儿,再坐一会儿,当你的心能和它沟通时,你就会开始发生崭新的变化,你的生命瞬时能领会什么叫灵性苏醒——
这朵很小、很小的透明花,就开在寿宁的南山顶上,你去看看吧。
我把这种旅行叫做机缘巧合。碰上了,就全心全意地珍惜。而且要诚心诚意地努力,不能半途而废,也不能三心两意。从福州出发登程时,有一首歌便进入我心中,“不要问我从哪里来,我的故乡在远方……”
我心中有橄榄树,才来到这东海之滨的福建。几百年前,也有个人因为梦想,跋山涉水进入福建境内——而且是福建边缘的寿宁小城。他从富庶之地苏州来的,到这个群山之间的贫乏偏僻小县任知县,他是写过著名的“三言”的冯梦龙。在寿宁,他实现了安邦益民的仕途梦,给文学史增添了具有现实主义价值的一笔。仅仅因为这个人,我就觉得应该不惜脚力,来寿宁看看他驻足四年的地方。我喜爱那些不但会写诗著文,也能身体力行为民众服务的诗人作家。只是会写几行诗、几篇文章的文人,在我看来并没什么了不起。虽然不能说百无一用,但我确实更佩服能为希腊自由捐躯的诗人拜伦,为法国正义事业参加巷战的作家维克多·雨果。他们的果敢举动提升了自己的文学意义。说到底,文人首先是人,在存亡危难之时,选择了做人的义举,才昭示出“在奥斯维辛写诗”苦难中的文学脊梁。
但是,寿宁已经不是明朝那个寿宁。今天的中国,即使在戈壁荒滩或者极地高原上,一座县城也能崛起一排排时尚的高楼大厦。招商引资带动发展的各路招数,使得无论哪里的县城都有些“千人一面”的似曾相识。一方土地的独有个性哪里去了?铲平一个个山头、劈开一座座青山,铸出钢铁水泥半个新城也许是容易的,而保存与维护一个县城源远流长的文化气脉,则非常需要良苦用心和艰苦工作。我总是不懂为了旅游开发,许多人在修复古迹、新造庙宇、重建“古”文化、“古”民居一条街,为什么不能把普通民生代代相传的自然城郭用心整理,来展示出它古老的魅力与繁衍的美丽?我这话不是虚妄,据我所知,大家涌出国门纷纷奔赴意大利、瑞士、英国参观,难道不是为了看到百年前的建筑原生态吗?西方人并不热衷于除旧布新,而让我们兴趣盎然的也不是什么速成的城雕和摩天大楼。是莱茵河畔的老教堂、塞纳河畔的老铁塔、圣母院,吸引我们前往。在西方国家,对古老教堂天际线的保护意识,使得他们坚拒商业诱惑。那里的一处处旧民居、古城堡还在发挥使用功能,不过是修修补补的结果——他们不肯以旧换新。天哪,什么时候能停止欲望膨胀的开发,不再制造新的建筑垃圾和速朽之物?什么时候会觉悟到物质所需不必很多,要更在乎心灵价值的守望?
于是,我不禁问:何者为“寿”?怎样可以“宁”?在密集簇拥商业店铺的窄巷里,我一边购买寿宁特产黄独(被称为“江南一绝”,却廉价到令我咋舌!),一边脑海里翻涌这种所谓不着边际的念头,实在是我盼望这个皇帝赐名的高山县城,真的能一代代人延续着安康宁静,成为别具一格有古老遗存的特色小城,让许多人心向往之。
在寿宁县的第三天下午,我被引领到了南山风景区。
小车疾驰,出寿宁城关19公里,到达南阳镇境内。车窗外是一座座茶山闪过,还有山间深藏的一个个原始部落般的村庄。鸡犬相闻,竹林掩映,村路在草丛中延伸,南瓜藤和御豆藤缠绕着篱笆,黑瓦白墙的矮房子安卧,几缕袅袅上升的炊烟随风而动……山野的气息扑面而来——
不久,我就伫立在南山顶的山门前了。只见唐伯虎的诗句题写在门柱两旁,陶渊明的古意被今人引用在门楣上。不言而喻,我会有一个山中诗情画意的午后了。
下车后,开始登山。南山顶海拔一千两百多米,比我曾经爬过的黄山光明顶,显然不算高。然而,登高不是目的,领略山上一路的景色才是惬意的收获。寿宁的南山顶虽然名不见经传,却并不缺乏我们所能知道的山势磅礴、怪石嶙峋、洞穴迷离、庙宇矗立。天然的、人工的数十景点可以让游人留步观望,但我对这些司空见惯的景物有点儿心不在焉。我觉得十分有趣的,则是看云雾缭绕于峡谷与山巅之间。而且,我攀援多高,云雾升腾而上多高,好像这些云雾故意尾随人的脚步,轻盈地忽而来去,游走如龙,增添了山上的空旷感,也使人心胸豁达起来。沿着先人凿出的古道拾阶而上,羊肠小径旁边是密集的树木,居然还有野果挂在树枝上,可以随便采摘而食,又平添了一种登山的乐趣。
我是在细雨中登山的。寂静的山上,微雨如梦,只有虫鸣天籁在耳畔,再就是雨滴敲打树叶的声音了,曼妙无比。到达“三省十八县观景台”时,我停下脚步,在山顶远眺——在这里,闽浙交界的高山上,我真的希望我能看见远方的外省和外省的朋友,重重山峦由深绿到浅灰,次第呈现山色之美,我为之心动,顿时默默地为亲朋祈祷平安!这一刻,女诗人伊路的《快乐》,恰恰可以写照我此时此地的心绪:
雨丝西斜
我知道南边有一些风
到处都是淅沥的声响
我知道到处都有扬起的面庞
花叶抖动藤蔓飘摇
我知道大地此刻有无数的快乐
因为一阵春雨一袭南风
来自我们目力无法到达的地方
现在,我要说说陪同我登山的王邦兴先生了。本来是任务性质的陪同采风工作,可一路同行后,我对王先生不禁肃然起敬。
王先生是官员,但他自己更愿意坦承自己是位骨科医生,专业行医大半辈子,看重的是治病救人。他对农民们患病就医难,多有感慨,也曾为农民手术治疗,不求任何回报。退休的年龄到了,谁也没想到,他居然退身到南山中,做起一个山民来。他喜爱东方的观音文化,主动在南山腰的观音阁里付出诸多精力,给人家传播精神提升的重要。他说,前半生用心于对病人骨肉疗伤,后半生希望改善痛苦者的灵魂。这种宏图大愿,尽管实现起来不容易,王先生却以慢条斯理的个性,成就自己的耐心和爱心。他童年生长在南山脚下,读书上学要翻越南山的道道山岗和沟坎,知道山中生活的艰难。退休后,他准备报答这片山岭的养育之恩,一会儿栽树,一会儿修路、修桥,把晚年余热奉献给南山的角角落落。他熟知南山上的每一种草木,每一块奇石,对来客可以如数家珍地介绍南山上有什么。走在石阶古道上,他的步伐比年轻人稳健,可想而知他走过了多少这崎岖山路。他常常吃住在山上,自己在山下播种马铃薯和其他蔬菜。我想,陶渊明的“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误落尘网中,一去三十年。羁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开荒南野际,守拙归园田。”他深谙其中味吧。
正是王先生曲径通幽左拐右攀地引路,我才可能在南山顶发现一个自然奇观——
在高高的南山顶的岩石上,竟然有一眼泉水汩汩流淌……
曾听过这样的话,山有多高水有多高。然而,我从未在高山顶上看见泉水涌出平整整的岩石。这和在沙漠里看见喷泉一样令人欣喜。清澈的泉水,遏制不住地在岩石上花朵盛开般地涌出,我的心中莫名地感动了!什么叫石头开花?这就是了。难道还有比泉水如同花蕾绽开在岩石上更美丽的花朵吗?透明的泉花自然地开放,像星光一样纯净,如同高空云卷一样圣洁——这大自然里的庄严奇葩,如果不是我们的脚步远离尘埃,又怎么可能在飞鸟栖息的地方发现呢?
王先生像珍爱宝贝一样,把藏于岩石上的这眼泉流用石头圈起来,泉涌就汇成了一泓清泉,净瓶里的甘露似地,这一泓清泉成为高山之巅的“圣水”。谁来喝一口,谁就会洗浴心灵,谁也会延年益寿。
哦,无论我们走了多么苍茫的路途,无论我们心灵上怎样蒙尘,一股清澈的泉流足以使我们歇息下来,也足以使我们洁净自己!
或者说,冥冥之中的长路,一定有冥冥之中的涌泉在等待我们。
道光年间知县何如谨在南山顶天池旁石刻上写道:“……钟声唤醒游仙梦,蛩语催成感事诗,独倚危峰数星斗,苍茫天意竟谁知?”
我只是出发时并没有预料到,我在寿宁的南山顶遇见了这眼甘泉。就像我没有预料到自己的人生来到福建,确实是又有了另一重幸福景观。
我深深地弯腰,掬水而喝,泉水沁入肺腑,心灵也为之一振。
这是我看见了岩石上的花朵啊!就像我看到了星空中的神明!
也是在南山顶上,彪炳史册的文豪知县冯梦龙,以塑像的形式屹立在山崖上。他今天还在高瞻远瞩地看着寿宁发展。尽管风雨剥蚀塑像,但一代文人大家的风骨未变,一任县令的眷眷父母心未改。他留给寿宁山水的精神遗产太丰厚了,就像书法家朱以撒先生题写在南山上的墨宝——“梦龙遗风”所显示的:即使物质上的诸多楼宇可以频繁更替,可冯梦龙为官一方的勤勉之道却会精神恒久。他那爱民为民的清正之风,已然浸润在寿宁人的一代代血脉中。
“不要问我从哪里来,我的故乡在远方……”
文学家冯梦龙的“橄榄树”,在寿宁。他的精神风范也是岩石上的花朵。
何者为“寿”?能造福人间,精神高贵传承百代,乃仁者寿。
怎样可以“宁”?以心怀天下平安为良知,勇于施舍甘泉为民众,圣心如清风明月,便能宁。
这样一想,寿宁的南山,不同于其他地方的所有南山,我觉得该称其为寿山了。
我们亲切的银
不知不觉间,白银又来到了我们生活中。你去福州著名的三坊七巷里走走,会发现很多家银器店铺栖身于南后街上,就连黄金的位置好像也没有白银显得这么突出了,难道时光流转,又一个美丽的白银时代已经悄然到来?
这不是个陌生的信息。对白银的记忆远没有杳无踪迹,上溯两代就可以寻根到温暖的白银气息,我们祖母的手腕上晃动银镯的光亮,仿佛就在昨天。只不过在上个世纪一个过于清贫的时间段后,人们忽然猛烈地爱好黄金,对财富趋之若鹜,便冷落了平民意识十足的白银。零散的若隐若现,则在少数民族地区的一些风习里,还能见到白银富丽的光泽,婚嫁时新娘的颈项前胸上若缺少了银饰,好像那新娘就不能不说是简陋了。中国西南的苗族、布依族、彝族、白族、土家族、藏族,中国北方的蒙古族、满族,中国东南的畲族、高山族……迄今都有这种共同的崇尚银饰现象。一旦妇女们佩戴起来明亮闪闪的白银,似乎一生的幸福就可以注定了。我想,这不仅仅是与财富相联系的务实做法,还有某种形而上的祈福价值观蕴含其中。很有特色的原始文明遗存与继承,大概只有生活纯朴的人们才能仍如此对待自己的先民文化。而汉民族与白银的瓜葛,首饰是算不上什么显赫的,我们更多的印象大致与通货有关。千百年来说到白银时常常指的是“银子”,不管是元宝、银锭还是碎银,或者后来的银币,古代近代中国和异邦均不例外地都用来当钱使用,怎么说,这也足以说明白银是贵重金属——据资料记载,竟然历史上白银曾比黄金价值还高,匪夷所思不?不然,物以稀为贵,采矿业熟悉这种大地珍稀的自然规律。
我是不大愿意佩戴首饰的,即使结婚大事,也只是勉强能接受一个婚戒而已。但那是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大家一窝蜂地选择黄金戒指,我说啥也不想无名指上弄个黄澄澄的家伙炫耀,于是多年来手上、腕上、颈上都光秃秃地裸着,直到铂金出现并且流行,总算是成全了我也能佩戴结婚戒指。然而,我对首饰热情起来,一个转折点,真是缘于白银。女友画家林任菁出差贵州,回来后送我一个礼物:一只镂花银镯。非常美,花式和镯子造型都绝对既有传统文化味道,又很有现代感。我拿在手上,不戴都不可能的了,因为觉得实在是难得的美饰,一个女性敏感于美就很难拒绝这个水准的装扮,所以这件银饰伴随我多年。从那以后,我走到哪里,便都留心银饰了。认识厦门一个女诗人,她由衷喜爱银饰的劲头让我开了眼。无论冬夏,都能见到她佩戴的一两件银饰。这几乎成了她独特的气质和个人风格,一种很难模仿出来的女人味道。白银给女性的美,好像是格外的重赏,就像我们看月光一样,白银和女性之间有了天然的亲密关系。
说到白银,我们不能不想到人类史上有个白银时代。这是古希腊神话里划分人类发展的第二个时代,这个时期人类感情发达甚于理智,比较于后来的青铜时代、黑铁时代,是某种情感纯洁阶段。所以,后世文学史,也用“白银时代”称呼一个国家与民族的诗坛重新兴盛——有点儿文学常识的人都知道,俄罗斯白银时代的文学群星闪耀,把俄罗斯诗歌贡献推向一个高峰,我们熟知的帕斯捷尔纳克、阿赫玛托娃、茨维塔耶娃、勃洛克、吉皮乌斯、马雅可夫斯基、曼德尔斯塔姆等一代诗歌骄子写下的作品,岂止是俄罗斯人民独享?应说是对人类的特殊奉献。可见用白银命名的事物,从来不包含平庸或俗气,相反,白银给我们的提示,常常是某种高贵和高洁的精神凝聚,让人怀想而念忆。
满足了我这个思念的情愫,也是我佩戴上一件银饰之时。这一次是我用心自选的,在老字号的“盈盛号”里,我浏览那些琳琅满目的银器,像回顾我人生难忘的情感事件一样,内心波澜浮动……而我必须把最美好的爱,固定在我最想要的一个首饰上,这是只有我自己洞悉的隐秘图像,我把灵魂里的爱情吹送到这件银饰里——爱情是需要纪念的,在我心中,爱情等同于生命的宝贵。每天爱情像黎明的鸟叫唤醒我,这时光我对白银的亲密态度便已经渗入到我的骨血中。
理解白银的美质,银匠有发言权。他们在银器上花掉的心思和甘苦,只有个人自知。一片银箔,一朵银花,一段银丝,会把他们的眼力和心力提升到显微镜般的高度,不但是技巧高明,还要有充分的感情投入,如愿以偿的银制品才能出现。我们今天看不见走街串巷的银匠了,他们现在已深藏在老字号店铺的工作室里,身份早已不是廉价的作坊师傅,而是工艺大师和设计师——时代赋予他们更高级的身价。但是,银器的价位仍然传承不远时代的平民意识,随便一个白领甚或打工女郎,都可以享受银制品的华光,真是这个时代难得一见的厚道。走进一家银饰店,绝不用考虑腰包是否鼓,打量一件喜爱的银饰,不必只是饱饱眼福,愿意的话,顷刻就可以把选好的饰品归为己有。这时我们要非常感谢银匠的创新思想,就说百年老店“盈盛号”吧,无论是工艺礼品,还是女性需求的手镯、项链、手链、耳饰,新的创意显而易见,保留历史优秀元素的同时,时尚符号不断出现在产品中。搭配我们潮流服装和发型,这些新的银饰绝对做到了恰到好处。你尝试复古风也好,你选择流行风也罢,都会得到温馨的体贴。
典雅的白银,终于又回归到我们身上。作为女性,我对白银的亲切感,就像我对棉布的信赖。我们可以转换很多种材质的服装,丝绸、化纤、混纺不一而足,但棉布不仅没有被淘汰,还成了我们最放心的贴身应用,什么时候、什么人,也不会对棉布厌倦吧。我想,我对银饰的佩戴,也会是越发一往情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