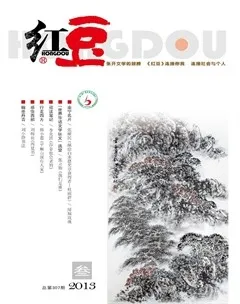植物记
植物之约
我对新疆的认识来自多年前一个作家朋友——他同时也是一个狂热的摄影爱好者——从新疆带回来的大堆照片:沉睡的喀纳斯湖,夕照、炊烟下的白哈巴,远山、牧马被层次繁复的蓝笼罩着的那拉提,银白树干和金黄透亮的哈巴河白桦林,魔鬼城乌尔禾,吐鲁番汲水的维吾尔少女,春天黄色小花铺排盛开的赛里木湖,布尔津的落日、树和天空,广袤草原和湖海的巴音布鲁克……
我被那些色彩所惊醒。那一树树繁茂金子般的胡杨,那蓝得旷世寂寞的天空,超现实得近乎不可思议。人间真有如此绝美的静谧和澄澈?诡谲和斑斓?我有些恍惚,找不到一个恰切的词形容我那时的感受。
多年后,我从王彬彬《2012年〈回族文学〉读札》一文里获知一个叫冶福生的西北作家,他在一篇小说里写到村庄天空的蓝:“是那种让人心慌的蓝,那种一揭去蓝帷幕就能看到什么的蓝。”——我和王彬彬一样,觉得用“让人心慌”来形容天空的蓝,真是准确又尖新之极!也终于记起,曾经我被一大叠新疆照片所震慑,就是“心慌”这样一种心理状态——那澄澈无边的蓝,那璀璨透亮的黄,以强烈的视觉冲击,而令你瞬间眩晕。
然而我的新疆之行,一再地因各般琐事而延宕。或许是为“回报”我的一次次擦肩,2012年的8月和9月,我竟连着两次踏上新疆的阿勒泰和伊犁。如今我的脑海里回旋着那一路去过的地方,布尔津、五彩滩、喀纳斯、天池、吐鲁番、赛里木湖、伊犁将军府、巴彦岱镇、喀赞其、塔兰奇……我的饕餮大餐般的眼睛,来不及消化那一路的盛宴。而我的匆促的闯入和探看,也注定了仅仅是、只能是一个外来者的走马观花。
那么就说说植物吧。我的每一次出行,总忘不了对一朵花、一株草、一棵树的投注。我对某个地方的回忆,也常常是融入了某种植物的回忆。我的相机里永远装着花儿、草叶和树。尤其是树和树的天空。我的一次次行走,惯常姿势总是仰望,仰望远树和近树,一棵树、两棵树,乃至一整片树,它们在光与影之间细微的不同。
此刻,我的脑海里漫过在新疆路途上看到的树:白杨树、葡萄树、桑树、榆树、桦树、柳树、胡杨树、石榴树、沙枣树、无花果树、红柳、梭梭……不单是树,还有很多的草本植物。写《植物的故事》的英国《独立报》园艺版记者、专栏作家安娜·帕福德曾骑马与哈萨克牧马人亚历山大一起穿越中亚天山山脉。一路上随处可见贝母属植物、蓝鸢尾、荨麻、藏红花、郁金香、粉色樱桃、葱属植物、成片的紫罗兰、大茴香、紫堇属植物、叶子呈箭头状的黑海芋……“简直比哈萨克人地毯上的针脚还要细密。”
所有这些在东方遍地丛生的植物,它们曾千里迢迢,从中亚的故乡辗转迁居到了欧洲的大小城市:帕多瓦、普罗旺斯、巴黎、莱顿,乃至伦敦。它们在异乡被赋予了新“身份”,甚而脱胎为“新贵”。安娜在书里写到一个数据:“在15世纪中期到16世纪中期的一百年间,由东方引入欧洲的植物数量几乎相当于过去2000年中引入数量总和的20倍。”
这很令我感慨。一直以来,我从各种书里获知和认得那些“西方植物”,比如玫瑰,却恰恰是由亚洲引入欧洲才光芒四射。——其实玫瑰叫不叫玫瑰有什么关系呢?牧马人亚历山大叫得出天山山脉脚下80%的植物通用名——梨是“格鲁沙”,荨麻是“克拉皮瓦”,鸢尾是“乌克拉”,郁金香是“凯斯卡尔达克”,还有那些美Iw268ESUodVpnAOhwknN/A==味的蘑菇——“西纳诺兹卡”!
还有菘蓝,也就是板蓝根、大青叶,可是维吾尔人给了它一个好听的名字:奥斯曼。叫菘蓝时,它是染坊里的染料。叫板蓝根时,我理所当然地视它为清凉解毒的草药。而在维吾尔人家的庭院、在新疆大大小小的巴扎上,它却奇迹般地重生,它有一个美丽的名字奥斯曼草,维吾尔女子用它来描眉生眉。
在新疆生活了二十多年的诗人沈苇写过一本书《植物传奇》,我在书里识得它,知道每一个维吾尔女子还是小姑娘时,她的妈妈都会用奥斯曼草汁给她描眉画眉。想象那些捣碎了的深绿汁液,丝丝缕缕被眉毛吸附、蔓延、生长,那是怎样一种草木葱茏的舒展!
那个下午,在伊宁市达达木图乡布拉克村的塔兰奇文化村,我邂逅了这种草。意外相逢,竟似旧友般亲切。阳光铺洒的庭院,我梦幻般重返童年——一位维吾尔族大妈在给小女孩涂抹奥斯曼草汁,我弯腰上前,也请大妈帮我画眉。有心的《伊犁晚报》首席记者卢钟拍下了这一瞬间。看到照片,真是喜悦!那个坐在我和大妈间的小女孩,抬起画好了奥斯曼眉的额,眼里盛满清澈和纯真,还有一脸友善的好奇——哈!是呀,这真像一个寓言,它以无可预知的方式把我带回小时候。那眉毛上的奥斯曼,是通向童年的桥梁。
很多国家和民族都有自己的象征植物,如白桦之于俄罗斯、樱花之于日本、郁金香之于荷兰、猴面包树之于南非……那么广袤深阔的新疆呢,似乎很难用一两种植物来概括。新疆的植物太丰茂了!只要有绿洲,就有树。哪怕是沙漠和戈壁,也都奋力长出梭梭、红柳、沙棘和骆驼刺。
在喀赞其坐“马的”,迎接我们的一条条巷道,齐刷刷都是树,大树小树。刷着和天空一样颜色的维吾尔族民居,从洞开的庭院里看到更多的绿:葡萄架上挂着串串饱满透亮的葡萄,石榴树、无花果树枝繁叶茂,各种鲜花长势兴旺。你走进任何一家庭院,扑面而来的肯定是遮荫的绿、绿、绿。炎热阳光泼洒在葡萄藤蔓上、无花果树的枝叶上,你站在绿荫下,看天看地,眼里都是斑驳的光影,恍惚有迷离之感——那是一个陌生的闯入者在维吾尔人家感受到的第一丝气息:绿气息。维吾尔族聚居的城市还有很多别的气息:香料的气息,经书的气息,尘土的气息,巴扎的气息,麦西来甫的气息……所有这些气息构成了一座城市的灵和魂。而所有这些气息中,绿是第一位的。
维吾尔族是一个爱树如命的民族,他们每到一个地方,决定居住下来时,首先要种几棵树,然后才是盖房子。维吾尔谚语:“绿洲上没有树荫,还不如在戈壁滩上活。”“在地下种树的人,能够吃到天堂里的果子。”所以你无论在城市的大街小巷行走,还是隔着车窗玻璃远望绿洲、农田、村庄和荒野,你总能够看到树。
我在伊犁将军府看到两棵120年的古榆树,沧桑浓郁。榆树的枝桠胡乱地向上伸展着。不讲章法的个性有点像胡杨,也是一径向上,自由随性,每个枝桠都乱长胡伸——不像南方的树,很多南方的树都被人为地修剪成球状、伞状、树篱状。尤其是主干道上的树,刚有一点繁茂气象,就被园林工人以“养护”为名不动声色地肢解了!还有些树,因为病虫侵蚀,被一劳永逸地用水泥将树窟窿死死堵住。这个硕大难看的疤,从此突兀地暴露在城市的日光下。更多景观道上的树,干脆不见一片叶子,枝枝桠桠缠满了电线和小灯管,白天你不会注意到它,及至晚上才闪出它雪花般的银亮和霓虹来——可,这已经不是一棵树自身的美了。
所以,我武断地以为,城市里的树不是树。城市里的树,可以是景观灯的依附,是聊胜于无的安慰或点缀,就不是一棵自然生长的树。自然生长的树在原野,在绿洲,在山谷,在森林,在很多爱树如命的民族间。沈苇在《植物传奇》里说到一些北方民族(尤其是阿尔泰语系民族)的记忆中,有崇拜苍天、高山和树木的传统,“认为树是天空的支柱、神灵的居所。”——其实树神崇拜,几乎是遍布世界各个民族的一种习俗。有的民族甚至规定禁止去采摘树神上哪怕是一片树叶。那才是一棵树的福祉!这样的树,是生命树、灵魂树。
那两棵伊犁将军府大堂前的古榆树,肯定也是神树。大片大片长在绿洲上的野性的胡杨林、白桦林肯定也是神树。所以在新疆行走,你总会相逢一个个灵魂。它们或呢喃低语,或呼啸着舞蹈,或配以苍凉的呼告,或欢腾歌唱,或忧伤,或快乐,或激越……而你无论遭遇什么样的灵魂,最好的表情是学会一声不吭,懂得静立驻足。
安德烈·纪德在《人间食粮》里说:“自然万物都在追求快乐。正是快乐促使草茎长高,芽苞抽叶,花蕾绽开。正是快乐安排花冠和阳光接吻,邀请一切存活的事物举行婚礼,让休眠的幼虫变成蛹;再让蛾子逃出蛹壳的囚笼。正是快乐的指引下,万物都向往最大的安逸,更自觉地趋向进步……”
其实植物和人类一样,一切的灵魂的挣扎,都是为找寻一个让自己安居的家。
花、树和青苔
在瑞丽中缅边界的桥岸边看到一棵凤凰花树,高大繁盛,花朵烁烁。你一抬头,就撞见了一树红花。大朵大朵的醒目着,如火如荼。风吹过,啪啦,一朵花从高空里坠落。水泥地上尽是硕大花朵和鸟羽一样的花瓣,也无人捡拾无人在意。喜欢花的女子,弯腰捡起一朵,再一朵,满心喜悦。人在树下,也有了花一样的神情。低首微笑,朴素温柔。
大巴在老滇缅公路上行驶时,还看到路两旁一树一树开得热烈的扶桑花。红的惊艳,粉的嫣然,白的晃眼。也是大朵大朵,一点也不低调矜持。此地的花和树,和生长在这里的傣族、景颇族女子一样,皆热情灿烂,盛装裸足。在莫里热带雨林看到的三角梅,也不似别处的规整有序和探头探脑,一簇簇一丛丛,尽一切可能地高攀到直插云霄的竹梢上,不管不顾,大胆热烈。
比之花,更耐看的是树。我喜欢仰望树的天空。站在一棵棵高大繁盛的树下,我总是情不自禁仰头、仰头、再仰头。天空在繁密枝叶间漏将下来,树影婆娑。一盏一盏的金色小灯砸进眼里,瞬间眩晕。这是在夏天。秋天又不同。北方的秋天,天空高远,旷世寂寞,这时候你抬头,透过杨树、枫树、槐树、核桃树……疏朗峻拔、秋意浸染的枝桠,任何角度,你看到的都是一幅绝美的画。再也没有比这更辽阔、纯净、葳蕤和静谧的天空了!第一次,我伫立在树下发呆、出神,一声不吭仰望天空和流云。那些流云就是天上的帆船,载着你在天空中翱翔。
我还喜欢密林间长满青苔的石头。在雨林里看到一块不规整的顽石,佛一样静卧着,一动不动。若仅仅只是一块什么都不长的干枯石头——城市里多的是这样的石头,高价买来,雕成山水或是动物的模样,被买主供起来,视作镇店(楼)之宝,在我看来了无生趣。可是在雨林里的顽石却不同。温润潮湿的热带雨林,连石头也是有生命的。呼应着高大的绿树、缠结的藤蔓、羊齿植物和灌木丛,林间大大小小的石头上,覆满了翠绿青苔,浓密厚实。你用手去碰它,轻轻触摸,一阵酥痒的喜悦。
脑海里翻出我和青苔相逢的美好时刻。一次在川藏高原的山林间,我邂逅了大片大片长在泥地上、倒木上和玛尼堆上的青苔。我俯下身,将脸轻轻地靠向它们,漫生在青白石块垒成的玛尼堆上的翠绿青苔,仿佛是我的旧友,甚或说丢失了的童年的自己——那一刻,我在雾霭密布的森林里把它们找回来了!它们是那样清洁、孤傲,恣意生长着,远离喧嚷……
又一次,在庐山植物园看到陈寅恪墓。一般游客不知陈寅恪,也甚少来拜谒,幸而获得一份清和静。陈寅恪是江西修水人,墓地选在这里,和一山的草木结邻,甚是合宜。墓地简素得只三块形状各异的石头。一块大石上刻着他写给王国维的名言:“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这令我想起湘西凤凰的沈从文墓。也是安于喧嚷市声外的山角僻静处。墓地一块大石头,正面刻着沈从文手迹:“照我思索,能理解我;照我思索,可认识人。”背面是其姨妹张充和手书撰联:“不折不从,星斗其文;亦慈亦让,赤子其人。”
比之沈从文墓的清幽静谧,虫声寂寂,总觉得陈寅恪墓少了点什么。少了什么呢,一时懵懂。及至步出墓地,看到小径空阔处的两棵老水杉,顶天立地,隐天蔽日——这才豁然!陈寅恪墓地的三块石头太干净了,亦不见葱茏的大树。眼前这两棵水杉相依而立,里侧的一棵树干上绿绿的覆满青苔,像是一件滴翠的绿绒衣,真真清宁安好。
陈寅恪墓若是隐在这两棵覆着苔藓的水杉旁,那就理想了。
植物亦如人,也是有灵魂的。若持一颗朴素静美的心,你能感受到它身上的诸多美德,比如沉默,比如荫庇,比如岁月荣枯,比如汪曾祺笔下的“莲花池外少行人,野店苔痕一寸深”的怅然!
沿途的花事
写过一篇《看树》,想着可续一篇《看花》。也搜罗了不少草木花事书,却是一宕再宕,未有行动。倒是在草木文字里浸染久了,越发的珍重起来,不敢敷衍,怕生生辜负了那些花儿草儿。遂悄悄发愿:但有时间,我要一篇一篇地将与自己有缘的花儿草儿逐一写来。
脑海里泛起老家门前一株紫玉兰,早春里烁烁怒放,一夜风催,“纷纷开且落”。兀自开落了好些年,却才知,紫玉兰在古代叫辛夷!而我曾以此为名写过一本书《辛夷花在摇晃》,更早些,我信手给自己取了个网名辛夷花——莫不是天意注定,怎解此番缘分?真真是“不能名言,惟有赞叹;赞叹不出,惟有欢喜!”(俞平伯语)
正当紫玉兰、白玉兰狂花满天,一树一树地醒目迎春时,可巧有机会,与三五女伴去嘉善看杜鹃花。约定的日子,因这个早春的寒凉而延宕。于我却是欣慰,春意迟迟,何妨慢些,花事已了,春也去了,慢慢地等待一场花事之约,好比细用慢享一个完整的春天,多少快乐难得!
于是每日上下班路上,特别留意经过的一个公园。玉兰花开尽,梅花桃花樱花梨花次第缤纷。眼见一树树花儿繁盛地开,纷扬地落,而树下四围多年生草花圃却只有新绿,尚无花蕾,点缀其中的绿叶小灌木,即是别名映山红的杜鹃。若不是有一个杜鹃花约,多年来路经于此,何曾投以别样关注,只因它太过寻常了。乃至对它何时孕蕾,何时花开叶长,何时繁花灼灼,都浑然不觉。
这个早春,我沿途的投注却都在杜鹃上了。又从旧书网上觅来科学小品名家贾祖璋的《花与文学》,刘难方、王兴麟选注的《历代杜鹃花诗选》。从科普记述,到文人雅士的诗词吟咏,算是对杜鹃花的前世今生有了番印象,亦长了见识。
杜鹃花有许多别名,见于唐代的有山石榴、山榴、山踯躅、踯躅和红踯躅,宋代起又有映山红和石岩的名称。我看贾祖璋摘引的文献,明王世懋《学圃杂疏》称:花之红者曰杜鹃,叶细花小、色鲜瓣密者曰石岩。——这“叶细花小、色鲜瓣密者”不就是我在嘉善碧云花园看到的杜鹃盆景么?云片的造型,小叶小花密集地铺陈,乍看去,嫣然秀致,一片霞锦。花园主人道,别小看这造型别致的小叶小花种,年久的树龄已达百年,植株看不出嫁接痕迹,一树开出粉、白、紫、红等多种颜色,比之大叶大花的寻常映山红,确乎珍稀与难得了。
贾祖璋只道是“石岩”,他收录书中的《杜鹃啼处花成血》写于1987年。巧的是,这一年,杜鹃花被确定为嘉善县县花。翌年,贾老逝世。惜乎有生之年,钟爱花木一生的老人,未能得见嘉善人培植出来的新品种。
我在城市的花园、路旁、庭院看到的杜鹃,又叫西洋杜鹃(西鹃),有别于小叶小花的东洋杜鹃(东鹃)。《历代杜鹃花诗选》载:“来自日本的东鹃,有能在春、秋开两次花的‘四季之誉’;最早在荷兰、比利时育成的西鹃,于七至八月间孕育花蕾,也能在秋冬开花……”“东洋鹃,因来自日本之故,又称石岩、夹套、春鹃小花种等。”
若不是拜读贾老著述在前,如上文字怎会引我慨叹——却原来,这所谓西鹃,原是从我国输入西欧,经栽培杂交而得,如英国18世纪栽培的欧洲杜鹃花只10种左右,20世纪初发展到千余个种和品种。及至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又回输到我国,称西洋杜鹃。而这东鹃,同样是早在唐代传入日本,后又分别输入我国和欧美。贾老谨严的文风亦忍不住感叹:“这个名称,不免有点数典忘祖,因为它们主要是从我国产的多种杜鹃花培养而成的……”
撇开这些不谈,我对杜鹃花的认识,源自大学时收到贵州友人寄来的一枚蓝杜鹃。薄如蝉翼的深蓝花瓣与枝叶压成了花标本,成为我草叶收藏的珍爱。我且给它配了诗。此后但有收藏,即配诗一首。如今这些稚拙的青春吟唱,连同三大本“草叶集”、“草叶集”里已然枯萎的杜鹃花骸一样,真真“花事已了,春也去了”——然,谁说不是秦观云“芳菲歇去何须恨,夏木阴阴正可人”呢?
少年花间岁月回不去,但有诗为证,草叶为证,再从纸上回到花树天地间,不是怅然,而是喜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