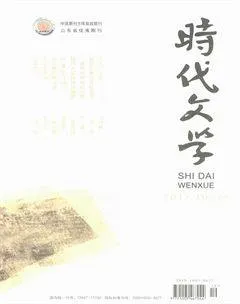宁昭收小小说二题
某局长逸事
某局长,不知何方人士,不知姓甚名谁,从一个小职员,一直拼爬到局长的位子,个中酸甜苦辣,曲曲折折,或许只有他一个人品味得出。但他有许多趣闻轶事在周围流传,姑记几则。
耳聋
某局长耳聋,在单位是出了名的。一次,下属单位火急火燎地送来一份文件,需要他签署,当时他正在某酒店用餐,已是三点多了,办公室主任便给他打电话:局长,单位有急事,请速回。他答:啊啊。办公室主任又说:上面催得紧,得你抓紧办理。他答:哦哦。回到单位时已是五点多钟了。
某人欲想巴结他,便天天守着某局长说屁话:局长真有魄力,局长真体贴群众,局长真有眼光。某局长总是啊啊而已。
一日,小张到某局长老家联系业务,同某局长的一位亲戚相遇,便说起某局长的为人,得知他尚有一八旬老母,住在三间草房内。回到单位,他随便和同事说说 ,某局长对母亲不大孝顺,恰巧某局长从办公室外走过。
第二天,小张便被下放到基层单位。临走时,某局长道:小张,到基层锻炼锻炼吧,多了解基层的苦楚,得为群众解忧愁啊,学会孝敬父老乡亲啊。
好酒
某局长是大家公认的性情中人,一日,同事闲聊,便问某局长,如果大难来时,你最后舍弃的是什么?某局长答:酒。
某局长好喝酒,喝就喝茅台。这好像是单位的广告用语。下基层,下属准备的必然是茅台。向上汇报工作,某局长必是携茅台前往。
一日,到某乡镇视察工作,乡镇长是其老同事,玩笑般地汇报说:仅有的两瓶茅台酒被另外一位局长定下了,凑合着喝点五粮液吧。某局长听罢,掉头就走。
于是某局长便得了一个“茅台局长”的外号。
忽然有一天,某局长宣布从此戒酒。下属们好像松了一大口气。追究局长戒酒的原委, 有的说是局长得了酒精肝,有的说是局长被市长批评了,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最后消息灵通人士透露:某局长听说茅台酒多假酒,害怕损害自己的身体,改喝法国的葡萄酒了。
后代
某局长最担心的就是后代的健康问题,因为他听人说喝酒多的人会影响后代的智商。
某局长有一个女儿,从小聪明伶俐,活泼可人。虽然最终只是考了一个中专,但三年后,凭着他多年的关系,被安排到一个市级机关工作。
儿大当婚,女大当嫁。到了年龄,某局长的女儿自然是嫁了一个如意郎君。
女儿怀孕后,某局长的太太今天买海参,明天买鲍鱼,生怕因营养不良影响了下一代的身体健康。
十月怀胎,一朝分娩。某局长的女儿产下了一个女儿,正在大家拍手相庆之时,医生忽然发现,某局长的外孙女竟有一个先天缺陷:没有屁眼。
某局长听说过,谁做多了亏心事,谁就会生个没屁眼的后代。
在通过手术给外孙女造了一个人工屁眼后,某局长从此竟像变了一个人一样。
文革旧事
盛夏,炎热。无事可做,遂摇着芭蕉扇,坐在树荫里想起了一些往事。特别是在上个世纪六七十年的的事,也就是文化大革命时候在乡村发生的一些事,现在回想起来,颇有意味,摘录几则,引人一笑。
往外揪
董某,40岁左右,是社办企业的工人,为人木讷、直诚,长得瘦小精干。那时,粮食和棉花是生产队的主要产品,棉花采摘完后,多有人采摘遗落的棉花,拿回家,积少成多,纺线织布做衣服。大家都穷,对于这样的事,大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一日,其妻女到生产队里采摘后的棉花地里拾棉花,顺便拿回家。他得知后,立即到大队部汇报,说是:挖集体墙角。村干部说:无妨。他说:不能让这种风气蔓延。妻女被游街示众。公社里因他检举有功,奖给他十斤棉花。虽得了奖励,社员们却对他另眼看待,便给他起了个外号:往外揪。每次他从本村到公社驻地厂子上班,孩童们都喊:往外揪。他只笑笑,从不回话。直到社办企业破产,他被人喊了十多年往外揪。
现在,他八十多岁,现在的孩子们都叫他董大爷,他的外号早就被人遗忘了。
矬人高声
某某,是造反派的一个小头头,在公社里是挂了号的积极分子。他个子不高,嗓门却极大。用当地百姓的话说就是矬人高声。每次揪斗地富反坏右分子的时候,都由他带头喊口号。
一次,公社革委会揪斗县里的老干部,公社周围几十个大队的社员都参加,声势着实了得。某某是第一次见到那么多的人,心里不免紧张起来。在带头喊口号时出了错,把打倒某人,喊成了打倒某某,群众不知就里,也随声高喊打倒某某。
当晚,某某被县里的造反派押走,被判有期徒刑十年,理由是:现行反革命。
十年后,某某出狱,正赶上了改革开放,他也没有一技之长,便干起了卖老鼠药的买卖。在集上,他吆喝的声音格外高,格外亮,三里乡五里庄的群众,都知道他有些冤枉,便都去买他的老鼠药。生意红火,不出几年便成了当地有名的万元户。
后来,他听一位老道说,卖老鼠药杀生太多,便洗手不干。后,不知所终。
饥饿年代
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是一个特殊的年代。留给人的记忆,仿佛就是饥饿。人们好像什么都可以拿到餐桌上,天上飞的,地上跑的,水里游的,动物、植物、微生物,甚至树的皮,草的根。因此就出现了许多和吃有关的笑话。
小六子,三十多岁,东乡人氏,自小父母双亡,没有给他留下更多的遗产,只有一座破草房,几张锄镰掀撅,还有一张烂床。
家里穷,直到成家的年龄了,也没有娶上房媳妇。看着年龄相仿的人都当了爹,他一方面羡慕得了不得,一方面又自觉形惭。日子也就过的稀里马虎,没有劲头。
在吃上更不讲究,一顿稠一顿稀,三顿饱两顿饥。邻里们看他可怜,时有周济,但解决不了大问题。
虽然过得这样,但他却有个馋嘴的毛病,见了好的不愿吃孬的,见了细的不愿吃粗的。
那年春天,村东头小盒子家开了一个肴菜店,他便想去买点猪头下货吃,当时只要几毛钱一斤,但凑来凑去,也没有凑出几分钱来,又不好因为这事去麻烦别人,就在心里系着一个扣。
一次,他从从村东头走,忽然闻到了一股异香,那是猪头下货的香味。原来,小盒子在卖了一段时间的别人的货后,便琢磨着自己煮猪头下货,软磨硬泡到镇上的饭店里淘来了配方,便真的自己煮了起来。
小六子闻着猪头下货的香味,如醉如痴。忽然跑了起来,来到家里,拿起干粮筐子找了一个遍,找到了一块玉米面子窝头。然后,又匆匆的往回跑。来到小盒子的院外,站在墙边,做起了深呼吸,接着就咬了一口窝头。一边做深呼吸,一边啃着窝头。不几口,就把那块窝头啃完了。紧接着,他竟嚎啕大哭起来。
街坊们听到哭声,聚拢了过来。见是小六子扶着墙大哭,便问为什么?
小六子哽咽着说:这么好的猪头下货,竟没有个馒头来配菜,遗憾啊,呜呜,呜呜。
酒虫子
有的人喝酒酒量大,有的人喝酒酒量小。有的人愿意喝酒,有的人不愿意喝酒。归根到底,老百姓说是因为有酒虫子的缘故。
酒虫子,大家都没有见过。据说是长着一个三角形的脑袋,一只眼,一条长长的软软的身子的怪物。
谁要是有了酒虫子,谁就会嗜酒如命。身体会消瘦下去,酒量却会越来越大。
张三爷就是一个有酒虫子的人。他家里过去是一个大地主,家大业大,人口多。他爹娘一撒手,就把这么大的家业留给了他。他也不善经营,就任由那几个师爷操持。师爷们看他好哄瞒,便做起了手脚,往自己兜里藏掖。偌大的家业便开始走下坡路。张三爷正值年轻气盛,讲究的是仗义疏财,结交的是一些酒肉朋友。不几年家道就败落干净了。几百亩地,他都卖给了周围的几个勤快人,几座宅子抵了赌债和酒债。一个如花似玉的媳妇也跟着人家跑了,只剩下穷光净蛋的他。
这倒成了一件好事。在解放时他被化成了贫农,那几个买他房子的勤快人被划成了地主。文化大革命一起,他因祸成福,逃脱去了戴高帽子游街受批斗的厄运。
自小,张三爷文不成、武不就,没有学成什么本事,骑马坐车惯了的他,特会照顾牲口。瘦骡子懒马,只要在他手里一顾侍,再瘦的牲口也会变得膘肥体壮,虎虎生风。因此,生产队里就叫他当了饲养员兼车把式。
喝酒的嗜好一直没有改,要不大家都说他身体里有酒虫子么。
每天,他都会到村里的代销处,打上二两酒,买上一包花生米。回到家里,一边喝酒,一边吃着花生米。脸上就会露出惬意的微笑。
一年冬天,他得了病。长病期间,医生嘱咐他忌酒。头几天,他还听说,忍到第四天的时候,再也忍不住了,拖着瘦瘦的身子来到了代销处,让营业员打上了二两酒,依着柜台一饮而尽,然后用袄袖子把嘴捂住,便摇摇晃晃的走出了代销处。路上碰上人,也不说话,只是用那只闲着的手比比划划。
第二天,他的病竟神奇般的好利索了。
后来,大家问起此事,他解释说:说啥也不能让那么好的酒香随便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