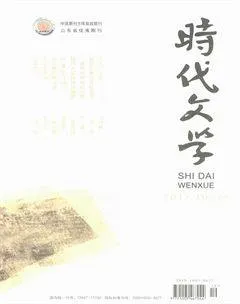沉重的飞翔
这是任立的第二本诗集,第一本由林莽作序的《任立的诗》出版于2002年9月。7年过去了,诗的庄稼是该又一次收获了。真如诗集中说的《干活,没有什么不好》,干写诗这个活,更没有什么不好。任立爱干这个活,这个活一旦干起来,就再也停不下来,恐怕要干一辈子了,而且这个活最后会使任立飞翔起来。在任立的一生中,有两件事是不能不干的,一件是经营生活,与山东农业大学一个下属企业合作的生意,奉老抚小,不仅仅养家糊口,还要让生活越过越好。另外一件就是写诗,这是为了“使我保持着诗和歌的天真 / 保持着大自然一样纯美的心灵”(《这是我的家》)。前一件事是面对现实,承受生活之重;后一件事是展翅飞翔,寻觅心灵的家乡。这两件事合起来就是任立的人生,虽然跌宕起伏,但他一定会像雄鹰一样飞翔天空。就是这本诗集,就是我这篇序的题目。
贴近生活,尤其贴近诗人本人的生活,是这本诗集的特点之一。任立诞生于1967年,是文化大革命全国性灾难发生的第二年,也是他父亲致残家庭灾难发生的第二年。说起来不信,我与任立第一次见面向他打听的一个人,竟然就是他的父亲。他父亲在山师中文系上学时比我低一年级,我知道他,是因为系里曾成功地演出曹禺的话剧《雷雨》,他是话剧团的团长、艺术总监。演出前在幕前讲过话,后来反右时被打成右派。听说文革开始不久,他就挨斗,被迫跳井自杀,同班同学都认为他死了。是我从任立那儿了解了真相,告诉他们,任文浩还活着,不过致残了。《让我想想》一诗写到他父亲的悲惨命运,这就是父辈的遭遇留在下辈心里挥之不去的痛,说他生于苦难长于苦难,毫不为过。他就是在历史罪孽的阴影下成长起来的,过早地感受到世态的炎冷,从小没少遭人冷眼白眼。“我也曾经在无数个人生的冬季 / 遭到雪雨的戕戮和压折”(《一根麦秸躺在马路上》),“我就像生活中的红对联纸条 / 被一点胶水粘着在风中飘荡”(《飘荡的红对联纸条》),这种在另册家庭过日子的孤寂冷漠感觉,旁人是体会不到的。从被疏远被遗弃处境中体会最真切、表达最概括的大概就是那首《我有一种被地球摔出去的感觉》一诗了,“摔出去 / 摔出去 / 摔出去我才知道被摔出去的感觉”。不是诗人喜欢抱怨,而是历史透过被它伤害的第二代人的命运在诗中悲悯叹息。正是父辈的遭遇成就了他一生不离郯地的宿命,甚至,他因生计艰困而中断了山东艺术学院的学业,只能在当地酒厂就业,为了生计附带着做点小生意。为此,他得背着大包小包挤火车、住客栈,孤寂于异地他乡,嘈杂于批发市场。在《去E城谋生》、《我躺在昆山的草坪上》、《北京的六月》、《人们像蚂蚁蜗牛一样生活着》等诗中,对这种奔波劳顿的底层辛苦生活有着真实细致的描述。现实的生存压力并不比历史的心灵负担轻松。因此,他对郯城的感情是复杂的,既因生于斯长于斯而感到亲切留恋,“我舍不得离开这个散发着乡村风情的小城”(《这是我的家》),“家乡的每一样东西 / 我都喜欢离它那么近”(《我喜欢离那么近》);又感到它的空间过于狭小,“捆住了我欲飞的翅膀”(《让我想想》),“我在郯城的天空下无法飞翔”(《小郯城》)。矛盾的心情交织在他心头,他说:“在苍凉的郯地的白云上写诗 / 我写下第一句是爱 / 第二句是恨”(《我在一朵白云上写诗》)。这就是我们在这本诗集中读到的郯城,这就是我们在这个小县城里结识的一段真实人生。它由于还残留着历史冷酷的脚印而不能不沉重,它因为要在喧嚣纷争的现实中谋生存求发展而不能不沉重。面对这样的人生,你会不由自主地掩卷深思,深思那段残酷斗争的无情历史,深思当下物欲泛滥的满目荒芜。
浪漫是这本诗集的又一特点,现实无情诗有情,生活沉重思轻盈。身体虽然踯躅于郯地,灵魂却可以翱翔于天空。这也就是任立钟情于诗,几十年来不离不弃的原因。“因为在郯城这片荒凉的大地 / 除了面对诗歌,我很孤独”(《我给小树打手机》),诗给了他温暖,给了他安慰,给了他浪漫的想象,给了他梦寐以求的爱情。有一首诗写得很像童话,那就是《一把琴靠在小树上》,诗分两段,第一段写谁相信将一把琴靠在一棵小树上,树就会唱歌,“它细细的枝条,薄嫩的叶子 / 又有多少激情多少力量”。第二段写“一把琴靠在一棵小树上 / 我真的听见了小树在歌唱”,小树还把推撞它的风和打击他的雨当作朋友,邀请小鸟、白云、小孩和它一起唱,“歌唱四季,歌唱自然,歌唱大地……”,于是谁都相信它会歌唱了。诗的结尾说:“如果这把琴靠在我身上 / 我也会将生命之歌奏响”。“琴”代表一种机遇,从不相信小树会唱歌到相信,既是机遇的赐予,也是潜力的发掘,不给人表现的机会,怎么知道人家不行呢?“小树”则是自况,它不仅用歌声证明自己能唱,还邀请大家一起唱,包括打击过它的风风雨雨。这种和谐的关系和情景也正是诗人的理想追求。对于未来,诗人是满怀希望的。诗集中有些诗,一看题目就阳光灿烂,如《黎明是怎么来的》、《迎向太阳》、《我是一只想飞的鸟》《给我一个窗口》、《春天真的就这样来临》等等。诗人向往纯净的生活,生活却并不纯净,怎么办?诗人的想法是要“过滤”,要“砍去”。所谓“过滤”,就是要“像一位诗人 / 梦想着最最干净的爱情干净的思想干净的精神 / 筛去金钱、权力、地位等世俗的杂质……”(《过滤》);所谓“砍去”,就是要“做些斧子砍去 / 砍去生命的癌 ……/ 砍去世俗,砍去堕落与卑劣 / 世界干净了谁都会写出一首美好的诗歌”(《做些斧子砍去》)。“过滤”是对自我而言的,是自我的自洁行为;“砍去”则要有鉄肩担道义的精神,敢于向邪恶宣战。和谐的环境、美好的社会是要人人自觉去维护,去争取的。诗集给予人们的正是这种自信和理想,有了它们,就等于有了心灵的翅膀,既能肩负沉重,又能超越沉重,可以翱翔于诗的天空,在那里自由地飞来飞去。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在诗集中虽然感受到历史和现实加给个人命运的沉重,却并不因此就悲观绝望的原因。我们看到风雨如磐之下升起的是生命的昂扬。诗集中还有不少诗篇是写亲情、友情、爱情的,都是美好真情的自然流露,使读者在动情之余暗想,原来“野孩子”的内心也有儿女情长柔痴缠绵的一面。
诗集中多数诗篇是用赋的铺叙手法写的,往往抓住一个中心句,反复吟诵,排比式的铺展开去,让人感觉犹如大海汹涌的波浪。这样写比较畅快自由,可以不受格律规矩限制,直抒胸臆,又回肠荡气,倾情尽意地表达心中所思所念:一种壮美,一种柔美。但如果缺乏节制,就会使结构显的松散,也会被排浪般的句式淹没。诗的手法还是以更加多样化为好,赋、比、兴都要有一点。构思的时候,除了发散式思维,还要有整合式思维,做到张弛有度,收放自如。即使是自由诗,语言的乐感也是不能不讲的。这都是今后写诗时可以注意不断改进的地方。既然决定干一辈子写诗的活了,总希望把它干得越来越好,越来越精彩,是吗?有改进的余地,就有了对未来的期待,我们期待这一本诗集能给大家一个新的惊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