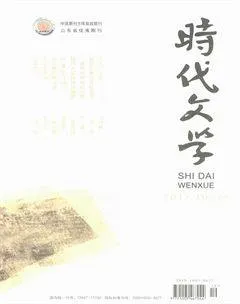春祭
一
我的姥姥,路过那年春天时,不小心跌倒了。她留在了十多年前的四月天里,再也没能走出来。
那个晴朗的上午,过往的邻居们发现,姥姥安静地睡在了门前的杏花树下。她的手里紧紧攥着姥爷的一件灰布长衫。纷纷扬扬落下的杏花瓣儿,像一搭粉白的罗裳,忽闪忽闪地盖在她的身上。
正在做针线活儿的姥姥,就这样无声无息地离开了尘世。她怎么就这么舍得撒手呢?她挚爱一生的老伴,正在田间翻土耕耘,播种希望;她牵挂一生的儿女,正在单位工作忙碌,积极上进。她还没来得及看他们最后一眼。
可是,春风不问世间情。它像带走一朵凋零的杏花一样,从杏树的脚下带走了她。
我跌跌撞撞地跑去看她,觉得身子在半空中悬浮着,像眼前四处飘飞的柳絮。我恍恍惚惚地想着,那个最疼爱我的人不在了,那个我最热爱的人不在了。我一路走一路哭。从此,那个春天,好似一枚毒刺,深深地扎进了我的心窝,让我疼痛得难以呼吸。多少年了,我都不敢伸出颤悠悠的手去触摸一下,我怕碰到姥姥那凉飕飕的月光样苍白的脸。
她是个太有主张的女子,一向做得了自己命运的主。从小时候坚决抵制母亲给她缠足,到碧玉年华时的自主婚姻,再到堂前儿女成群,她为他们搭好了人生的戏台,设计好了精彩的剧本。日子像老屋里的磨盘一样步步辗过,她总有本事把生活的主动权,牢牢地攥在自己的手心。但唯独生老病死,她做不了主,上苍夺了她的权。在她生命的第七十五个春天,在万物勃发的美丽春日,她突然停止了生机。
那天早上,她一如既往地陪老伴吃了早餐,目送他去田间劳作,随后她欢喜地坐在楸木的梳妆台前,把自己妆扮得整整齐齐干干净净。却没料想自此人去镜空,荒了烟云。
她把所有的爱和暖,都给了这个人世。自己却什么也没留,就那么冰凉地走了。
时间是神奇的巫师。它让姥姥的一生,变得既平凡也不平凡。平凡,源于她是中国无数个普通劳动妇女中的一员;不平凡,是因了爱情,她坦然完成由一位富家小姐到乡村农妇的角色转换,并在此后漫长的岁月中,用她的勤俭和智慧,改写了一个家族的历史,成为将军的母亲。她的一辈子,微小如尘,但我不知,是否也伟岸如山?
我所知的,是母爱可以高比山峰、宽如海洋、灿若星辰。中华民族五千年的文明发展史,也是一部悠长的传承与绵延母性光辉的历史。
二
开春,三月天。暖洋洋的太阳,照在胶东莺飞草长的河堤岸上。
孙家有女初长成。十三岁的姥姥,穿着粉嫩的绸缎夹袄,一对黑油油的长辫梢上,扎着两只水蓝的蝴蝶结。她清澈的眼睛,望向空中,纸鸢在天上攀升着。她张开臂膀,追赶着,跟她发上的两只蝴蝶一起,在风中自由地飞舞着。
她是快乐的。脸上的笑,像春光一样明媚。
她是大家闺秀。她的家族,在当地颇有名望。她的太祖父,曾在朝中任三品官。家中有良田万顷,房屋千余间,经营着“三富堂”字号的绸缎庄、粮店和染坊。
为何取名三富堂?年幼的姥姥,并不知晓。许是隐着宿命的端倪吧。就在当年黄叶飘零的秋日夜晚,她嗜赌成性的父亲,终把祖宗留下的店铺和田地,输得一干二净了。他无颜面对妻儿,偷偷跑去了关东。
Hrmwo9YoH0HcezyKw6AvQw==幸而居住的宅子还在,不至于使她们母女流离失所。她的三个姐姐,那时都已出嫁了。小小的姥姥隔着门缝,看到年轻的母亲,发髻凌乱,泪流满面。娇生惯养的她,忽然一夜之间长大了。她对母亲说,不想去私塾读书了,她要跟她学女红。心灵手巧的她,吃苦耐劳,很快便能做出漂亮的衣衫,盘出精美的扣子。母亲在镇上开了一家裁缝铺,小小年纪的她,开始用羸弱的肩膀,帮母亲挑起生活的重担。一年后,她的父亲回家了。日子又渐渐殷实起来。但伤了元气的门庭,再也难现昔日光彩了。
一晃儿,姥姥十九岁了,出落成如花似玉的大姑娘了。眩目的青春华彩,让她美得晃眼。她是真的美。周围十里八乡,没人不说她美:瓜子粉面,柳叶娥眉;一双大而亮的黑眸子,游动在好看的双眼皮眼窝里;不高不矮的窈窕身材,行走如风吹绿柳。保媒的踏破了门槛,都是受当地名门望族的少爷所托。但姥姥不肯点头。她在等一个人来提亲,正是我一表人才的姥爷。
姥爷长姥姥三岁。生于老实本分的庄户人家,是家中独子。勤劳能干的他,每逢集日,便会起早赶到六里外的镇上去卖席子。姥爷是做席子的高手,他把长成的高梁秸剖开后,按所需宽度破成篾子,放入河水中浸泡数日后捞出,将里瓤刮净展平,铺在地上一寸寸手工编织而成。成后再用硫磺熏好,色泽白润光洁。这门手艺,姥爷坚持做了几十年,在我童年时还亲眼见识过。他编出的席子,又软又结实,铺在火炕上舒适耐用,销路极好。每次卖不完的席子,姥爷都会捆起放在姥姥家临街的厢房里寄存——姥姥的父亲心善,他常在街头把长袍马褂兜起,买满满一兜瓜果回家,半路上每遇到一个孩子,不管相不相识,便会分给人家一个,结果到家后总是两手空空,自家孩子一个也捞不着吃,因而他同意免费给这个年轻人提供方便也就不足为奇了。姥姥捅破了雕花木窗上的窗户纸,看到了这个高大英俊的青年,怦然心动,一张俏脸倏地开遍了桃花。但她有着闺秀的矜持劲儿,始终未踏出房门见他。她的梦里,却开始有了他英俊潇洒的面容,清幽幽地散发着春天的香味儿。有一次,口渴的姥爷进屋讨杯水喝,忽然瞧见了貌如天仙的姥姥,他听到了心中春雷轰隆隆炸响的声音。
忠厚老实的姥爷,这辈子干得最漂亮的事儿,就是壮着胆儿去孙家说媒。他甚至没来得及想过,那么金贵的小姐,自己能否养得起。好在姥姥干脆地应允了。尽管她的父母一力阻拦,说她放下那么多门当户对的公子哥儿不挑,偏生看中这么个穷小子。但他们也熟知女儿执拗的性子,索性就由着她吧。她的父亲气恼地说,今后你家里揭不开锅,可别回来求爹娘。姥姥也硬邦邦地撂下一句话:吃苦受累我担着,绝不回家烦爹娘。
迎亲的锣鼓喧天,姥姥身穿自个做的大红绸缎的嫁衣,颤悠悠地坐在花轿里,从娘家到夫家六里长的沿途,挤满了看新娘的人们。大家奔走相告:孙老爷家的四小姐,嫁给老陈家的大小子了。威武的姥爷骑着高头大马走在前面。那种盛大的场面,让今天的我想起来,都禁不住会笑弯了嘴巴。
从那时起,陈家鲜活的家族史,被姥姥用双手平稳地接住了。此后,她用纤巧的双手,一步步引领陈家,走出世代务农的历史。
三
夏日清晨,点点火红的朝霞,栖落在这个温馨的农家院落里。
已为人妇的姥姥,小心地把婆婆搀扶到门口的青石板上坐定。然后把一瓶水,轻轻地放入她的手中。回头叮嘱完公公后,这才放心地扛起锄头,跟随丈夫去锄无边无际庄稼地里的草。
婚后的姥姥,脱去从前的软缎衣裳,换上粗布青衫,把溜光水滑的齐腰长发盘起,利落地挽成发髻。不摆半点娇小姐的谱儿。她持家有方,勤俭度日,井井有条。
她的公公患有气管炎,胸腔里终日响着沉闷的胡琴声,做不了活计。婆婆在生下唯一的儿子坐月子时,落下了眼疾,年纪轻轻便失明了。山上还有好几亩土地,等着春种秋收。里里外外,一大摊子事,晃晃悠悠地搭在了姥姥身上。姥姥每日起早贪黑,外随丈夫种田锄地收割,很快锻炼成精通农活的一把好手;内里伺候公婆,涮洗缝补,妥贴地料理着屋檐下清寒的日子。
姥爷曾对我说过,姥姥当年孝顺公婆是出名的,从没跟公婆红过脸儿。邻里无不交口称羡。每顿饭菜上桌,姥姥都会把好吃的先拣给公婆,然后是丈夫,最后才轮到自己。晚上为公公煎草药,给婆婆洗脚,把婆婆长长的缠脚布洗净晾干。她愉快地做着这些活,脸上总是笑盈盈的,从不抱怨。在她看来,能与意中人厮守相伴,再苦再累的日子也是有滋有味的。姥姥称姥爷“掌柜的”,而姥爷称姥姥“内当家的”,他们一辈子相敬如宾,几乎没吵过架。
院角墙上的青苔,绿了黄了枯了,枯了黄了绿了。在一段段伸展的时光中,孩子们一个接一个,陆续出生了。昏黄的煤油灯下,又多了姥姥低头为孩子们拆拆缝缝做衣服鞋帽的疲惫身影。
姥姥用她精明的头脑,谋划了农闲时贩卖海鱼的生财之道。那时,孩子们已能接替父母,学会照顾爷爷奶奶。每天天不亮,夫妻俩便早早地起身拾掇,姥姥负责在家卖鱼,姥爷则推着独轮车去烟台海边拉鱼,来回二百多里路,全靠用腿和脚一步步丈量。卖剩下的鱼,便下锅给老人孩子改善生活。姥姥是开明的,待儿子和女儿不偏不倚,从不重男轻女,每个孩子碗里均匀地分配一块雪白的鱼肉,她和姥爷吃鱼头。据说吃鱼会启人心智,她养育的孩子们,果然个个聪明伶俐。
在姥姥的精打细算下,勤劳致富的生活,犹如芝麻开花节节高。匣子里叮当作响的钱币,滚来滚去,滚雪球一样扩大厚实起来。姥姥用辛苦挣下的血汗钱,翻新了旧屋,并添置了六十多亩田地。粮囤里堆积的粮食齐屋高。后来,时代风云变换,姥姥主张把大部分土地捐了出去,家中只余几亩薄田。日子又回到了起点。
为了贴补家用,姥姥曾变卖了几乎全部的嫁妆。但那张老红的楸木梳妆台,无论如何是舍不得卖的。她用手抚摸着雕凤刻牡丹的妆台,那里收藏着一个女子深埋在心底的富贵繁华梦,照过她春花般明丽的欢颜——这一世,姥姥在陈家所有悲欢离合、起起落落的日子,都在它的上面静静地过着。
从二十二岁至四十二岁,二十年的岁月里,姥姥就像一棵开不累的花树,一茬一茬,顽强地孕育出五男三女八个花骨朵,她不遗余力地输出养分,供养着他们。其中的七朵,健康平安地打开花苞舒展着,长大成人并成才。只有她的三子福臣,在六岁时夭折了,这成了她刻骨铭心的痛楚。直到晚年,姥姥仍泪水涟涟地跟我提起此事:福臣格外乖巧懂事,小小年纪便会给母亲捶背解乏。平时跟哥哥姐姐学字,已识得很多字了。在他五岁那年,有个算命先生在街上碰到他,端详半天,对姥姥说:你家福祉担不住这孩子,这孩子如果活下来,那是个了不得的人物。姥姥打一激灵,但她压根不愿相信。转过年来,福臣便患上了肺炎,整日里咳个不停,头无力地耷拉在门槛上,娇嫩的小脸憋得通红。姥姥心如刀割,抱着儿子求医问药,晚上整夜地合不上眼,替他理胸顺气。但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初的乡村,医疗条件和医学知识有限,福臣还是没有留住。痛彻肺腑的姥姥姥爷,把幼小的儿子用谷秸编的席子包起来,埋在村北的坟茔里。两人几乎每天都会到儿子的坟前看看,给他培培土,生怕被野狗刨出来。说到这里,姥姥总会擦擦眼泪,长叹一声:唉,要搁现在,打几针青霉素就能救了他的命。
五十年代末,我现在的三舅出生了。长得眉清目秀,酷似福臣。姥姥把对福臣的思念,倾注到三舅身上。她悉心教育三舅,对他寄予了很高的期望。后来,三舅果真成了共和国二十一世纪的将军。只可惜,姥姥没有坚持到那一天。
四
秋天黄昏的斜阳,染红了麦秸棚上吊着的一个个淡黄的葫芦和一串串金黄的玉米。
孩子们乐呵呵地把一群群欢实叫嚷着的鸡鸭鹅,赶进了窝里。在散去的一缕缕炊烟中,忙活了一天的姥姥,才能插空坐下,欣喜地看着儿女们嬉戏玩闹着。
识文断字的姥姥,有着远胜普通农妇的见识胸襟。她从书本中,读到外面精彩的大千世界。她暗自思忖:一定要让孩子们学好知识,从乡村里走出去,摸一摸、闯一闯外面广阔的天地。于是她对姥爷说,无论多难,也要供孩子们上学读书。她省吃俭用,把鸡鸭鹅产下的蛋和地里的新鲜蔬菜瓜果,都拿到集市上卖掉,用作孩子们的学费。她一再告诫子女,知识改变命运。一定要好好读书,开阔视野,到外面的世界发展壮大,有所作为。
当邻居的孩子们在帮父母做农活的当儿,姥姥的孩子们,却端正地坐在镇上的学堂里,认真地听老师讲课学习。
我的大舅,孩提时淘得出奇:上房揭瓦,飞檐走壁,无所不能。能创出各种玩的花样儿,但就是不喜读书,经常被姥姥押送着去上学。有一天,贪玩的他,趁身后的母亲没注意,撒腿就往高梁地里跑。阳光照在秋收后光秃秃的田野里,一大一小两个人影在呼啸的风中疾速地奔跑着。大舅的鞋子跑丢了,被锋利的高梁秸茬扎破了脚,鲜红的血滴滴答答掉在土里。他再也跑不动了,一屁股坐下来。气喘吁吁的姥姥抓住他,本想结结实实地揍他一顿,但瞧着他红扑扑的小脸,又舍不得下手。姥姥一边替儿子包扎着伤口一边问,你为什么要逃学?儿子说,昨个看到树上有只鸟蛋,今儿想去看看变成了小鸟没。姥姥又问,你为什么喜欢小鸟?儿子的眼睛突然放出兴奋的异彩:因为小鸟有翅膀,能飞得又高又远呀。姥姥摸着儿子柔软的头发说,孩子,只要你好好上学读书,就会像鸟儿一样长出翅膀,将来也会飞得很高很远——大舅扑闪着大眼睛,信了姥姥的话。为了能像鸟儿一样长出一双飞翔的翅膀,他开始用功学习,成绩优异。成年后他做了老师,成了一名优秀的校长。也终于明白了姥姥当年的苦心。
姥姥非常注重对子女们的思想启蒙。她教孩子们认的第一个字,是“正”字。她对孩子们说,正,就是正直,正派,正气。就是要堂堂正正地做人,端端正正地处世。只有行得正坐得正,遵纪律,守规矩,才能做一个有益于国家和社会的人。她为子女们规划了两个发展方向:一是老师,教书育人;二是从军,保家卫国。沿着这两条路子,她的七个孩子,全部跳出了农门,按当地的说法,就是都吃了公家粮。三个女儿和大儿子小儿子都成为了光荣的人民教师,三舅则参了军。姥姥又做主把三个女儿都嫁给了军人。只有二舅算是另类,他上学时被一家大企业挑中,后来走上了副厂长的领导岗位。
重教和拥军,当我撩开岁月撒下的烟尘,重新打量姥姥的眼界时,不禁感叹:姥姥一个小妇人,竟有着如此令人敬重的社会责任感。
早在解放战争时期,姥姥便是拥军模范。她曾带领村里的姐妹们扭着大秧歌,迎接解放军进村。她带头纳鞋底,做军鞋,用麦秸做扇子,慰问亲人解放军。她还积极动员丈夫支前。姥爷曾在弹火纷飞的战场上,用他魁梧壮实的身躯,推着小车,为部队运输物资。并抬过担架,救过伤员,也是一条为解放事业出过力的热血汉子。
姥姥对解放军的爱戴,是自觉自愿的。她感激,是共产党的政府,替她主持了公道。那是土改前,姥姥家的土地与村干部家紧挨在一起,村干部偷偷挪动了分界石,多占了姥姥家的土地。姥爷唉声叹气地说,算了,忍了吧。姥姥并不作声。第二天一早,干净利落的姥姥,顶着白花花的阳光,步行十里路,到了区政府驻地。进屋后,姥姥擦擦汗,不亢不卑地问区长:“这人民的政府,是不是为人民做主?”区长惊奇地打量着这位年轻勇敢的妇人,点头说是。姥姥理直气壮地把事情的原委一一道MYEXi8WQ9o2S8NFlpU2uSw==来。次日,区长便派人用弓重新量了土地,把村干部侵占的三分地还给了姥姥。
事后,姥姥教育孩子们说,做人一定要挺起脊梁,活得有尊严。过分的忍让,不是美德,是懦弱。姥姥是有着大丈夫气概的。
五
覆盖在皑皑白雪下的冬季村庄,鸡不叫,狗不吠,分外静谧。
路上的积雪,闪着银白的亮光,如同姥姥头上的发丝。年过花甲的姥姥,拉着我的小手,送我去上学。
我的童年,是捧在姥姥手心里的。依着姥姥的呵护和宠爱,我的童年快活得跟天上的仙女似的。
我有时会抱怨,姥姥的血脉,到我这里拐了两个弯,我只继承了她的四分之一。
我的母亲,是姥姥的长女。我六岁时,父亲从广州换防到昆明,母亲一人带我很吃力,便把我送回了姥姥家。姥姥见到在南方水土里养得面黄肌瘦的我时,心疼地把我搂在怀里说,天可怜见的,长得跟绿豆芽一样——那时,姥姥的儿女都已长大外出了,家境也很好了,在村里是数一数二的人家。从此,姥姥几乎把全部心思都用在如何调理我健康成长上面。
整日里喜鹊般叽叽喳喳绕在姥姥膝下的我,其实更像是姥姥的小女儿。
为了让我长胖,姥姥每天清晨,会在旺旺的灶火上放一把大铁勺,等勺子热了,便往里倒一点花生油,再砰地打一个鸡蛋进去,然后来回掂着在里面嘶嘶乱叫的黄橙橙的蛋饼。我总会在满屋飘散的蛋香味里醒来,美美地吃下香喷喷的煎蛋。
姥姥还会蒸满锅的地瓜和玉米面饼子给我吃。她说,粗粮最养人。于是我吃一口甜得流油的地瓜,再吃一口黄灿灿的玉米面饼子,就着姥姥配的小咸鱼和绿油油的青菜,把肚子撑得滚瓜溜圆。姥姥还在南屋挂个柳条篮子,里面总放着为我准备的好吃的点心、水果和奶糖。过不多久,我就像姥姥伺弄的地里庄稼一样,长得又肥又壮,脸胖得跟小盆似的。
有了充足的体力,我开始不省心地动脑琢磨玩耍的歪点子。有一天,我翻着姥姥做针线的笸箩,灵光忽现,心想把姥姥的线穗用火点着,定是很好玩的。于是我立马付诸行动了。但线穗并没如预想中的那样熊熊燃烧火光冲天,只是温温吞吞地闪着点火星冒着点青烟。正在我沮丧的当儿,姥姥从外面推门进来了。惊慌失措的我,一下子蹿到炕上,把线穗儿掖进了被垛里,想着这样就不会被姥姥发现和责怪了。我笑嘻嘻地跟着姥姥进了南屋,看姥姥用簸箕簸麦子。姥姥忽扇忽扇地把小麦一下下扬起,那些夹在里面的浮糠草屑便飘走了。我正看得入神,忽听姥姥惊叫着跳起来:北屋炕上怎么了?怎么出来这么大的烟味儿?姥姥快速冲过去,我也颠颠尾随着。只见炕上浓烟滚滚,成撂的被子被点燃了。懵懂的我,这才回过味是自己干的糟糕事儿,吓得七魂出窍,趁姥姥泼水灭火的空儿,偷偷地溜出门去。我在街上晃悠了一上午,看猫看狗看树看草,直到肚子饿得咕咕叫,不得已才硬着头皮回家去。我灰溜溜地跨进家门,本以为等着我的是姥姥的训斥和拳头,没想到却是姥姥端出的热呼呼的饭菜。待我狼吞虎咽地吃饱后,姥姥才开始对我说:孩子,水火无情,火是玩不得的。幸亏发现得及时,要不把咱家烧光了,咱去哪里住呢?你记住,玩火是坏孩子做的事儿,是很危险的,会给人带来灾难和祸事,以后千万不能再玩火了!——看我认错态度良好一个劲地点头,姥姥还发了两个甜瓜来安慰我。似乎是我做了什么好事值得奖赏似的。
老天,我怎么有这么个宽宏大量而又循循善诱的姥姥!从那时起,我牢牢记住了姥姥的话,在人生路上,努力做个“不玩火”的好人。
姥姥植下的花草,总是比别家长得茂盛。我奇怪地问她原因。她说,善良的人,养的花草自然长得好。我信。因为姥姥正有一颗慈悲的心。
好多次,我都跟随姥姥去给街上乞讨的人送衣服和饭食。有时,叫花子身上的衣服破了,姥姥还会吩咐我回家取针线笸箩。人家坐在石板上吃饭,姥姥则在旁边帮人家缝补衣服。那一刻,慈眉善目的姥姥美极了,就像年画里的观音菩萨。而我端着笸箩骄傲地挺着胸脯,觉得自己就是菩萨身边的侍童。
有一年腊月,滴水成冰。生产队里的老牛产下了一只小牛。被寒冷冻坏的小牛起不了身,看热闹的人们哄笑着散去了。只有姥姥不忍心,她把毛茸茸的小牛抱在怀里回了家。她用被子把小牛包起来,放在暖炕上,救活了一个小生灵。
姥姥总是乐于助人。谁家有喜事,手巧的姥姥,都会去帮助做大花饽饽和剪窗花。姥姥做的大花饽饽,不仅好吃,更好看,上面捏的花儿朵儿水灵灵地活着似的;姥姥剪窗花的技艺更是一绝,不需事先描画绘图,拿起剪刀几下子就能剪出花鸟鱼虫等各式花样来。我最喜欢姥姥剪出的一溜红彤彤的小孩儿,手拉手憨厚地笑着。把他们贴到窗户纸上,梦里都会听到他们嘻嘻哈哈的笑声。
姥姥还是村里的义务调解员。说不清帮助多少邻里解决了夫妻、婆媳、兄弟、妯娌之间的纷争。
姥姥的言传身教,潜移默化地渗入我幼小的心灵,并长远地影响着我的做人处世方式。直到我十二岁时,被父母接回身边,依依不舍地离开了姥姥。每当我做错事,父亲扬起巴掌要打我的时候,我便大叫着:姥姥,姥姥——父亲就会泄气地放下手来。
姥姥是我永远的护身符。
六
寂寞的老屋,透出经年的荒凉。
我嗅着,姥姥遗在这里的气息。我摸着老屋富有纹理的肌肤,看着姥姥鲜活美丽的容颜,在时光中渐渐干枯成墙上的一帧帧老照片。
姥姥踏上古稀的台阶后,一向健康硬朗的身体,开始摇摇晃晃,走下坡路了。
母亲说,姥姥青壮年时操劳过度,年老时就找补上了。姥姥生下母亲的第三天,就上山干农活了。她从没正儿八经地坐过一个像样的月子。
她七十一岁时,积劳成疾,突发轻微的血栓住院。幸好抢救及时,没留下任何后遗症。但精气神已大不如从前。就在姥姥离世的前两天,我去看望她,帮她清洗衣衫讲卫生时,她还像以前一样,从柳条篮子里取出为我备下的好吃的。慈祥的姥姥,仍一如往昔地微笑着。
我以为,姥姥可以永远安然地这样微笑着,给后辈们一个回报她的机会。但没料到,她竟如此仓促地被光阴收走了。
光阴仿佛一朵木槿花,早晨开,黄昏落,一晃眼,一辈子过去了。
姥姥的一辈子,如同一只辛勤的老茧,为儿女们能化成光明磊落的蝴蝶,孜孜不倦地奉献着,到最后只剩下了一具空壳。
她集勤劳、善良、坚韧、贤淑、俭朴和忠贞等美德于一身。我想,她只是那个年代众多母亲们的一个缩影。她们含辛茹苦,任劳任怨,为家和国培育出有用之材。正是这些看似寻常渺小的母亲们,用一副副臂膀,汇成一股巨大的力量,撑起了二十世纪的半边天,并与他们的儿女站在一起,推动着时代浩荡的进程。
我听到了一声轻叹,婉转,悠扬,那是我熟稔的她的声音。其实,姥姥一直住在我的心里。我时常能听到她在我心中走来走去的声响。
在她离世的第十个年头,她恩爱一生的老伴,也去那端陪她了。
两年后,她的三儿子,不负她望,晋升为少将。可惜将军的母亲,没有看到儿子的荣光,没亲手抚过他肩上金光熠熠的军阶。
姥姥姥爷合葬的坟前,树木苍翠欲滴,迎春花朵怒放。她的将军儿子和大校儿媳,长跪不起。他手抚石碑,低低地与母亲说着悄悄话。泪水从他的眼眶悄然溢出。或许他想起了当年母亲送身披大红花的他去参军时伫立在村头久久不归的身影,或许他想起他从基层的通讯员做起,一路拼搏而来,从考入普通军事院校,再到研修于国防大学,他从没松懈过学习的姿态,是母亲殷切的嘱托一直支撑着他奋力进取。他用树枝在地上写了一行诗:知有慈母无路入,马前惆怅一枝春。
戎马倥偬的将军,为母亲骤然从春天的枝头坠落而黯然神伤。他知道,母亲替他选了从军这条路,便注定忠孝不能两全。他履行着保家卫国的神圣职责,却没能保住自己的母亲。他也知道,母亲是不会怪罪他的。因为母亲常在书信中教导他:大家远比小家重要。
满阶芳草绿,一片杏花香。我亲爱的姥姥,春天又来了,杏花开遍了山野。我多想回到那个春天,守在你的身旁,轻轻地为你梳理满头白发,给你扎一根红头绳;柔柔地用温水为你洗一洗脚,小心剪去你多余的指甲;又或者,给你讲老旧的故事,给你唱好听的戏曲,我可以为你做任何事儿,只要你高兴;我多想把你给我的爱和暖,虔诚地捧在胸口,一点一点还给你;我多想牵着你的手,扯住你的衣襟不放,不许你在春天里跌倒,让你怀抱尘世安暖,笑眯眯地赏遍姹紫嫣红、无边春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