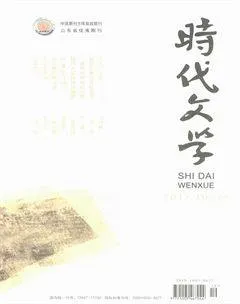雨中过黄河
临近黄河正落细雨,汽车沿着湿滑的坡道一鼓作气奔到大堤之上,我猛然收紧的心又突然放开,全没了一路上的昏昏沉沉。居高临下的瞬间一瞥,顿觉天低云暗,伸手可触,河宽水阔,近在咫尺。烟雨迷蒙里,大河上下满目苍黄,浮桥穿越天险,拉近了两岸的距离,过往车辆甲壳虫似的缓缓移动,就想我若在其中,也只能是一点影子,也许这一点影子也模糊不清。
河流有各自的特色看点,不同的河段也会尽显差异。黄河挟泥带沙一路奔腾,进入下游,收敛了龙腾虎跃排山倒海的气势,河面渐宽,水流平缓,一派祥和,然而,你仔细观察,在温驯不燥的表面下涌动的激流暗伏玄机,令人不安。我曾无数次在黄河上往返,艳阳高照,河是暗黄,烟雨苍茫,便显古铜,流淌的似是一河粘稠的金属液体。与河蜿蜒而行的是铜墙铁壁似的大堤。历史上黄河多次决口改道,祸及民众。1855年6月(清咸丰五年),黄河在河南兰阳铜瓦厢决口,夺大清河流经山东腹地入海,这是黄河最近的一次改道,在人与河的博弈中,便有了这经年累月沿河而筑被誉为长城的大堤,书称堤防。长城为防兵祸,又用来绝水患,可见兵祸水患同为人类大敌。黄河的桀骜不驯、暴戾无常,两岸堤防的厚重憨实、稳如泰山,有自然书写的波澜壮阔,有人类记录的惊天之举。黄河下游的河与堤是一幅瑰丽雄浑庄严深沉的完整画卷,美在其中,缺一不可。
喜欢河或许是人的天性,对我来说,还和读书有关。我热衷于身临其境,无论大河小河,天然河人工河,如果有机会便想去看看。我也醉心于阅读文字上的河,作家诗人们把过多的感情倾注到对河流的描绘上,笔下有着感人的魅力和无限的想象空间,即使一些地理历史方面的书涉及河流的叙述,也难掩文人们的冲动,自觉或不自觉染上文学色彩。读过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曾为他描绘的顿河风光折服。他笔下的顿河,哥萨克男人英俊剽悍,女人美丽善良,在时代风云的激荡中,他们的命运如顿河水一样,时涨时落,时急时缓,充满了传奇色彩。自然与人的完美结合,真正进入到情景交融、出神入化的天地。顿河,我注定到不了那个地方,不过没有遗憾,读书同样让我领略了顿河如画的天地。到一个叫枯河的地方,安顿下来就去寻,路人笑我痴,指点一条仅存痕迹的河道,那里的风吹来扬天的沙尘,想到枯河二字,我恍然大悟。后来读清人笔记,看到对枯河的记载,舟楫穿梭往来,号声不绝于耳,入夜渔火点点。我心生疑问,既如此,为什么叫枯河,难道古人为这条河命名时就已知道它后来的命运。
那年去大汶口访古遇暴雨,众流齐汇大汶河,本是乱石裸露荆棘丛生仅有涓涓溪流的河床,一夜间爆满,城门外那条古老的石板桥也不见了踪影。我爬上临河的城墙俯看,河水湍急翻滚,浪涛汹涌激荡,遥看对岸白茫茫一片,想到庄子《秋水》篇里的“百川灌河,流泾之大,两涘渚崖之间,不辨牛马”,更觉是神来之笔。我身后城墙下是有百年历史暮气沉沉的山陕会馆,雨水洗去蒙尘,清新鲜亮了许多,亭台楼阁、雕梁画栋虽已残缺斑驳,但仍能想象得出当年的富丽堂皇和山陕商人的腰缠万贯。会馆中戏台完好,那上面曾演出过风花雪月,也上演过刀光剑影,那里曾响起冲天的锣鼓,就像大河奔流急促紧张的咆哮轰鸣,声震八方。大汶河算不上一条大河,新石器时期大汶口文化遗址的发现,才使大汶河声名远扬。有人说,先有大汶河,后有大汶河人,没有大汶河,就没有新石器时期大汶口文化。说这话的人不会是哲学家或者诗人,我想,一定是位考古家或者历史学家。
少年时,在一个公社驻地的礼堂看过一些电影,有次看的是纪录片《红旗渠》,讲述的是河南林县十万儿女开赴太行山,历经十个春秋,靠一锤一钎一双手,劈山凿洞,架桥修渠2000公里,引漳河水入林县的故事。影片画面上那些手握铁锤钢钎普普通通的人,那些人拉肩扛热火朝天的场景,曾激动的我热血沸腾,并深深嵌进我的记忆。三十多年后,我才有机会亲眼目睹这条盘绕穿行于太行崇山峻岭,被誉为人工天河的天下第一渠——红旗渠。艰难岁月早已流失,当年的建设者们不会想到,他们为生存流血流汗有人甚至付出生命代价修成的渠,如今成了旅游景点,林县人又一次得到实惠。我沿渠游走,无心于青山绿水,仰视高山,似乎又看到人捆绳索悬于山崖峭壁的画面,在游人嘈杂声中有一种声音格外清脆,那是铁锤钢钎与石头的撞击,我不是来旅游,而是在重温少年时看过的一场电影。很庆幸,电影里的故事和人物燃起的激情至今仍没有淡去。红旗渠应该是一条大河,它由千千万万林县人汇聚而成,其精神是愚公移山,其力量势不可挡。同去的一位诗人说,先有林县人,才有红旗渠,有红旗渠,才有红旗渠文化。
我看过的河,大都从书中读过,不管是历史书,还是文学书,是慕名而去,在身临其境中体验感受,有时还有点验证的意思。河流千姿百态,有各自的风光和风情,有各自的历史和传说,美感从中而来,思索也从中得到启发。在泗河源头泉林,我拜谒孔夫子观河碑碣,便想一定是奔流不复的泗河成全了夫子逝者如斯的慨叹;去过沅水辰河,沈从文用生动的笔触写出了河流的恬静柔美,人性的纯朴自然,俨然一个世外桃源;过富春江多看了几眼,就因为郁达夫的一篇散文,我虽不喜欢文中阴郁的格调,但真实的富春江如诗如画;读过孙犁的《风云初记》,去正定看到书中写到的滹沱河已干枯,河美是无处可寻了,想到作家笔下的人情美该不会和滹沱河一样吧。也有扫兴的时候,在南京满心欢喜地去看秦淮河,这个古时风尘女子翘首弄姿,落魄文人借酒消愁之处,风流韵味早已消散,朱自清俞平伯笔下的秦淮河也像他们一样逝去,两岸一片假古董,令人乏味。那日也想去长江边看看,又突然想到六十多年前日寇在此屠杀我无辜同胞的罪行?,有描述,当时是血流成河。我心沉重,江边没有去成,南京这个地方,我也不想再来。
回故乡,走济青路,出济南向东,便有了绣江河、西河、武源河、缁河、维河、胶河、大沽河,还有一些我叫不出名字的小河。西河和武源河相距不远,都已断流荒废,乱石野草荆棘,更显荒凉,然而,西河在新石器时期就有人类居住,武源河边更是龙山文化的发源地,可想当年两河流水四季不断。河流不仅养育了人们,还养育了文化,造就了一代一代的优秀人物,像绣江河源头的李清照,淄河边上的蒲松龄,胶河岸边的莫言等,河上风光无限,令人难以忘怀的还是他的人文历史。
我住的这个地方,北去二十公里,有禹疏九河的漯川古道现今的土骇河,清水汩汩;南望十公里是古四渎之济水现今的黄河,浊流滚滚。两河的滋养使这方成为富庶之地,人们安居乐业,两河的滋润使这方民风朴厚直爽,重大义行善举。值得警惕的是,环境污染水资源匮乏加剧的今天,河流改变着颜色,水质发生着变化,来水逐年减少以致断流干涸,这一切正悄悄地影响着我们的生存和生活方式,模糊着我们的感知和想象,这种影响和模糊的过程往往是在不知不觉中进行的,我的担心,是人精神的退化。人与河息息相关,先人们的“顺其自然”是一种态度,“人定胜天”也是一种思想,最终走向“天人合一”是为上策。
车早已驶过黄河,落雨更加细密,我无法把这些散乱的思绪理清,或许有人问,你想告诉我们什么,我只能说,不知道,还是去河边看看吧,那里有会有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