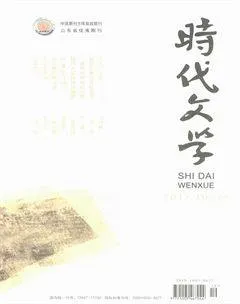老村那眼青石井
太阳还没露脸的时候,通常路上是有雾的。那雾是从村后的山腰上流下来的,看得见摸不着,有水的味道,我便一路闻着走到青石井跟前。
井圈是湿的,井台也是湿的。这不奇怪,老村三四十户人家都在这口井里吃水,每天从鸡鸣啄破天空的时候开始,青石井就像散开的麻团,麻线般的小路牵扯着不同方向来的挑水人。怕是自打有井的的时候就是这样了,多少个年头谁也说不清。你看那井壁,幽幽的青砖泛着黑润,条条块块还生了厚厚的青苔,缀着经年累月。你看那井圈,布满深深浅浅的索痕,像德旺爷眼眶两边的皱纹,饱经沧桑。还有井圈下的青石板,拼接的痕迹已被千万次的踩踏磨得没了缝隙,石面光滑得可以磨刀磨剪。
挑水很累,打水却是件惬意的事。幽深的井底,一眼洞天,伸头窥探,人成了水中倒影,五官清晰。还看得见蓝天,看得见天上流过的云,天有多高,井就有多深。扯着绳索把水桶慢慢放下,手腕一抖,咣当一声,水桶就很听话地倒了个儿,咕咚,灌满了水。三下两下扯到井面,清澈的桶里晃悠着一张笑脸。
第一次打水可没这么潇洒。十五岁的时候,奶奶对我说,男到十五当家汉,别老让你妈挑水,这该是你的活儿了。于是,我就学着母亲的样子,把扁担横在肩上,两只手握着水桶钩,担起水桶就走。可总是这头高来那头低,两个水桶很不安生地和地面磕磕碰碰。到了井台上,邻家的小大姐看着我抿嘴想笑,我知道她笑什么,就不服气地放下水桶,想做出样子让她看看。可是,水桶却不听使唤,先是咣当咣当碰撞井壁,到了水面又老不下沉,装不了水。那井绳软不拉叽的,一点也使不上劲,水桶横漂在井底奈何它不得。小大姐终于笑出声来,说我,书念多了吧,水都不会打。说着,就给我示范。那是我第一次很谦虚地向没念过书的邻家小大姐学习一门技术,站在她旁边,我也第一次感觉她竟是那么漂亮。
我担心奶奶会问我是怎么把水打上来的,幸好她没问。但奶奶却问,你是不是给德旺爷打水了?我说忘了,奶奶说,若是你妈就不会忘的。
德旺爷住在老祠堂里,无儿无女,一大把年纪。原先他是有家室的,早年间因为不愿意为驻扎在这里的日本鬼子做苦力,被打折了腿。鬼子还放火烧了他的房屋,残害了他的家人。从此,德旺爷断了感情的念想,鬼子投降后便一个人住在废弃的祠堂里,青灯古佛,过起清简的日子。老年后身子不方便,就在祠堂门口摆了一个小摊,卖些油盐酱醋之类的小玩意,糊以日月。青石井就在距离祠堂的不远处,井旁长着一棵百日红,瓷盆口粗,我估计,树龄比德旺爷的岁数还要大。小时候我不知道百日红为什么树干上光溜溜的没有树皮,叶子没长出来就开花,而且开得红艳艳,时日长久。是德旺爷告诉我说,为什么这树没有皮?那是日本鬼子用刺刀戳的;为什么这花无叶就开,而且开得艳,开得久?那是青石井里的水滋润了它的根系。我似是懂了。奶奶却说你不懂,多少年来,德旺爷就这么守着青石井,守着百日红,你道为甚?因为德旺爷的媳妇就是被鬼子害死在青石井旁的。奶奶还说,德旺爷的媳妇名字里也有一个“红”字。
母亲挑水时总是先把德旺爷的水缸打满。德旺爷的水缸也不大,只装两桶水。其他人也挑,就看谁占着先。不论谁挑,德旺爷都会说一声谢谢,再送一脸的微笑。而后,就坐在门口的摊子边,远远地看着青石井旁边热闹的场景。
多数时候,青石井旁是有人的,尤其是半晌午的时候。不下田做农活的妇女们总是要聚集在这里洗衣洗菜,或是洗刷什么家具器皿之类的东西。当然,也有顺便去德旺爷摊子上买东西的人。他们一边洗一边闲聊,张家山前李家山后的人情世故,王家庄稼刘家牲畜的长势好坏……说不完的生活琐事,谈不完的陈年老调。人心如井水那般清澈,人脸若百日红那般明艳。青石井就像一汪幽深的眼眶,奉献着自己的明眸,记忆小村淡淡的岁月,照亮人们清贫却有滋有味的日子。
青石井也有紧张的时候。那年干旱,地里的泥土裂得像婴儿嗷嗷待哺的嘴,庄稼苗子稀稀拉拉,奄奄一息。几乎所有的池塘都干涸成泥浆,祈求一场雨成了人们日思夜想的话题。有人开始往德旺爷的住处跑,不是去找德旺爷,是烧香磕头求拜他摆放在祠堂上厅的那尊菩萨。然而,平日不烧香临时抱佛脚是不灵验的,袅袅烟雾变不成天上的雨云。于是,又搭班唱戏,传说里好像有唱戏求雨的故事。那南乡来的刘瞎子,三弦轻弹,慢摇简板,气定神闲,沙哑的声音先唱薛仁贵征西,再唱穆桂英大摆天门阵。可是,怎么唱也请不来雷公菩萨的雨盆盆,怎么唱也唱不来龙王爷的水钵钵,只能心系琴弦,听戏止渴。
德旺爷说,用青石井的水浇苗吧,或许能救活那些庄稼的。于是,所有的人都来到青石井旁,把人打水,把人往地里传送,肩挑手提的人形成了长龙,一直延伸到地里。村里还立下规矩,节约用水,不得用青石井的水洗衣洗菜,吃水也要省着点。然而,青石井毕竟只有那么粗,储水不多,经不住陡然间的大量汲取,不多时,水浅见底了。人们又开始唉声叹气,怨怪这井水怎么如此不经用。德旺爷说,人的筋脉都是要疏通的,要不然血都流得不畅。你们只顾着取水,何时给青石井疏浚过?
洗井?人们恍然大悟。可是,洗井是个技术活,要请专业队的,费用不少,哪来这笔钱呢?大家又泄气了。德旺爷从床底下翻出一沓子大票小票,把自己一生的积攒都拿了出来,对村里领头的人说,快去请洗井专业队!
弱水三千,只需一瓢饮。可是,当这一瓢水都没有的时候,庄稼就不能存活,古语说的没错,瓢水渴死牛。是德旺爷及时的提醒了大家,也是德旺爷慷慨解囊救了老村。
那一年,附近村子因为干旱地里几乎绝收,但我们村子却从干旱的缝隙里抢回了几成庄稼。人们为了感谢德旺爷,秋后在青石井旁立了一块石碑,刻写着德旺爷的功德。
岁月像青石井的水源源不断,我们的年轮也像井圈上的沟痕一日日加深。不知道从哪天起,村子里的人开始陆续外出,一个人的脚印,踩着另一个人的脚印,循环往复。通往城里的路越走越远,向往都市生活的心越跑越大,渐渐地,老村萧条冷落了。德旺爷已经过世,祠堂又复归荒凉,偶尔,有求根寻租的人来这里转上一圈,临走,丢下一声叹息。有野狗野猫出入墙根转拐处,凄惨的鸣叫像是追寻过去有剩饭剩粥的日子。
老井没了德旺爷的守候也少有人光顾,井旁昔日热闹的场景已随风飘散。井台上的野草,终于等到机会从青石板拼接的缝隙里钻了出来,从条条块块蔓延成一片,远远的看,井台像个荒丘。伸头再看井里,井壁的青苔已缀满灰尘,井水平静如冰,油污般的浑浊照不见人的身影,也照不见头顶上的蓝天白云。我不知道,少年窥探的眼神和青年渴望的笑脸是否依旧深锁在井底?我不知道,厚积了老村许多年月的淳风淳俗是否依然游离在青石井的四周?
欣慰的是,那块石碑还在,默默而立,憔若德旺爷清癯的面容。我忽然觉得,青石井变成了德旺爷浑浊的眼睛,凝视着还不曾远走的岁月。
一只灰喜鹊立在百日红的枝丫上向井台张望。看得出,那里是它经常往返的领地。我知道,灰喜鹊离不开这棵百日红,离不开青石井,也离不开老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