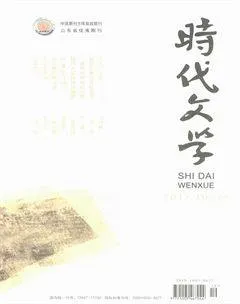蒲松龄与古铜镜
闻名世界的被誉为中国短篇小说之王的蒲松龄(1640-1715),字留仙,一字剑臣,别号柳泉居士,世称聊斋先生,山东省淄博市淄川区洪山镇蒲家庄人。先生19岁应童子试,接连考取县、府、道三个第一,名震一时。补博士弟子员。以后屡试不第,直至71岁时才循例成岁贡生。公元1670年,因家贫不能自给,到江苏宝应县为契友作幕宾,因不惯于官场应酬,不足一年便索然而归,后在淄川县西铺村毕际友家做塾师,舌耕笔耘近40年,直至1709年方撤帐归家。教书之余,他在“柳泉”旁搭棚待客,悬壶送饮,搜集素材,发愤著书,写成了著名的文言文短篇小说集《聊斋志异》。全书共有短篇小说520篇,内容丰富多彩,情节幻异曲折,文笔简练,叙次井然,堪称中国古典文言短篇小说之巅峰。康熙五十四年(1715年)正月,蹇滞一生的蒲松龄病逝,享年76岁。其墓就坐落在淄川蒲家庄东南一里许的小土丘上,封土高约2米。墓前原有1725年(清雍正三年)立的墓表碑。
公元1966年,在那场史无前例的“运动”中,蒲松龄墓碑被砸毁,墓葬被“红卫兵”挖掘。在其少得可怜的随葬品中,有一面铜镜,现珍藏于蒲松龄纪念馆。这面铜镜是蒲松龄生前日常生活中使用的妆奁用具,但不是蒲松龄生活的那个时代铸制的,而是一面古镜。 蒲松龄为什么要使用古镜?这面古镜是什么年代的?蒲松龄这面古镜是怎么得来的? 笔者根据自己的铜镜实物资料和多年收藏研究古铜镜的经验,对照分析蒲松龄的这面古铜镜,结合蒲松龄文集和有关史料,对上述问题作些考证和分析,以共勉于方家。
一
这面古铜镜为圆形,直径8.9厘米,镜面呈微凸状。大扁圆钮(或称大球形钮),钮径2.1厘米。厚宽平缘,缘宽1.5厘米,缘厚0.4厘米。钮孔两端使用痕迹明显,磨损不一,一端磨损严重孔径约0.5厘米,另一端孔径约0.3厘米。 镜背主题纹饰为以钮为中心环绕着高浮雕的的龙虎对峙图案,龙与虎头部之间饰以“五铢”钱纹,下部饰一瑞兽,构成镜背内区。一短线钭纹圈带与高起的缘边将内区和缘区分开。 宽平缘自成一纹饰区带,饰一圈三角锯齿纹和一圈单线水波纹,中间有一细线弦纹相隔。
镜面锈迹通体呈现绿色,有龟背状自然锈纹,锈层较薄,但不浮。镜背铜锈层次纷杂,锈色斑驳,红锈层、绿锈层和亮锈层浑然交融。
二
蒲松龄生于明崇祯十三年(1640),卒于清康熙五十四年(1710)。这个时期,正值在中国历史舞台上存在了几千年的铜镜走向没落的时期。作为日常生活用品的铜镜,既没有别的物品可以取代,也不再是工艺美术的重点,直至清乾隆前后,铜镜最终被更为实用的玻璃镜所取代。 明末清初的铜镜,其时代特点,还是很明显的。这个时期的铜镜,其基本特征是重实用而不尚花纹,纹饰粗略,质地不好。其形制特点是以“圆板具钮”的圆形为主。镜钮为银锭钮,圆柱形平顶钮和小圆形钮,不见大扁圆钮。镜缘都是窄素缘,无装饰。镜背呈现完整平面状,没有凸凹分明的内外装饰区。其纹饰图案虽然延续着历代的传统题材,但风格单调,图案基本为日常生活中常见到的动植物和吉语铭文,是借用假托、转喻和谐音来象征吉祥的。 由于其材质为黄铜质,加之时间短,现在出土的明末清初的铜镜的锈迹都是绿色,少见红斑和亮锈层。 根据铜镜的形制特点和纹饰风格以及对锈迹的比较分析,蒲松龄的这面铜镜不是其生活时代之物。
三
蒲松龄的这面铜镜与东汉末年的铜镜的基本特征相符。 汉代,是中国铜镜史上的辉煌时期,不仅其造型、纹样、技巧和意境风格独特,而且传世铜镜之多,令人瞩目,出土的汉镜更为全国之冠。 东汉中期以后,汉代铜镜获得了重要发展,其题材内容和表现手法一直影响和沿袭到汉末三国乃至魏晋南北朝。东汉末年铜镜的基本特征表现如下: (一)在形制上,圆形厚重的镜体配以扁圆大钮,镜钮占据镜背面积的比例大,并成为装饰内容的一部分。这种扁圆大钮只出现在汉中期以后,以汉末和三国时期最盛。(二)镜背用凸凹的不同平面,分为内装饰区和镜缘装饰区。主题纹饰在内装饰区。(三)在表现手法上采用高浮雕技法,使纹样隆起突出,高低起伏,显得生动自然,视觉效果为半立体状。(四)铜镜边缘为厚宽平缘,并饰以华美的纹样。这种纹样多为锯齿三角纹,单线或双线水波折纹,以及弦纹和钭线纹。三国以后,铜镜边缘开始变为三角缘和窄缘,镜缘从此不再成为装饰带。(五)这个时期的铜镜材质都是高含锡量的青铜。这种青铜质的铜镜,在地下不同的地理环境中埋藏了千余年,出土后呈现的红斑绿锈杂列相间,坚硬自然。亮锈迹根据出土坑口的不同,呈多种亮色,南方多呈黑漆古,北方多呈水银沁。(六)这个时期铜镜的主题纹饰中,神兽(多为青龙、白虎、朱雀、玄武,是古人信奉的四神)题材十分流行,龙虎对峙镜出土和传世的都很多。这个时期,在货币中仍然流通着方口“五铢”钱。在神兽镜中饰以五铢钱纹,是汉末铜镜装饰的重要特征。 综上所述,蒲松龄的这面铜镜与汉末铜镜的基本特征都相同和相似。因此,笔者确认这是一面东汉末年的铜镜。《淄博文物志》及近年出版的《蒲松龄志》将这面铜镜定为北朝时期三角缘神兽镜显然是不正确的。另外,根据《中国铜镜图典》一书所载,经科学发掘出土的铜镜资料也可以佐证: 1、河南省陕县刘家渠东汉后期墓出土一面,圆形,扁圆大钮,直径9.9厘米,宽平缘。高浮雕的龙虎夹钮对峙,头部间饰以五铢钱纹。钭线纹圈带外饰以三角锯齿纹和水波折纹。 2、湖南资兴和四川宜宾东汉晚期墓各出土一面。圆形,扁圆大钮,直径分另为10.6厘米和9.3厘米,宽平缘。主纹为高浮雕的龙虎对峙。宽平缘上饰以三角锯齿纹、单线水波折纹。
四
关于这面铜镜的来历和相关情况,蒲松龄自己在《古镜行,赠毕衡伯》一诗中说得明明白白。现将此诗抄录如下:
古镜行.赠毕衡伯
古镜,古镜,不知甚代何年。故人发箧相赠,其大如拳。背上罗纹细细,朱绿班班。四周有物盘踞,非螭非虎。但辨榆荚小篆,明明五铢钱。四座迷迷,欲解不能得解,抱问博物茂先。言是唐朝大钮,当出陵冢,得之地下黄泉。置几上,睫毛疏疏可指,年生两茎白发,拔去公然茂齿。我将怀之湖海山岳,及尔共悲喜。待颔髭摘尽,留会与膝下孙子。乱曰:“黄金买丝,绣作荷囊。玉椟深藏之,深藏之,勿疏其防。君子少,小人常多,波斯贾,其奸不可量!失镜去,故人心怆。”《蒲松龄集.聊斋诗集.郑二.癸亥》(525页) 根据这首诗,再对照分析这面铜镜,可以得出如下结论: (一)蒲松龄的铜镜是故人相赠的。从“其大如拳”(8.9厘米),“罗纹细细”(水波折纹钭线纹等),“朱绿班班”(红绿锈迹斑斑),“非螭非虎”(汉末的龙虎形象)和“但辨榆荚小篆,明明五铢钱”等句看,蒲松龄随葬品中出土的这面铜镜与其诗中描述的那面铜镜完全相同,当为同一面铜镜。 (二)蒲松龄请教像懂博物的张茂先(即《博物志》的作者张华)那样知识渊博的朋友,“抱问博物茂先,言是唐朝大钮,当出陵冢,得之地下黄泉”,判定铜镜是出自地下陵墓之中,并断为唐代之物,说明蒲松龄当时为这面铜镜的鉴定和断代是下了一番功夫的。虽然由于历史的局限,断为唐物是不准确的(唐镜的风格特点与这面铜镜迥然不同),但却也有据有论。 (三)蒲松龄是很喜欢古物的,虽然由于一生贫困潦倒,无经济能力收藏。但从这首诗上看,蒲松龄对这面铜镜是何等的喜爱和珍视,“我将怀之湖海山岳,及尔共悲喜。”并准备晚年以后,将这面古镜传给子孙,并让子孙“黄金买丝,绣作荷囊。玉椟深藏之,深藏之。”绝不允许外国有钱商人骗哄买去,“波斯贾,其奸不可量”,“失镜去,故人心怆。” (四)这面铜镜既是蒲松龄生前所珍爱的古董收藏品,也是其生前日常生活用品。从镜子的锈迹看,镜背和镜面反差大,特别是镜面绿锈,呈明末清初出土铜镜所具有的特征。这是因为当时镜子出土后,镜面被磨光,涂上一层“玄锡”,被重新使用过,蒲松龄逝世后,又作为随葬品入土的结果。 从这首诗看,蒲松龄曾使用这面铜镜观容自赏,“置几上,睫毛疏疏可指,年生两茎白发,拔去公然茂齿。”这说明,一生清贫的蒲松龄只能将“古董”和“日用品”合二为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