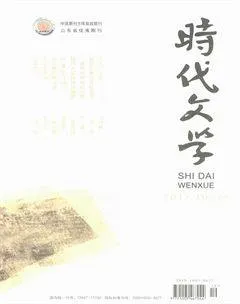父亲的自然
家乡人形容数大,习惯说,两手挓挲也拨拉不开。父亲去世已二十年,拈指数来,一手一手,一手一轮回,感觉就有些茫远,真正是两手挓挲也拨拉不开了。
自父亲去世后,我有了自己的孩子,以父亲的身份反思父亲,父亲去世的真相越发迷离起来。我有时想,他还生活在生前的村庄里,最起码,在老树老屋的气息里,还应该有他的声息。可是霜天晓角,微雨暮钟,人在何处?我有时疑惑,他的坟体越来越厚实,坟头草越来越茂密,有人陪着,坟才能逐流年衰老,也许他还在世,还能陪伴着孤坟一起老去。又有时四顾茫然,村庄变了,不再复当年的灰暗,光洁如洗,路畅心阔,哪里能找到他的身影?
老屋屡经整修,浑破如老衲僧衣。胡同里黑马打过滚的地方长满牛膝菊。他去世的头几年还在房头崖下落雪的马车,其形相我竟然在正棋山麓一棵法桐树下遇到,站在上面,唤醒当年的质感,心里的血还是温热的,但周遭已经山河殊异了呀。
偶尔与乡亲交谈,才发现父亲还活在乡亲的方言里。譬如在清明上坟回来遇上德金叔,他感叹四哥帮他盖房可出力了。譬如遇上世俭叔,他在不经意间也说到父亲帮他出力盖房的事。那一瞬间,父亲还在盖房子。
造化有时也真眷顾人。父亲不单在乡亲的方言里出力流汗,竟然能在乡亲的文字里活着。铎振叔出身农民,以公办教师的身份退休,徙居德州,抽空写了《垛山前怀的故事》,把乡间的人和事用文字记录下来。其中有《四哥王德芝》:
他蹲下身来,用手抓一把土使劲一捏,然后站起身来一松手,鸡蛋大的土掉在地上散开。
“土中含水分15——20%,这个湿度,下星期天一定能出麦子,放心吧。”
这段文字充满了现场感和氛围感,是我目前所见的唯一出自乡亲笔下有关父亲的文字,弥足珍贵,聊以弥补父亲音像皆虚的遗憾。
对于我来说,它也是“在场”的文字,揭示了一段本真的面目。天上云薇青,地上菊花黄。山南水北,伊人何往?汗水落,尘土扬。秋光温煦,金风朗畅,廿年风景心头霜。
它更像是1990年代的《弹歌》①。父亲复活成一个巫师,以田野为道场,沟通人神物我,直达农耕先祖的本来面目,在流荡的光影里且踏且舞,间或歌哭朗笑。
于是,这寥寥的文字便洇出了汗水和尘土的味道。他是一个农民呀,没有现代的仪器来分析,他怎么能知道物性,难道他就是长养麦子的那抔土?
父亲一生,躬耕黄土,风尘扑面,性格里确实充满了土的元素,勤于长养,甘于化育,性重情厚。
父亲随手扬起了自己的自然。那里面有天人之始,父母之本。父亲的自然,尽显土德之瑞。他和他同时代的农民兄弟,土生土长,一起延续着乡土中国的传统。
他刨地锄地的镢柄锄柄是木制的。薅青草的篓子是绵槐条编的。拈芽滤种纯手工。赶车的鞭杆赖由几根竹条拧成绳状,扬手甩出的鞭响就是农民版的《竹枝词》了……如此种种,都是土德向生存空间的顽强延伸,泥土也有向更高空间拓展的梦想。
衰老没落的时节,他也用一根树枝赶车。
赶车能管住马耳朵就成。父亲生前如斯言。
大道至简,这话里的玄机我无从解读,却透出更加神秘的形上意味。它和父亲用过的器具都小心翼翼地躲避着铁器的锋利与乖戾,朴素温良的气息从血脉肺腑间逸出,抚慰着农民自然的通感。
我也是土命的孩子啊!在我的身体里,流淌着血浓于水的热度,沉淀枯干,也是一把泥土——我生活在父辈的自然里啊!
父亲可能意识到这一点,就在适当的时候离开了,像他的父辈一样,像他的农民兄弟一样。父亲去世的1993年,乡土中国开始悸动,现代化之梦唤醒每一颗不肯沉沦的心灵。世界进入了钢铁时代,草木泥土,吟咏着农耕文明式微的牧歌。在文字里扬起泥团的父亲,成为时代的殉道者,最终消失在平畴远风里。
流水逝去,遗下河床。草木逝去,遗下山梁。云彩逝去,遗下天堂。父亲逝去,遗下了什么?是绵密如雨的意识流?还是轻虚如雾的乌托邦?
父亲遗下了一个真实的自然。这个自然里,山还在,河还在,庄稼依旧年年荣枯,燕子依旧年年来去。这个自然里,有他,也没有他。血脉星云,也残缺,与完美,也混沌,也明晰。我是他,也不是他。一切荒诞,一切又真实。
也许这才是另一层真实。真相的背后,无极而远,民如野鹿。父亲的先辈这样离开了父亲,父亲又这样离开了晚辈。父亲和先辈一起站成了谱牒,留下了后辈成长的自然。
父亲的自然,只有空明,没有离伤。
注:①《弹歌》:目前所知中国最早的诗歌,相传作于黄帝时代。其辞曰:断竹,续竹,飞土,逐宍。其中“宍”即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