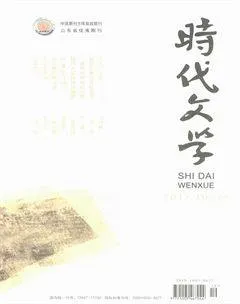泪洒上学路
上世纪六十年代,是人们生活极度困难的年代。
1965年仲冬,那个北风呼啸的星期六下午,正在菏泽二中读初三的我,一回到乡间家中,便骤然被笼罩在了一种异常悲凉的气氛之中!除了那逼人的寒气,犹有氤氲在父母亲脸上那浓密的愁云,还有弟弟妹妹们那一张张闷闷不乐的神情,刹时令我心头紧蹙,毛骨悚然!
经我急不可耐地寻根问底,方知家中正陷于前所未有而无法自拔的窘境。由于当年农业受灾,粮食歉收,家家户户的生活皆是青黄不接,要靠国家救济苦度荒春。而像我家那样人多劳力少(我们兄弟姊妹多而年幼)的缺粮户,根本等不到冬天过去便囤底无粮了。正当父母亲发愁无门的时候,本打算年关出手能解点燃眉之急的我家那头半成品(约80-90斤重)的瘦猪,又突然被“四清”工作队弄去抵偿父亲当大队会计时苦于生计欠下的几十元借款。尽管父亲恳求能再宽限俩月,等猪长够秤了(当时生猪出栏最低标准为120斤)再卖掉还款,那样尚可腾出一点买粮的钱,但最终却无济于事(运动后期才实行了“减、缓、免”政策)。面对这雪上加霜的困境,茫然不知所措的父亲母亲,顿时只剩下了绝望与为难的份儿!
当时摆在父母面前的最大问题,莫过于全家人的生活和我的学业了。当着全家人的面,父亲一边抹泪,一边哽咽着对我言道:“这回咱家的日子真是没法过了!给老师说说,咱休学吧!”我闻听不禁心头一震。父亲对我的学业可从来都没含糊过,非万不得已,绝不会轻言放弃。那一刻,听着父亲声泪俱下的表诉,我心中纵有再大的委屈,还能说些什么呢:“爹,我听您的,回去就找老师!”人们常说:“穷人家的孩子懂事早。”那一天,我比任何时候都倍加体谅和可怜我的父亲母亲,倍加俯首温顺地陪伴父母度过了一个心酸难熬的周日。直至天色渐晚,才锥心刺骨般匆匆踏上了返校之途。
从老家到学校那区区七华里的路程,是多么的熟稔,多么的亲切,多么的神圣,多么的庄严!这条路连接着我的求学之梦和人生理想。尽管那时它还是一条蜿蜒不平的乡间小道,且全靠徒步行走;尽管单靠国家每月补助的12斤粮票和自选的低等伙食标准,无法维持在校生活所需,每周都要扛着母亲蒸的粗面(或糠菜)馍馍,去弥补肚肠之饥,但每次走在这条路上,不管温热寒凉,还是风霜雪雨;不管尘土飞扬,还是泥水缠足,从来都没有过丝毫的踌躇与彷徨。而那天走在这条路上,当我想到马上就要被迫弃学,离开深爱的母校、老师和同学的时候;想到父亲母亲含辛茹苦供我上学却无奈步入绝境的时候,离家前那面对父母强颜压抑的无尽悲伤,禁不住一下子倾泻而出!伤心的泪水,夹伴着尖利的北风,顺着我那嫩瘦的脸颊滚滚流淌。为了宣泄心中的悲懑,我索性仰面大呼起来:“苍天有眼,我要上学,快救救我吧!”当时,前方不远正走来一位五十来岁,身穿黑色棉衣的过路人。他显然听到了我声势力竭的呼喊,于是快步近前道了一声:“咋啦孩子?天下没有绝人之路,再大的事也得挺住啊!”“没事的,大爷您放心!”辞别这位像我父亲一样高大善良的长者,反复琢磨着他那句“天下没有绝人之路,再大的事也得挺住”的忠言,我仿佛在漫漫寒夜里突然望到了一缕明亮的曙光!
就在我一路边哭边走,边思边想地步入校园的当晚,同学们不约而同都发现了我的异常,接踵而来的便是一声声贴心的问候和真挚的关爱!我班团支部书记孙吉莲同学急忙找我问长问短,班主任朱德荣老师闻讯紧急召集班委会议,并旋即找校长为我申请了三元钱的救济款,继而又在下学期将我的助学金由两元增至三元。我至今还清楚地记得朱老师把我叫到他办公室时的情景。身材魁梧面容慈祥的他,一边用手拍抚着我的肩膀,一边反复重复着“不要怕!再难也要想办法”这句话,使我久久沉浸在了无比的温暖和莫大的鼓舞之中!
为了报答老师和同学们的关怀,我发誓,再苦再难也要争这口气,进而把裤带勒了又勒,紧了又紧,将每月伙食定粮由27斤降至24斤,并取消了每月三元钱的订菜款,这意味着我一日三餐不吃菜,不吃油。虽然如此刻薄的生活标准使我整天饥肠辘辘;虽然当年全家都承受了难以想象的生活磨难,以至于父亲忍疼揭卖了家中房瓦,变卖了母亲的衣柜;虽然周围人等曾对我家投来过轻视耻笑的目光;但我们终于闯过了那道异常艰难而意义非凡的一关。
“人间自有真情在”,“患难见真情”,这些古今中外的至理箴言,曾经被世间多少生动的故事所诠释。在漫漫人生中,我曾遭遇过各种各样的坎坷与困难,但也在身陷困境与绝望时,有幸饱享过弥足珍贵的人间真情。除了困难时期党和国家对我家生活的救济,对我学业的帮扶,更有像朱德荣老师那样爱生如子的恩师,雪中送炭,在危难关头对我施以的救助……那每一份真情,每一份挚爱,都将永远深深铭刻在我的心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