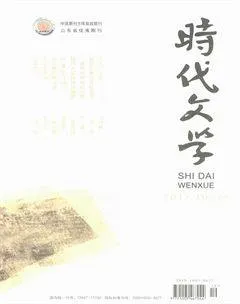家乡的水井
近日回老家一趟。午饭后我来到辘轳井旁,驻足良久。井壁长满青苔,毛茸茸、绿茵茵,满是岁月的痕迹。水质清澈见底,我看到了我清晰的影子。
辘轳井南倚背阳的大堰根儿,井口的青石块被钢丝井绳划上了道道沟痕,井旁的石板路也磨出了深深的脚印。站在井边,手扶辘轳,望着大堰上几株枯萎的蒿草,许多往事在眼前浮现摇曳……
一
我的家乡,在淄川东南山区的幸福嵧。十年九旱,水井是人们赖以生存的生命源泉。小时候,村里有两口古井,一口在村边太平桥东,另一口是村外近二里路的西蹲井。村里人口持续增长,牲畜用水也日渐增多,干旱季节,两口井远远不能满足饮水需要。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村里找人勘察,陆续打了十几口井。有的打到预定深度不见水或者水太少,成了枯井,能用的也就两口。
那时打井,村里没有电力和机械,全靠人力土法挖掘。一开始,有人挖,有人用绳子和筐往上拔。挖到三四米后,开始采取“机械化”。先在选定的井口旁树一根五六米高的粗木杆子,在木杆的顶端拴上一根横着的长杆,竖杆为支点,利用杠杆原理,一人在井口掌握方向和向下续空框,两人在较短的动力臂一端用绳子向下拽,将人工一锨一镢凿出的土石料运上地面,由专人运离井口。深度不断增加,杠杆的支点逐渐向远离井口的一端移动,使动力臂缩短,虽然费力大了,但能增加阻力臂一端的绳子伸向井里的距离。人多力量大,效率不算太低,但深度总归有限。
挖到十来米深,仅靠“杠杆”就很难挖深了。“机械化”程度需再提高一步。撤掉“杠杆”组合。在井口上方用三根或四根长杆,组合成正棱锥形,在锥形顶部下方固定上一个手推车轮圈,将一根绳子嵌入轮圈槽内,利用定滑轮虽不省力但能改变用力方向的原理将土石运出(后来就有专门的“滑子”作定滑轮了)。一般的,井口有一人轻握绳子掌握方向兼指挥,两人拉绳子。指挥员喊一声“上”,两人将绳子搭在肩上,拉车似地弓背低头前行。一声“停”,两人止步拽住绳子。等候在井口的另两人将运上的土石渣或抬或推运到一旁。一声“下”,拉绳人掉头拽着绳子倒行。循环往复,日复一日,挖到预定深度或见到泉水汩汩涌出为止。一口井有的在三四十米以上,挖到岩石后还要再凿下去许多米。然后,用石块一层一层地砌成下粗上细的圆筒形井壁,井口一般用长条石块砌成边长半米左右的四方形,或用整块大石板中间凿一直径半米多的圆孔,以便村民取水时站得稳当。最后高筑井台,离地面二三百厘米,以免杂草污水进入井内。至此,就算大功告成了。
七十年代中末期,家乡有了交流电。农业学大寨,建设大寨田,打机井修水渠,旱田变水浇,战天斗地夺高产。机井选址都在低洼的河道处,井口大,直径十多米。运送土石料大都人抬车推,场面大,人员多,上上下下,热闹非凡。简单的电动机械派上了用场,劳动效率大大提高。几个村联合打的“幸福”机井,水量不够充足,我村没获多少利。与东坡村伙合打的“西河”机井,为村民的饮水和灌溉贡献很大。
打一口井,约需数月时间、几百个工日,甚至还会付出生命代价。由于设备简陋、工艺落后,上下运送土石料时常有土石块坠落、拉绳断裂等危险。七十年代初,挖村西桥东那口井时,阴历六月初一这天上午,细雨纷飞,带领社员打了十多口水井的老大队长李元全大伯正在下井,井口把绳人员没稳住拉绳,脚下一滑,使他坠入几十米深的井底,为村民的饮水事业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小学课本上说,江西瑞金“红军井”的碑文是“吃水不忘挖井人,幸福不忘毛主席”。水井和幸福连在一起。由此可见,水井对于人们是多么重要,人们对贡献于民的水井和挖井人有多么感激。
二
村庄附近,没有长流的河水。到了雨季,村中小河才有那么几天水流。在此生活过的人们,都对水井有着难以割舍的情缘。井筒圆圆的,井口方方的,成年累月地敞向云端。它映照着故乡的日月星辰,摄录着飞鸟的矫健身影,叠印着人们的喜怒哀乐,阅读着古今的沧桑岁月。井口虽小,内容却博大而深沉。井水因了洪涝干旱的影响,水位有高有低,却从未曾干涸。炎热的盛夏,井水仍是凉丝丝的,再寒冷的严冬,井水依旧温乎乎的。
每个家庭每天都要挑水,工具是带铁钩的扁担——担杖和带铁系的水桶——筲。从井里提水要讲技巧。大多数家庭都有一根四五十米长的麻井绳,用一端将水桶拴结实,或在绳端系上一个回形铁钩将桶钩牢。水桶缓缓下放到水面,拽着井绳左右摆动几下,让水桶口朝下猛地一松,然后慢慢拉起水桶,轻颠两下,断定水桶已满,就弯下腰两只手倒换着将水桶拉上来。一圈一圈把井绳挽起挂到胳膊上,挑起水桶运水入缸。
我眼前这口辘轳井,是七十年代初挖的,深约四十米,当时安装了较为现代的取水设备——辘轳。用辘轳取水省了不少力,但有两个关键问题:一是套三环,二是注意安全。绳端有个直径约十厘米的铁环,两个稍大点的圆环中间连着四节长形铁环从小环内穿过。此三环套起来,会的不难,难的不会。初次使用时,还需见习几番。这种装置,水桶一般脱不了钩。水桶放入井中,辘轳会越来越快地旋转,人必须侧着身子,躲到摇臂的后边,双手扶住辘轳,井绳快放完时,手用力刹住辘轳,再用一只手扶着摇把,一只手摇着井绳把水桶灌满水,然后一圈一圈把水桶摇出井口。
挑水吃那年月,劳动是生产队管理,统一出工、一齐收工,劳动力没有个人自由,只能在清晨和傍晚挑水。挑水的人很多,很热闹。井台上,小路边,讲故事,拉家常,嬉笑打闹,一片生机。人们每天都要在井边见面,有的情侣,也利用挑水的机会悄悄说上几句话,递上心爱的手绢,抓一把花生,递几个红枣。胆大的还偷偷拉拉手、拍拍背。水井旁如同现在城市的早、夜市一般,挑水的,排队的,打招呼的,闲聊的,挑着水一起回家的……桶儿叮叮当当,扁担吱吱悠悠,自然形成了一曲和谐的乡村乐章。
在村里,别的事可以不干,挑水却从未间断。沐着晨曦,伴着残阳,迎着春风,顶着夏光,踩着冬雪,沾着秋霜。一年四季水井无私奉献着,乡亲们踏着弯弯小道,担担水儿挑满缸。
我家住在村东二里路外的半山坡上,父亲在生产队里干活,一天出工、收工三次要多走十多里路。时常饭还没吃完,队长就吹着哨子招呼了。家里七口人及牲畜用水全靠父亲起早贪黑一肩挑。我是长子,对父亲的辛劳看在眼里,疼在心里。很小就学着挑担子,十岁时已独自挑土挑水。一开始,父亲用一个废弃的铁暖水瓶皮改成了微型水桶,又配上一个小点的水桶,练习挑水。十二岁时,就能供全家吃水了。初学挑水,犹如蹒跚学步,方法不对头,担杖压在脖子上,龇牙咧嘴,抬不起头,东倒西歪,走不成溜。两桶水挑到家剩下不足一桶。在父亲的指点示范下,掌握技巧,两肩交替,上下肢协调配合,渐渐学会。刚开始肩膀受不了,一担水没挑到家,双肩红肿,疼得火辣辣。父亲说:“三日肩膀,二日腿。连挑三天就好了。”我咬牙坚持了一星期,感觉果然好些。
我在挑水的时光里渐渐壮实长大,也让我学会了风雨一肩挑。感谢您,家乡的水井,您是我最初锻炼身体的操场,也是我人生的第一课堂!
三
八十年代初,改革开放的春风,吹进了沉睡的村庄。专业钻井队利用专门设备为村里打出一眼三百多米的深水井,水量充足,水质优良,富含多种人体必需的矿物质,呈弱碱性,符合国家饮用矿泉水标准。九十年代初,村里招商引资,办起了“神来”矿泉水厂,优质矿泉水源源不断运往各地,村里增加了收入。近几年又把自来水管道顺到每家每户,村民用水方便了,做饭洗衣,就连洗澡喂猪也用矿泉水。再也不用为吃水发愁,冒险下井了。
家乡的老水井已退出历史舞台,有的封口,有的被填埋了。
我为家乡的进步感到由衷的高兴,又为废弃的水井感到莫名的遗憾。只有这辘轳井,依然守望着,奉献着。在冬天自来水断停的时候,还有部分村民隔三差五来这里挑水。
艰苦的童年生活,促使我发奋学习。恢复高考离开家乡,丰衣足食三十多年。每每想起故乡,就会想起水井。美不美,家乡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啊。
艾青说:“我是喝大堰河的奶长大的。”而我,是喝母亲的乳汁和家乡的井水长大的。感恩母亲,感恩那些挖水井的家乡父老们。
难忘家乡的水井,我虽远离了你,但仍和村里人一样,时时回味着一个个故事,在梦乡里大睁着眼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