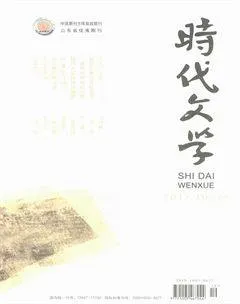国王的回忆
上午十点钟的火车站,阳光灼热地黏着皮肤,如同一个拉着人的手啰嗦不断的中年妇人,令人避之不及。不过,在这里,再灿烂的阳光冷眼看,也带着伤感。站台,离别的代名词,站上这里的地面,那些与离别相关的情绪和记忆就会忽然间生了根,从地底下冒出来,抓住人的脚腕一路爬上全身。
我摇了摇脑袋,将那些试图爬上来的记忆摇散震落。我不是来回忆的,今天我的小姨,要从遥远的新疆回来了。正值暑期,来车站接她的任务,自然落到了我这个从事教师职业,三十三岁仍未婚配的闲人身上。而我刚才差点又想起的站台故事,已经过去很久,像一部老电影,那些离别中的情绪,经过很多年时间的包裹,不痛不痒地,青草触上脸颊一般,吹一股什么风,就散了。
小姨的回乡,和她感情生活的波折有关。听母亲说,似乎是偶尔翻看姨夫的手机,发现了不能够接受的东西。她性格一贯强势,耻于质问,单方宣布离婚之后,就独自甩袖回老家来了。
我是晚辈,自然不便做任何评论,只装作不知道,认真地履行接待的职责。晚点了十分钟,我站在出站口围墙边的阴影里,百无聊赖地低着头,打量周围人的鞋和裤脚。
老舒来了电话,问早上干什么。
在车站,接一下小姨。
怎么不早说,我开车去。他语气里有种表达亲密的责怪。
反正也没事,我坐公交来就行了。
车头挟着一股风,飞了过去,火车进站了。
车来了。我说。
接站的人的脖子,都拉长了几寸,目光更是从出站口的铁栅栏门里长长地伸出去,一起抓住仍在前进的车身,用力拽。车停稳了,到站的旅客从那封闭的车厢里下来,走向出站口,渐渐地汇聚成了一条人流。
绝大多数的人脸上都带着浓重的倦意,我认真地注视每一张脸,甚至连一个女人脸上麻点儿多,一个男的鼻子旁边长着痦子都看得一清二楚。
看到了,我的小姨,穿着条及膝的黑裙子,单肩背着一个大包,身后的拉杆箱在凹凸不平的地面上蹦蹦跳跳地,牵在手上的孩子一样。
一路上还顺利吗?我接过她手上的箱子。
人太多,挤得,身上的汗就没干过。她眼神一直躲闪着,语气轻而低。
回来就好了。我一语双关。两个人就这么提着箱子,并排出了车站,然后打车,直奔城郊的姥姥家,母亲已经在那里等着。
从老路走吧。小姨看着窗外说。
也好。我理解她的意思,久不回家的人,都希望再走走记忆里的路,以找到记忆里的那种温暖。于是叫司机把车开上一条村道。还是沙石的路面,两边是高大的槐树,荫翳蔽日。正值开花的时节,满树的碎花朵,也有早败下来的落在地面上,一树一树地,成了形状。
还是不一样了。小姨偶尔感叹一句。
那是自然,如果还和七八年前一样,怎么证明时代在发展呢?我努力地表达一种喜悦的情绪。
是啊。她淡淡地回应。
下了车,还有差不多四五百米的路程需要徒步,才能进村子。跟在小姨的身后,我发现人的情绪其实不仅是语言目光能够传达,因为我能感觉到有种失落或类似于惶惑的东西挂在她后背上,甚至连同走路的姿势里,都渗透着。情绪,原来是一种气味,从人的内心和灵魂里散发出来,飘溢在周身。
这里有几棵老树,好像不见了。小姨略站了一下,幽然地说。
大概吧,谁知道呢。我顺着她的目光看过去,并没有想起哪里有一棵或几棵树。我只有小时候在姥姥家玩过几年,后来上了学,就不怎么来,对于这个第二故乡,缺少关注与琢磨,基本也只剩下一个概念了。
玲玲来了吗?是玲玲吧?路边一个黑脸的婆婆认出了小姨,叫她的小名。
惠婶婶,我是玲玲。小姨认出了对方,站下来问候。
玲玲!惠婶婶从坐着的树墩上站起老身体,伸出两只晒得粗黑的手,拉住小姨,不断地摸索,如同见到了自己久别的女儿一般。
多少年都不见了,回家来了。惠婶婶翕动着发紫的干嘴唇动情地说。
我不惯见这种外人间的过分亲热,便远远地站在一边。
寒暄几句,惠婶婶松开手,说,去吧,快去看你妈妈去吧,多少年了不见,想呢。
这样的老太是村里常见的,一生勤苦,养育操劳,儿女大了,还要帮着照料孙辈。她们老来大多一身病痛,煎熬着度日。
走出几步再回头,我看见惠婶婶在拿手掌擦眼睛。
看见你回来,她倒哭了。我语气里带着些不理解的嘲笑。
是想起艾娃了。小姨黯然地说。
艾娃是她女儿吗?
是。
哦。我感觉得到小姨并不想多说什么,也就不再问。
转过个街口,就到了姥姥家。门口的两棵槐树,长得很是齐整,茂密的树冠,仿佛一小片落下来的天空,高的树荫里,有不知名的鸟儿对答鸣叫。
妈妈!小姨紧着脚步踏进院子,在窗跟下叫了一声,听得出泪水的质感。姥姥和母亲从屋里迎了上来,母女三人,在屋子中央相遇。姐妹之间毕竟更加亲密一些,母亲先迎上来,和小姨拥抱在一起。松开了,又转向姥姥,伸出两只手,和姥姥的两条手臂握在一起。我拎着箱子站在一旁,笑着,心上酸酸地。
姥姥自知小姨伤心,便不问其他,只问一路上的情形。母亲则打水,让小姨洗手洗脸。
洗完了,喝了杯水,小姨起身在屋子里细细地查看。屋里的陈设,一如当年。靠墙角的方桌上,一副桃木的插屏镜子,一对荷花纹的双耳花瓶,都是姥姥结婚的时候太爷爷给的陪嫁。对过的墙上,挂着老镜框,里面镶嵌着姥爷姥姥以及母亲和小姨姊妹小时候的黑白照片。还有用了几十年的铝壳暖瓶,红漆剥落的碗柜,锈迹斑斑的洗脸架等等,这些东西安静地散发着温暖的光,勾起了小姨无数的回忆,看着,像又要流泪。
再次坐下,小姨坐在中间,母亲和姥姥在两边,一人握住一只手说话。从上回的分别开始,拉拉杂杂,想到什么说什么,喜的,悲的,夹杂在一起,一忽儿笑,一忽儿难过,一忽儿又感叹。
门开着,院子中间那棵老梨树,皴裂的树皮上写满沧桑,但是抬头,却能够看得见一树新鲜的树叶,如同老人的手上牵着个孩子,阳光穿过层叠的树叶,撒落在地上,仿佛地面上无端地开出了发光的花朵。风吹树叶的沙沙声,轻轻唱和,诉说着时光的故事。
想吃什么?姥姥问。
吃什么就说,就因为拿不准你想吃什么,才没有提前预备。母亲接着说。
什么都行,只要是妈妈做的,吃着都香。小姨说着,眼泪又涌上来。
姐姐做的就不香了?母亲调笑着。
香,都香。小姨抹着眼泪笑。
她的举止,和我印象中的完全不同,感觉上,她是一个开朗到豪爽的人,爱说爱笑,喝酒也厉害,我父亲每次都叫她喝倒。这回回来却总是掉眼泪,说什么都动感情。
那就吃臊面吧,长长地,顺顺地。姥姥说。
姥姥的臊面,的确好吃,尤其是汤的味道,香浓醇厚。我小时候脾虚,不爱吃饭,但每次姥姥做了臊面,都能吃好些。
姥姥亲自去和面,母亲则准备着洗菜切菜。
国王,你干什么?母亲故意笑问。
我还是打下手,负责剥葱剥蒜吧。小姨笑了笑,低着眉说。
小姨不会做饭,这我大概知道,也不奇怪,她在家年纪最小,上有母亲和姐姐,又有两个哥哥,诸事都不用管,难得有锻炼的机会,后来成了家,家务也基本由姨夫料理,做饭,只在兴起时动动手。
我坐在方桌旁,一边看她们忙碌,一边给姥姥剥小姨带来的核桃。他们姐妹的童年趣事,母亲自我小时起就时常讲,很多我都熟悉。
老舒又来电话,问人回来了没有。我说来了。
要不要我也回去看看。他问。
在姥姥家呢,不来了吧。
行,那你有什么事儿打电话,啊。他的最后一个啊字表达了一种亲密和关怀。
嗯,我也用一个字表达了我的接受和顺从。
有可靠的男朋友了吗?挂上电话,小姨问我。
也有,就是没个可靠的。
多大的人了,还挑三拣四的,不知道要在娘家赖到什么时候呢。母亲不失时机地数落了我一句。
遇见差不多的,就好好谈谈,日子过起来了,都一样。小姨说。
嗯,知道了。我回答完,便跟去找姥姥。
哈!老舒,不知道的人还以为是老叔,有多老似的,其实,他只比我大两岁,三十五了,二十四岁结婚,婚龄一年,离婚无孩,然后就一直晃悠着,到了现在。
吃过了饭,又陪着小姨去了隔壁的二舅家,二舅和二舅母都不是善于表达的人,只淡淡地聊聊天,准备了晚饭,以表达多年未见的情谊。
平常他们常过来吗?小姨问姥姥。
他们有他们的事情,我这里也不需要人照顾。姥姥的意思明白。
小时候,原本姥姥和两个舅舅是住在一个院子的,但是人多,事情也杂,渐渐地,有了分歧,能看出来一家是一家,大舅和大舅母就搬出去自成了一户,姥姥姥爷和二舅他们住一个院子,后来又生了些什么事情,干脆他们也单门别院地住去了。姥爷去世以后,母亲坚持要将姥姥接进城,可姥姥怎么也不答应,坚持一个人住在乡下。
我们都得感激你姥姥,母亲常对我说,要不是你姥姥守着那个院子,我们现在哪里还有个去处呢。
我知道母亲说的大约是所有出嫁了的女人的心里话,有个娘家,好歹还有个去处。就像今天回来的小姨,如果不是姥姥在这里,即使是躲避,又哪里能找到一个这样好的地方呢。
天色晚了,我们围坐在姥姥的炕上,翻看姥姥前些年绣的枕头顶子。
玲玲,三喜如今是什么态度啊?母亲终于切入了正题。
他能有什么态度。说到姨夫,小姨立刻眼神灰暗下来,背靠着墙,眼神空洞。
也可能,你多想了吧。母亲小心翼翼地说。
谁知道呢。小姨再次低下头,翻看绣品,但是明显地,她的情绪烦躁起来,手不停地动,却没有认真看一个。
男人,都一个样,哪家的好。母亲叹了口气。说起来,我也是一肚子的气和委屈。
姐夫挺好的。小姨低着头说。
好不好的,谁家的事情谁知道。外头看着好的,也不一定里头也是一样的好。
母亲说这话的意思,我是知道的,她和父亲在一起,也时常会因为什么事情闹矛盾,比如家务干的多少,或是谁的习惯怎样了,等等,但是相比较而言,我认为在家里,还是母亲付出的多一些,女人嘛,母亲常教育我,还是要以家庭为重。
小姨还是不接腔,这时候,如果她能把心里的委屈和郁结说出来,也许就好办了。所以,母亲所说的话,只不过是一种引导。
睡吧,小姨说,坐了两天火车,怪累的。
也好,有什么,等缓好了再说。
关了灯,睡了。
我今天,看见惠婶婶了。沉默了半晌,小姨说。
惠婶婶?还好吗?
看样子也是一身的病。
哎,那样的境遇,不病反倒奇怪呢。
她拉着我的手摸了半天,我过来她又哭了。
小姨的声音幽幽地,燃起的一只香一样。
可能是想起艾娃了吧。
二十多年了,那时候,倒好的比亲姐妹还要好。
那时候我要是不去新疆,现在会是怎样?小姨和母亲坐在院子里。
现在的事情,那时候怎么能知道,
也许那时候不去新疆,现在就是另一个样子。
如果不去,肯定是另一个样子,但是,不去,也不一定比现在好。
你说的是,就那么些事情,不是这样,就是那样,其实都是一样的。小姨双臂搭在膝盖上,十指垂地。如果艾娃那时候没有找那个小伙子,情况肯定也不一样。
嗯,应该是吧。
不过按你说的,也不一定就好。
好不好的,就看怎么说了。你如今这样,不知道有多少人羡慕呢。
人都是看着别人好,真正自己到了那一步,才能知道,什么都是浮云。小姨说。
什么都是浮云。我站在他们背后噗嗤一声笑了,教育局长也会说这么时髦的话呀。
你以为就你年轻呢。母亲揶揄我。
没有,我已经老了。我说的是真实的感受。
在长辈面前说老,怕是要挨打了吧。小姨转过脸,稍微地露了个笑。
你们这年纪,正是活的好时候,我们这些年轻人,反而灰暗的很。我说。
对了,箱子里有哈密瓜圃,要不要吃?小姨说。
吃啊。于是我转身去拿来,坐在他们俩对面,哗啦啦地剥开袋子,一起分食。
记不记得有一年,爸爸带回来一筐青皮杏子,也是这样围在一起,吃了一晚上。小姨说。
怎么不记得,我的牙酸了几天,什么都不能咬。母亲托着腮帮说道。
还有一年吃西瓜,你小姨偷偷把瓜子塞进鼻孔,害得我们都跟着挨打。母亲对着我说。
是啊,我记得爸爸去追哥哥,他就跳进猪圈,爸爸就没办法了。小姨也笑。
故乡的确是个疗伤的好地方,小姨自回来,就和母亲一起,四处闲逛,那些童年时代一起玩过的老地方,虽然已经变了模样,但是,依稀地,都还认得出来,于是,每走几步,便有一个和童年有关的故事,需要讲述一遍,讲述的过程,就是一个回忆快乐的过程。
其实我那时候挺嫉妒艾娃的。小姨坦白地说。
你们不是最好的朋友吗?为什么嫉妒她呢?
又说起了艾娃。
原来中学毕业后,小姨考上了师范,艾娃则辍学回乡了。宛若天人的女孩子,父母哪里就能舍得让做苦力,只在家里烧饭打扫,偶尔帮称着做什么,也是围巾包的严严实实,唯恐太阳晒黑了皮肤,风吹乱了头发。这样做法,若在别的女子那里,一定是会被人耻笑,担忧今后嫁了人如何担当重任,但是在艾娃,似乎大家有的都是疼惜。“那样的女孩子家,怎么受得了苦呢”。
同时,上门说媒的,求亲的,也络绎不绝,夸张地说,门槛几乎踩烂。然而,不管来的是何人,艾娃的父母一律以女儿年纪尚小回绝,其实在心底里,他们也是存着一份私心的,想为女儿谋个与众不同的人家。
后来,村子的路上经常出现一个小伙子的身影,白净,十分面善,来来去去地,再后来,就看见艾娃时常同行,大家便知道事情的大概。这小伙子是村子附近造纸厂的工人,城市户口。艾娃若能够找到这样一个人家,也不算辜负容颜。于是,在小姨师范刚刚毕业的那年冬天,艾娃便嫁给了工人小伙,成就了一段乡下女子人人羡慕的姻缘。
都是女孩子,她凭着自己的美貌,轻易地就能的得到周围人的宠爱,而我,虽然大家都叫我国王,但是,我还不是得整天起早贪黑地拼命读书,才能得到大家的赏识。小姨大概是第一次对母亲说起这些。
没办法,女人的命运,有时候真的很无奈。
不过,艾娃真的嫁的太早了。小姨感叹。
你要不是上学,说不定那么大也该嫁了。母亲笑道。
就是,还不知道嫁个什么样的人呢。
就你那个脾气,肯定嫁的不是杀猪的就是钉碗的,好人家谁要啊。母亲玩笑。
嫁给杀猪的还能天天吃肉呢。小姨顺着玩笑,也露了一丝丝笑脸。
三喜那时候怎么对待你的,难道你忘了吗?
怎么对待的?我插话问道。
我来给你讲,母亲说。
那年的冬天特别冷,你小姨从师范毕了业,被分到乡下的一所小学当老师,住宿舍。
说起来,那时候条件也真是差。小姨接过来说。我记得那时候的宿舍,刮大风感觉房子都在跟着颤,下雨就漏,晚上听得见老鼠在报纸糊的天花板里跑,每晚睡觉,都吓的要死。
你知道吗,母亲抢过来说,你姨夫害怕你小姨受冻,就自己打煤砖,晒干了再用车子拉到你小姨的学校,给码在门口。
说那些做什么。小姨的情绪忽然之间伤感起来。
那时候,你小姨最发愁的就是生火,柴少,引火都用农民地里弄来的葵花杆子,一个不注意就灭了,为那个她不知道搭了多少眼泪,你姨夫就想方设法地弄了一打尼龙袋子劈柴,给她送到学校。那天刚好下着雪,等他推着车子到了学校,一头一身的雪,熊一样的。
母亲讲述的时候,语气逼真,仿佛这一切是她自己的经历,而非小姨的。当我听到这里的时候,忽然空濛着眼睛看着远山。大雪天,一头一身的雪,熊一样的。小姨的经历竟与我的有重叠,不同的是,我那个浑身是雪的熊,并没有坚持陪伴我到现在,而是在另一个雪天和我在火车站的站台上告了别。过去很久了,没什么,每个人都有认为更加重要的东西,我不恨他。
有回他们学校把养的猪宰了,分了肉,你小姨夫一口没舍得吃,全拿来给我们了。母亲接着讲下去。
一条路上,不可能总是鲜花。小姨望着远处眼里一直含着泪。
说的是,但是,总还是有过鲜花盛开的时候。
我宁愿平平淡淡地,就像你和姐夫那样。小姨看着母亲。
我却在羡慕你的那些浪漫经历。母亲说的是实话,我的父亲,的确是一个没有丝毫浪漫细胞的人。
人都是在彼此的羡慕之中生活,因为羡慕而努力,或者因为羡慕而消沉。小姨说。
别人不羡慕你就好了,你还要什么,我的局长。母亲笑道。
是啊,我还羡慕什么,哪有什么十全十美的事情呢。小姨自嘲地笑笑。
你看,那不是慧婶婶吗?母亲突然伸出手指往远处的村道上指了一指。
是啊,那么大年纪了,还要操劳,真是不容易。
难怪看见你要哭呢。
你说艾娃要是那时候和我一起上了学,会怎么样呢?
能怎么样呢?你说能怎么样?
我不知道会怎么样,但是,一定会不同。小姨若有所思地说。
姐,小姨在一个树桩上坐下来,眼睛看着远处。其实那个小伙子,我之前就认识的。
什么时候?
就是在她认识艾娃之前。你听我说。
你不要笑我,小姨说。
可是当时,我不知道自己哪里来的那么大的理智。他是个工人,我不想把自己的青春和生命寄托在这样一个男人身上,我还有更大的理想。于是我拒绝了她。
这像是你,国王。母亲看着小姨说。
你听着,还没有结束,我不但拒绝了他,还告诉了她一个虚假的消息,回到乡下的那个我的女伴,一直都在喜欢他,并且一直在等待着他去找她。
你是说艾娃。
是的。小姨说。你们都以为我和她就像姐妹一样,其实,只有我自己知道我的内心,我对她,有着深深的嫉妒,她的美丽,她的柔弱,让我都想时刻保护她,和她在一起,我时刻感觉到自己的粗鄙和笨拙。而我拒绝了这个男孩,却把他推向她 ,也是对她的一种报复,我要把自己选择剩下的东西给她,并且看着她把他当成个宝。
姐姐,我是不是太阴暗太卑鄙了。所以现在,我觉得我的报应来了。
不,不会的。母亲站起身来,抱住小姨的肩膀。
回来不大时候,忽然听得门口有停车的声音,然后就听见一个男人的声音说,就是这里。站起身来往窗外看时,才发现果然如大家的猜测。小姨夫带着表妹来了。
母亲第一个迎上去。三喜,你来了。说着接过姨夫手上重重的行李。
姨夫略微尴尬地与母亲问好,再上前握住姥姥的手,问候姥姥。说话的空当,眼睛直奔炕沿上坐着的小姨。
小姨面无表情地坐着。
妈!表妹上前去抓住她的手。你怎么不告诉我啊。
原来表妹好不容易迎来第一个大学的暑假,和同学一起旅游去了,不想中途被姨夫叫了回来。
你不想我,可是我想我妈呀。小姨说着帮表妹拿下肩上的背包。
姥姥忙着倒茶,又拉着姨夫嘘寒问暖,问表妹学校里的情况。都围着才进来的人,倒把小姨忘在了一边。
姨夫带了许多新疆特产,拿出来热热闹闹分给大家。他的样子倒和我印象里非常一致,热心热情又和气。
大家都在,一起包饺子吧。姥姥提议,对于女婿,似乎从来没有从姥姥嘴巴里说过什么不是,任何时候有了问题矛盾,姥姥都是先指责自己的女儿。
父亲也来了,又叫了二舅,一顿饺子吃得,非常热闹,吃完了,父亲姨夫和二舅喝酒,我们祖孙三代五个女人在一旁聊天。
老舒打电话来,说他到了村口。
有什么事情这么急吗?我疑惑地问。
也没什么,我来给姥姥送西瓜,放时间长了不好,大家一起吃。他说。
只好给他说了路。
谁来?姥姥问。
一个朋友,说给您送西瓜来。
啊,知道了。表妹调皮地坏笑。
我也不解释什么,出去门口看着。等他来了,一起把一袋西瓜抬进来。老舒挺自觉,一一地问候完,就起身要告辞,但是他既然来了,哪里有就能走的道理,硬被按在椅子上。也许,我这个老姑娘的婚事确实让大家感到需要操心了。
老舒表现还是不错的,放得开,又有礼貌。
因为老舒的出现,小姨和小姨夫之间的问题倒被忽略了,大家都开始谈论我和老舒。
小伙子人挺不错,再别挑了。老舒走了之后大家一起教导我。
没挑啊,我挑什么了。我红着脸说。不就来送个西瓜,你们就都被收买了。
人家大老远地送来了,你有点感激之心好不好啊。表妹说。
呵呵,比起你爸妈雪中送炭的故事来,这算什么啊。
雪中送炭?表妹大睁着眼睛。于是,母亲又把雪中送炭的故事讲了一遍。接二连三地,那些众人皆知的故事,拌和着欢笑,玩笑似的一个个都被翻出来。大家都心照不宣。
你妈年轻的时候有个外号,叫国王。我对表妹说。
呵呵,局长,原来你还有更厉害的时候啊。表妹抱住小姨说。
你以为呢。小姨在女儿面前,又自豪地,回到了真实的自己。
爸爸,看来还是你比较有福气,能够找到一个叫做国王的人,不过,说明你也很厉害。表妹转脸笑着说。
我找到你妈妈,的确是福气。姨夫看似玩笑的语气里,其实表达着一种歉意,不知道别人听懂了没有。
他们后来的事情我大概知道一些,小姨是跟着姨夫的关系,才从乡下调进城,后来又调去新疆的,如果不是姨夫一路的扶持,也许她也走不到现在的地步。
接下来的几天里,表妹央我带她去四处转转,老舒得了消息,自然乐意负起责任来。开着车,把能玩的地方都玩了,表妹认定了这是她的准姐夫,也不客气,游玩的同时,把那天大家教导我的话一一转述给他听。而小姨和姨夫,却被母亲和姥姥抓着,换了衣服,到唯一的一块自留地里干活去了。
好不容易回来一趟,得好好抓住使使他们。姥姥说。
晚间回来,表妹汇报一天之中的趣事,他们坐在矮椅子上,认真倾听。
好像要大功告成了。表妹对我说。
我有些惊讶,因为一直以来,我都感觉到表妹似乎并没有把父母的事情放在心上。她叹了一口气,接下去说。有什么呀,不就是看见不该看的东西吗,当做没看见不就好了。沉默一会儿,她又说,人啊,还是什么都不知道的好。
我忍不住笑出了声,你才多大呀,说什么知道不知道的。
姐姐,你不要觉得我小,我知道我爸和我妈他们什么事儿都不会有。
我还要说什么,却发现表妹站在那里哭了。
没事,会好的。
我爸的手机我看了,其实,真的没什么,姐姐。
我相信你说的。我搂住她的肩膀。
小姨终于计划着要走了,大家提议一起去小时候玩过的湿地逛逛。那里本来是野地,这些年经过整治和开发,变成了环境优美的天然氧吧。
到处走走,回去也有个念想。姥姥眼睛有些湿润。小姨看见了,也不忍再惹姥姥伤心,便一路装作欢喜。
自然之美,可以让人忘记自身的渺小情感,成片的芦苇菖蒲,以及白鹭野鸭的鸣叫,让人顿生清凉之感。真想不到,从前的荒野如今竟变成了这样的美景。大家感叹道。
表妹拉着小姨,不停地拍照,芦苇,野花,木桥,摆着不同的姿势。姨夫则陪着姥姥,一直走在最后面。
走到一丛黄色的旋复花前,小姨忽然站住,伸手摘下一朵来。定睛看了看,抬头四顾,然后说,不知道艾娃的坟,还找不找得见。
艾娃的坟?我大睁着眼睛,惊讶地问,你是说艾娃已经……
是的,艾娃早在二十年前,就已经不在了。说着,小姨讲完了最后的故事。
艾娃嫁给工人小伙之后,引得众人一致羡慕。所以虽然结了亲,也是疼爱儿子,顺从儿子的意见,实际上他们从内心里对这个姑娘和她的家人都是看不起的。自艾娃进家,就一直不见公婆的好脸色,丈夫在家时还好,每时丈夫出门去上班家里剩下公婆二人,基本是拿她当佣人使。艾娃天生柔弱,自己既没有工作也就没有收入,自觉理亏,只能忍耐着,也不向丈夫诉苦,只有回娘家来,对着父母流泪。父母纵然难过,但是嫁出的女儿泼出的水,也收不回来了,唯有劝女儿再忍耐些时日,好歹年轻人的日子总是长过老人的。
艾娃的公婆总不甘心儿子就这样在厂里一辈子,想尽办法寻到一个外出上学的名额,将儿子送了出去,小伙子新婚不久,心中虽有万般不舍,也奈何不了前途事大,便依依不舍地去了外地的大学。哪知他前脚走了,后脚家里就发生了事情。起先艾娃腹部隐痛,也不敢在公婆面前说,只悄悄忍着,以为忍过几天就好了,然而过了几天,不但不好,反而愈加严重,她本来孱弱,一有疼痛更是连床也不能起了。婆婆见状,刚好寻的机会出气,便冷言冷语一顿数落。再是穷人家的女孩子,自尊也是有的,便挣扎着起来洗衣煮饭。一拖再拖,有天早上,竟昏迷着不能醒来,婆婆感觉事态不妙,才回艾娃的娘家来,叫亲家去看。可怜一个仙女一样的姑娘,只见了母亲最后一面,送去医院后就再没有醒来。宫外孕造成的大出血。
等那小伙子赶回家来,丧事基本已毕,只抱着棺材痛哭了一场。下葬时同样凄冷,因未曾生养,进不得家坟,而在娘家,已然出嫁,也不能进家坟,便在一片荒地里起了穴,埋下了。
如果不是我,也许艾娃也不会那么早就死了。小姨说。
婚姻这东西,都是前世注定的,定下什么样就是什么样儿,不管什么样,珍惜着过就好。姥姥不知道什么时候站在了小姨身旁。该过去的就让他过去吧。
是啊,该过去的就让他过去吧。
于是,小姨走到一条小溪旁,扬起手臂,把采在手上的花朵洒在水里。水流很缓,那黄色的花朵,在水上婀娜摇摆着,渐渐流向远处。
有风缓缓地吹过来,带动芦苇的叶子,发出微微地沙沙。
小姨,你还和姨夫离婚吗?我侧耳倾听风声。
再说吧。
风好像无休无止地吟唱,从此处到彼处,从耳边到遥远的天际。
他们走的时候,是老舒和我开车送的。我们一直送到站台,帮着把东西递上去。车走了,我忽然有一些说不出来的难过。老舒看出来了,拿手使劲攥着我。
走吧,我说,就一直被他攥着,站台,被一步步抛弃在身后。
过两天我奶奶过八十大寿,你来吗?他在路上问。
得去吧,奶奶都那么大年纪了,不去该说不过去了。我回答。
真的!他转过来,一脸惊喜。
看路!我打他胳膊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