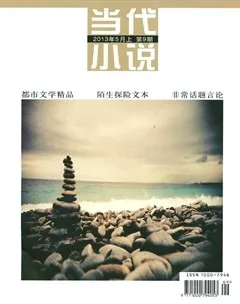一只瓦罐
她瞪着浑浊迷茫的眼睛凝视着前方,灰白的发髻随着头不由自主地摇晃而乱颤着,磨得油光锃亮的拐杖,紧紧地攥在手里,有意无意地敲打着地面。她像一个活的雕塑,每天定点坐在自家朝着街心的门槛上,保持着一个表情,一个动作。
人们已记不清她在这里坐了多久,只有手中磨得油光锃亮的拐杖和同样坐得锃亮的门槛记录着岁月的沧桑。但她已经成了这个古镇上的一景,一个不可缺少的、不加任何修饰的雕塑。
人们来来往往地穿梭于她的门前,有的和她打着招呼,有的已无视她的存在。人们叫着她“石大娘”、“石奶奶”,她老树皮似的脸舒展开来,露出慈祥的笑,头摇晃得更厉害了,摇得细细的脖子仿佛有些不堪重负。
“石奶奶”有一个嗜好,就是喜欢喝生水,并且是自己用瓦罐刚刚从井里提上来的水,直到八十多岁了还保持着这一习惯,每当她喝一口甘甜的井水,人们看到她的眼里总会放射出一种陶醉般的灿烂光芒……
那是几十年前的一个早上,蔚蓝的天空飘着几朵白云,空气里弥漫着野花的清香。八岁的环子由爹领着,去一个新家。新家里有衣穿,有饭吃。
到了新家,那家人哗哗数给爹六块大洋,爹接了,哆哆嗦嗦地放进了衣袋,回过头来抚摸着环子的头:“环子,要听话、长眼睛、勤快点……要听……”爹说着,眼里竟溢满了泪。
环子预感到了什么:“爹!我要回家,我不要新衣穿了,我要回家找娘,爹,我听你的话,我会干很多活,爹……”环子拉着爹的胳膊死死地不松手,生怕爹跑了,哭着求着爹。
新家的娘给爹使了个眼色,示意他快走。爹狠心地掰开环子的小手,哽咽而去……环子在新家娘的怀里无助地挣扎着,哭哑了嗓子。
就这样,环子以六块大洋的价格卖给了这个古镇上一户人家做了童养媳。
从此环子管这一家陌生的男人叫爹,女人叫娘,男孩春成叫哥。在这个陌生的新家里环子过着谨慎小心的生活,好在这一家人待她很好,新爹新娘也让环子随哥进了学堂。
环子和春成出去玩的时候,伙伴们总在她身后嚷着:“小媳妇,小媳妇!”大她四岁的春成追打着他们,保护着她,环子也跟在春成哥背后嘻嘻哈哈地疯跑着,环子不懂为啥他们都叫她“小媳妇”。
炎热的夏季里,春成放下书包,第一件事就是提上瓦罐,领上环子,到门口的深井里提一罐冰凉的井水。自从环子一进这个家门,春成哥慰劳她的就是这甘甜清凉的井水。从爹放下自己的那一天,环子就是喝着春成递给自己的凉水渐渐止住了哭声。从那,春成就每天提水哄着她,环子也在每天一罐甘甜的清凉里渐渐淡了对爹娘的思念……
春成提水,环子总是微微探着身子,想看清春成哥是怎样把水提上来的。
“往后靠,井边太滑,小心掉下去……”环子听话地往后挪一步。每次提水春成都这样嘱咐她,到春成哥把绳子挽到第五下的时候,瓦罐就会冒着丝丝的凉气上来了。然后,春成就把瓦罐递给她,“慢慢喝,别呛着!”环子接过瓦罐,贪婪地喝几口。春成哥牵着绳温柔地看着她,看她用袖子抹着嘴满足的样子。不管渴不渴,环子总是第一口喝春成从井里提上来的水,这一习惯已经从夏提前到春,跨过了秋,延续到初冬了……
在快快乐乐打闹的童年里,环子渐渐地长大了,长成了一个苗苗条条、清清秀秀的大姑娘,她也渐渐明白了“小媳妇”的意思。随着年龄的增长,环子和春成哥却有了些生分,环子还会在春成的注视下不由自主地脸红。
在环子十六岁那年的冬天,春成和环子圆了房。没改变的是环子还叫春成哥,春成仍然每天为环子提一罐清凉的井水。
就在转过年的春天里,春成应征入伍参加了抗美援朝,环子也在那年的秋天里生下一个男孩,一家人期盼着春成归来,环子更是望眼欲穿。可终究没有盼来春成,而是等来了一张春成阵亡通知单……
环子从十七岁守寡一直未嫁,惟一不改的习惯就是喝用瓦罐提的井水。
儿子长大了,常常看到娘守着瓦罐呆呆出神,再后来,儿子娶了媳妇,然后儿子也有了儿子,再后来……环子彻底地老了,老得从井里提水都有些困难,好在儿子孝顺,总把娘屋里的水缸注得满满的。可娘还是不时提上瓦罐哆哆嗦嗦地去井边打水。村里开始有人说儿子媳妇不孝顺,儿媳听到了劝着婆婆,婆婆眼里闪过一丝泪光,好像还有一些捉摸不透的无奈。以后她就躲着人偷偷摸摸地到井边提水,仍不改旧习……
再后来,环子瘫在床上不能出门。
喝着儿子端给她的开水,但再也没看到她陶醉般的灿笑,她常常看着窗台上的瓦罐呆呆出神。
终于有一天,环子走完了她的人生历程,走时,眼角那一抹余光仍游离在窗台上的那只瓦罐……儿子从那抹余光里又看到了娘满足的灿笑……
从此每到上坟的日子里,环子的坟头上总会摆上那个裂痕斑斑的瓦罐,瓦罐里一罐清清凉凉的井水清澈见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