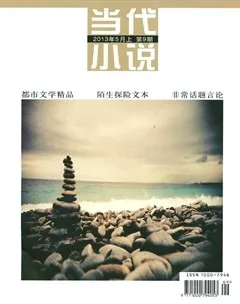盘炕
一
虽说快80岁,但壮壮实实的王老汉,说病就病了。吃不下饭,喝不下粥,眼看着老伴给他买的烧鸡、水果吃不下去。从医生那里回来,老伴说他得的是胃病,但他自己知道,生命就要走到尽头了。
王老汉与老伴吵了一辈子架,但末了他挂着的还是老伴。老两口有三间房的院子,房尽管不好,但修整了,在里面住上十年八年不会出事。他最想的是把外屋的土炕拆了,在里屋给老伴盘一个土炕。老辈子人们睡土炕,日子过好了之后人们睡床了,不知怎么的,鲁西北的乡下又兴起了睡炕。也是的,盘一个炕,炕旁边通一个炭炉子,烧炉子的时候,炕也热了。王老汉对邻居侄子说:“我死了,剩你婶一个人,不如我活着两个人好过日子啊。我在里屋给她盘个炕,冬天暖和些。”
宽着五个坯,长着六个坯,高着一个立坯……老汉望着几块坯和要盘炕的地方算计着。宽五个坯宽了些,只剩她一个人睡,四个坯就够宽了。长六个坯是够长的,长就长吧,除了睡觉,炕下头还能搁几床被褥。
老汉从不到70岁就弯腰了。腰这个东西真怪,说弯就直不起来了,强直也不行。他自己的理论是骨头弯下去了。硬硬的骨头怎么能掰直呢?又过了几年,腰越发弯下去,整个脊背与大地平行了,整个身子像一块角铁一样。老汉确定了炕的大小,就开始干起来。多少天了,吃不得硬饭,只喝点奶,喝点稀饭,感觉力气小了,搬动一块坯有些吃力。但无论如何在咽掉这口气以前要把炕盘起来的信念支撑着他。
白天过去,他洗过手,吃过晚饭,疲惫地躺在床上,就想自己这一辈子。
过去,王老汉父亲的日子在当地算得上富裕,家里有大车有牛,有几十亩地。不然怎么会在划成分的时候划成富农呢。但母亲是个过日子狠的人,他分家时,母亲就分给他一个黑瓷碗。这叫老伴说道了一辈子。无论谁提起分家的事,老伴都说“俺分家的时候,老的就分给俺一个黑瓷碗啊!”直到老来,一提起这事,她眼都是潮湿的。两口子在20岁上,从一个黑瓷碗过起,过得有了儿女,过得有一个像千千万万个家一样的家。
父亲有手艺,会木工活。虽然父亲没教,王老汉也看出了一些门道。在日子实在难过的那几年,他背起斧子锯子凿子下了东北,走百家门子混饭吃。东北的饭也不好混,山东的日子能过的时候,他又背起斧子锯子凿子回来了。在生产队的时候,他一早一晚用斧子锯子凿子干点小活,挣工夫就挣工分。他壮年的时候很有一把子力气,几百斤的小推车,他架起就跑。至今在老人们中还传说着他挖河的时候比赛推泥的事。不知谁出的主意,一河沟子的河工比开了力气。他们把一个小车子装上满满的泥,一个说,“谁能从河底推到河岸,我们一人赏给他一个窝头!”这个过去试着驾驾车子自觉不行,放下,那个也试试不行,放下。只有王老汉拨拉开一堆人驾起了车子推到了岸上。
王老汉力气大,饭量也大。有回赶上伙房吃包子,有人给他在一根扁担上排了一扁担包子,他一个不剩地吃进去了。“王大肚子”的名字别人叫了他十几年,“王大肚子”能吃一扁担的包子的传说也传了十几年。
二
鸡呀狗的又叫起来,天跟人似的也会睁眼闭眼,这时天又睁开眼了。天的眼还没睁明白,王老汉就摸索着穿衣起床了。他走进里屋,把昨天的活儿看了看,就接着干。这边的坯高起一点,他用手往下压压,那边的坯长出一块,他用瓦刀往下砍砍,低了的,他在下面加点泥垫垫。炕在他手下越来越大,越来越像个炕的样子。
他干着,不知怎么就想起了儿子的事。
他儿子的事我最清楚。
王老汉的老伴生的头一个孩子是闺女,生了闺女之后隔了多年不见再鼓起肚子。后来鼓起肚子并生下了一个儿子,两口子乐得就差蹦高了。儿子到了十七八岁,两口子还拿着跟宝儿一样,孩子要啥给啥,骂啥应啥。儿子找对象的时候是在生产队时候,简直难倒了能说会道的媒婆。
媒婆是王老汉老伴娘家的亲戚。每逢集市上,媒婆都坐在王老汉的炕头上,给两口子说道哪家闺女的情况。有的姑娘的爹呀娘的要来相宅子相人了,王老汉一家每次都是把我家的自行车、缝纫机、被子褥子搬到他家去,我的褂子也被他儿子借去穿,可一次次相不成。愁得两口子比愁生了闺女那几年不再鼓肚子还愁。庄稼人的日子都好起来之后,王老汉的儿子才娶来一个媳妇。
三
炕盘到一半多了,老汉感到自己的力气越来越不足。老伴让他再去看看,拿些药,他不再去。他对邻居侄子说,“我这病就这样了,花钱也是白花。我把钱花光了,你婶子的日子以后怎么过呀。剩点钱给她花呀。”想到这些,他自然想到儿女。闺女死去,原来他是指望儿子养老的,可后来的事他想也不敢想了。
闺女嫁到了五里外的蒋庄,女婿是个识文断字、文文雅雅的老师。女婿有工资,家里还种着六亩地,牛呀羊呀都喂着,闺女农闲时还做点小手工活,日子过得在庄里叫人眼热。闺女走娘家,大包小包给王老汉两口子提东西。老两口每次嘱咐闺女,“爹娘不缺吃不缺喝的,来看看爹娘就行啦,每回来拿这么多东西干什么,你们还得过日子的。你们日子过好了,爹娘就高兴了,比给爹娘拿多少东西都高兴。”
闺女总说:“我知道,爹娘拉巴我最不容易了。小时候的事我不知道,但我听人说了。没粮食的时候,你们都饿得不能动了,也舍不得吃口东西,省下来让我吃了。我能活下来有今天的命,不是靠你们的疼吗?” 每听了闺女的话,老汉两口子都一阵心酸。
可好好的闺女说病就病了,去县里、省里都没救过她的命。在她的大儿子就要订婚的时候,她抛下一家大小就去了。想到闺女,老汉的眼泪淌下来,他不得不用手背擦一下。
老汉两口子更没少疼儿子。儿子小时候,老汉走到哪里把他带到哪里。他觉得这是他的骄傲,是他的能耐,儿子要月亮,老子不给他摘星星。
儿子结婚之后,老汉给儿子盖起五间瓦房。儿子说:“你住的三间房子旧了,你过来住新房吧。你住东边三间,我住西边两间。”
老汉说:“我和你娘都老了,不要好啦。我住旧房多少年了,住惯了。你看着屋里没什么东西呀,可真搬起家来,坛坛罐罐的也不少哩,麻烦着哩!再说,老的少的住在一起都不方便。我跟你娘住在旧房子里,愿吃就吃,愿睡就睡。夏天我爱光脊梁穿裤衩子,住在一起,你媳妇在跟前,我还能那么随便!”
儿子被老子说服了。
老汉生过一回病,儿子抓药请大夫跑前跑后伺候。这次病好了之后,身体明显不如以前。儿子说:“你那三亩地甭种了,我种就行了。我三亩地是种,六亩地也是种,费不了什么大事。”
老汉也感到自己身体的衰弱,就不再为地操心。打下粮食,儿子就按地亩数给老汉送来。要磨玉米、麦子,都由儿子送到村子的磨坊里。老汉两口子过得还算滋润。
那年过麦前儿子买了小拖拉机。之所以麦前买,是为过麦的时候轧场用。不光自己用着方便,给别人轧场还能赚些钱。
那年过麦,天好得很,多半个月都是毒毒的日头。麦秆干得一触就折,麦穗干得一触就落粒子,麦子运到场里几乎不用晒就干干的。
村南一大片麦场。麦场里摊着厚厚的麦子。连着几个中午,老汉的儿子都是开着拖拉机在麦场里轧麦。轧下的麦更干了,还发亮。整个大麦场一片干亮的麦秸。
不知从哪里起,麦场里着了火。当有人变了声地吆喊“着火啦”的时候,火已经像流水一样遍布半个麦场了。老汉的儿子见了火,就抓紧调转拖拉机头往场外开,可火像大旋风一样呼啸着追赶他。大火一下就追上他,他急速地追赶火头想脱离大火,可他在拖拉机的一声爆裂中没有了踪影。
四
炕,还有最后一块横坯了。老汉歇了有半点钟,攒足了力气。他把坯揽在怀里,想把坯抱起来。可坯刚刚离开地,他的力气就用尽了。他不相信自己的力气消失得那么快,又歇了一会儿,再次抱那块坯。这次又失败了。他服了,承认了,用这个法子是无法将坯弄到炕上去了。他想出下面的法子:将坯放在炕下,找来一根棍子,棍子下垫上一块砖,将棍子一头插到坯下将坯撬起,撬起一点往坯下垫一块东西,撬起一点垫一块东西。这法子很有效,一会儿将坯撬到炕半截。老汉的汗珠布满了脸,他用手巾擦一把,手巾就被浸透了。
老汉休息了一会儿又接着撬坯,刚又撬起一点儿,在往坯下垫东西的时候,坯一下歪倒了,一个整坯被摔成八块。老汉伤心得要哭。他略歇了一会儿,又将一块新坯重新往上撬。这次就要撬上炕的时候,万万没想到棍子从中间断开,坯掉在地上摔得更碎。他休息了好长时间,换了一根结实的棍子,第三次万分小心地把坯撬上了炕。这时,他脸上的虚汗不再是珠子,而是变成一脸的水。他xmSgeFRQqVglc1+tVRqkfG2bqDj35nC1Ik6hT4NjYXM=手握棍子的力气也没有了,整个身子软在地上。
最后一块坯盘上炕,炕就只剩下上泥了。他没有力气到外面拉土,就在院子里选了一个地方挖出一些土。他觉得力气越来越小,挖挖停停,停停挖挖,挖不几下就冒出不少汗,腿脚发酸。一桶水他提不动了,就用舀子一舀子一舀子地从水桶里舀出水浇在挖出的土上。半天才把一堆土用水洇过来。他又往土上撒几把麦秸,再用镢头一下一下刨,把麦秸和土掺均匀。泥和成了,他没有力气一锨一锨地往屋里端,就用舀子往炕上舀泥。实在累了饿了,就坐下来歇一歇,去锅里舀一点米汤喝,再喝上一点奶。
炕上和炉子上的第一遍泥直到晚上十点多才上完。村子里的十点不像城里的十点,城里的十点都还热闹着,村里的十点,人大都睡下了。村子里很寂静,整个村子恐怕除了有人坐在电视机前看电视,就只有王老汉在活动了。
老汉凭自己的感觉,知道马上就要躺倒了,不能吃口硬饭毕竟已这么多日子。他记得赵家哥哥查出病没三天就起不了床了,没出半月就被埋到西边的地里。老汉要趁着还能动,赶紧把炕和炉子整好,一旦像赵家哥哥那样躺倒,这炕就无法再整。屋里的挂钟敲了一下铃,看来是十点半了,他想再用点时间把泥再抹光一下,明天可以晚起一会儿。可是他的手和脚不听他的使唤,不得不躺着让老伴给他洗了手。
老伴问他:“你还没吃饭哩,喝袋奶么?”
老汉把头摇了摇,话也没说。
老伴又问:“水喝不喝?”
老汉连头也没有摇。
老伴以为老头子太疲劳了,不去再打扰他。让他早一点睡。老伴也靠着老头子睡下了。
老天又一次睁开了眼,寂寞的夜去了。庄里鸡呀狗的又叫起来, 白天活了。
王老汉家还静着,老伴起来摸索着收拾家务、做饭。老伴找不到酱油瓶了,问床上的老汉:“把酱油瓶子拾掇哪去啦?”
老汉不应。
老伴又问,老汉还不应。
老伴朝老汉脸上看,老汉的脸不是正色,过去仔细看,老汉的魂灵已经不知哪去了。
发送了老汉,天也变凉了。里屋的炕已经干透。尽管炕不好看,但也算平整。老伴铺好席子,伸好被褥,生着炉子,打开通往炕里的通道,炉火舌头一样地往炕里伸。这个冬天,老伴可以在炕上暖暖地过了。
责任编辑:段玉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