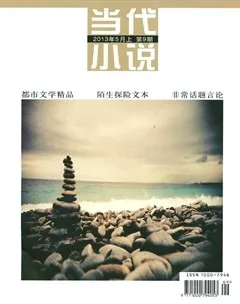奔月
西子的小脸儿怎么长得呢?没有谁会相信,小城里会生长出这样一个水一般鲜嫩的孩子。小脸儿怎么说呢?说他俊俏,太笼统了吧?男孩子长得俊俏的有的是;说他标致吧,有点靠谱了,但还是不确切。这么说吧,这孩子的皮肤像水一样在那里汪着,微风一过,都会泛起波纹来;眼睛眉毛,还有嘴和鼻子,如同画上去的,油彩似乎还没有干。把他比作一颗晶莹的樱桃,或者熟透的葡萄,一掐一股水,一弹就得破,一点都不过分。大概,肤若凝脂这个词就是这么个意思了。这个叫西子的水嫩的孩子,随同其他几个孩子来到剧团的时候,人们似乎掉进了神话世界一般大声称奇。
矜子盘腿坐在床上,安静如一尊雕像。多少个日子,矜子都是这样度过的,一天复一天,究竟有多久了,矜子自己也记不清了。她的生活像一潭死水,从来都荡不起一丝涟漪,而自己又常常会特别快地陷入忧伤,伤起来就痛心戳肺的。她觉得自己的生命正一点一点被时光销蚀,不知在哪一天,就会在这个世界上彻底消失……矜子从窗子里看着几个孩子被人领着走进院子,西子的皮肤被阳光一耀,像一块玉,白洁,细腻,闪烁着晶莹剔透的光泽,在七个孩子中脱颖而出。矜子心中不免一动,动得有点惊心摄魄,目光被那一汪水嫩牵着,不由自主地游移着,眼睛被染得灿烂起来。
下午的时候,矜子知道了那个吸引她的小男孩叫西子。
七个孩子当中,西子是最不爱说话的,就那个年龄最小,个子最矮,一说话就脸红的叫英姿的女孩儿,都比他说话多。西子来了以后,除了点头或者摇头,似乎没说过一句话。都说西子长得像个姑娘,性情也像。
剧团是老剧团,像院子里的那棵老榆树,有年岁了。人也是老的多,脸都像枯树皮了,干涩沧桑,即便是抹上厚重的油彩,脸也不会变得年轻,一抬头,皱纹能把油彩挤得纵横交错,陆离斑驳。剧团正处在青黄不接的当口,需要补充新鲜血液,在小城进行拉网式搜寻,最后滗出了三男四女七个孩子。
孩子们进了剧团,团里没有专门教授学员的老师,就分配给七个有经验的老演员带着,教他们练功演戏,也负责生活。
矜子选了西子。
说说矜子。矜子唱旦角,是剧团的头牌。从前行,演古装戏,十几岁的时候就唱红了,得了个艺名“小金花”。矜子不仅在小城透红,在专区、省城也有人买她的账,戏迷成堆成窝,蜜蜂似的,围着她转。现在不行了,一夜之间,矜子成了“三名三高”演员,资产阶级代言人,是被无产阶级专政的对象。专政最致命的手段,不是没完没了地写检查,挨批斗,是不让上台演戏。对一个演员来说,不让演戏,等于剥夺了她的第二条生命。矜子还年轻,才刚三十岁,花儿正开放的好时候呢。一朵花儿,你不让她开,久了,就灭了。矜子要求带西子,是工宣队侯队长特别批准的。那时候工人阶级领导一切,许多优秀的工人代表从工厂进入上层建筑,成为领导者,用操纵机械的手,掌握知识分子的命运。矜子带西子这事儿,本来很多人反对,说不能把新生力量交给一个资产阶级思想严重的人带,这是路线问题,是大是大非。孩子是一张白纸,能画出最美最好的图画,放在资产阶级分子手里,画出来的肯定是资产阶级的腐朽图画。但侯队长说一不二,如同在工厂里发号施令一样,坚持让矜子带西子。他说,只要权把子掌握在无产阶级手里,资产阶级就翻不了天,想翻天那是蚍蜉撼树,螳臂当车。再说,矜子每个月领着国家的工资,却什么事儿也不干,国家怎么能养活闲人呢?又有人说,西子是男孩子,矜子唱旦角,总不能让西子跟她学唱旦角吧?现在演革命样板戏,台上演的是工农兵英雄人物,才子佳人早就退出历史舞台了。侯队长说,小屁孩一个,指望他学什么,有个人照顾一下,长结实以后再说学戏的事儿吧。话说到这份上,再没人敢反对了。按说,矜子不能也不敢提要求的,她这种人是不能乱说乱动的。可这次矜子提了,而且十分决绝。侯队长看着矜子坚定不移又满含乞求的目光,动了恻隐之心。他突然觉得,这个叫矜子的女人,根本不像一个资产阶级腐朽分子那么可恶。
西子喜欢矜子。矜子长得有点像妈妈,而西子长得极随妈妈。西子的妈妈在县医院做医生,是小城里最漂亮的女人。一次她为一个造反派头头做阑尾切除手术,那个男人突然心脏病发作,死在了手术台上。事故被定性为政治事件,西子妈妈被审查,最后给关进监狱。几天后,这个小城里最漂亮的女人不甘受辱,在监狱里把衣服扯碎,搓成布条,将自己挂在监狱的铁窗棂上。剧团选演员的人,在学校里发现了水一般的西子,通过学校找到了在医院做杂工的西子的爸爸。西子爸爸原来是外科医生,西子妈妈自绝于人民后,他受到牵连,做了勤杂工,手里的手术刀换成了大扫把。他像在手术台上做手术一样干脆利落,没有丝毫犹豫,就让剧团的人把西子领走了。
矜子整天无事可做,领着西子到处玩。小县城也没有什么可玩的,无非是逛逛街,看看人,别让孩子想家就行。玩累了,就让西子坐在自己身边,目不转睛盯着西子看。矜子的目光满含温柔,似有一股水从里面淌出来,暖暖的,似乎带着温度。西子的脸红了,红得非常彻底,连脖子都是红的了。看着看着,矜子突然想:给西子化上妆该是什么样子呢?想着想着,矜子心里一阵悸动。
矜子把房门关了,从箱底取出化妆盒。
西子闻到一股特别的香气漫过来。循着香气,西子看到了那个神奇的盒子——那是一个用白铁皮焊接成的铁盒子,比他上学时用的铅笔盒大多了,也厚。盒子用粉色的油漆漆了,光亮而雅致。盒盖上画了一枝梅花,红白相间,生动灵活,很是夺目。打开盖子,盒子里一段一段被隔开,比他的铅笔盒复杂多了。长长的格子里放着一支支细长的笔,比他上学用的铅笔要细,长短差不多,一头却是尖的。笔头上是扁扁的、短短的毛,软软的,头儿齐齐的,整齐地排列着,如同一个个光洁可爱的小人儿。一个个的小方格里,装的是各种颜色的油彩,赤橙黄绿,分分明明,鲜鲜亮亮。那香气就是这些油彩散发出来的。还有更香的——那是一盒香粉,装在一个精致的圆纸盒子里,纸盒上有五彩缤纷的图案,中间是一只凤凰,展着双翅飞翔。粉盒没有打开,可那香气还是透过纸盒,争先恐后地钻出来。
西子的心一下提起来,气喘得不均匀了,胸口有点堵得慌。他突然感觉,一定会有他未曾经历过的事情发生。
“西子,老师给你化妆。”
“化妆?”西子不知道什么是化妆,为什么要化妆,但他还是点点头。他必须听老师的话,因为老师特别像妈妈。化妆就是妈妈说的打脸子吗?记得很小的时候,妈妈对他说,看你长得细皮嫩肉的,眉眼也精神,生来就是唱戏的料。唱戏就得打脸子,俺西子的小脸儿打上脸子,还不俊死了。西子突然想起妈妈,眼睛一酸,眼泪差一点淌下来。老师正要给西子化妆,西子知道,这个时候不能想妈妈,更不能哭。西子把泪水忍回去,把脸仰起来,等着老师给他化妆。
矜子用温水把干净毛巾浸了,给西子擦脸。矜子擦得很仔细,边擦边看,看得更仔细。擦着,矜子嘴里啧了一声:“这小脸儿。”
矜子开始配油彩。她翘起小指,像一根簪,在一个小格子里一挑,挑起一坨油彩,轻轻抹在另一只手的手掌上。再挑——在另一个格子里……先挑出的是朱红,后挑出的是土黄和白色。然后伸出食指,在手掌上将挑出的油彩慢慢调匀,手掌里的颜色魔术般变成了肉色。矜子的手指秀窄修长,却又丰润白皙,指甲泛着柔和的青光。西子着迷地看着,这双手应该就是妈妈的手,西子是看着这双手长大的。妈妈的手是拿手术刀的,而矜子的手是用来化妆的。
“这是底色,记住了吗,西子?”
“嗯。”西子低头看见,矜子手掌里盛开着一朵淡红色的花儿。
“抬起脸儿来。”
西子再仰起脸,等待着花儿在他的脸上开放。
西子闻到了越来越浓的香气,在他脸上蔓延开来。那是矜子的气息。
矜子翘着手指,两个手掌轻轻对拍着,手里的花儿便变换着形状,然后一朵朵开在西子的脸上。西子白嫩的脸现在变得红润润的了。
“用手掌轻轻往脸上拍,要拍均匀,这就是拍底色,记住了吗?”
西子的脸还仰着,不能点头,就从嗓子里“嗯”了一声。
矜子又翘起小指,从格子里挑出一点大红:“现在开始打眼影,西子,闭上眼睛。”矜子伸出无名指,在手掌上把大红调匀,然后轻轻在西子眼眉之间点抹——大红似一片渐渐晕开的云朵,弥散在西子的眼窝里。西子睁开眼,脸上有了层次感,眼睛开始有灵气闪出来。
开始画鼻梁了。矜子捏起了细细的眉笔。矜子用眉笔把黑红色油彩调成褐色,在西子鼻梁两侧各画了一笔,然后翘起无名指,将画上的笔线轻轻向鼻翼两侧下摊——浓彩渐淡,至边缘,若有若无了。矜子退后两步,眯起眼睛看,西子的鼻梁已是通天耸起。
拍了腮红,可以定妆了。矜子打开了粉盒,西子的鼻子不由重重抽了两下。
“香吗?”
“嗯,香!”
“闭上眼,别喘气,开始扑粉定妆了……别把粉吸到嘴里去。这粉别看闻着香,吸到肚子里就有毒了,会生病的。”
……用细毛刷子将脸上的香粉扫掉,西子的脸已经是秀色可餐了。
描眉的时候,矜子有点犹豫——西子是男孩子,该画剑眉还是柳眉呢……记得老师给自己第一次化妆的时候也犹豫着,说,这孩子的眉毛就像两条柳叶,根本不用改笔,照原样描上就够好看……柳眉吧,矜子想,就柳眉——像自己的眉,反正画着玩呢,也不是上台演出。
描完眉毛,再勾眼睛。西子是单眼皮,眼角微微向上挑起,是典型的丹凤眼。矜子心里想,这孩子的眼睛就是为唱戏而生的,不用费什么事,就照着眼廓稍稍一描,这双眼睛就精神得无与伦比。最后抹口红了,矜子说: “西子,把嘴张开,用牙齿在里面把嘴唇绷起来。”西子试了几次,不得要领。矜子就做给西子看——矜子的嘴微微张开,牙齿努力向外扩张,两片嘴唇就绷起来了。西子看会了,照样子做。矜子用无名指点了玫瑰色的油彩,顺着西子绷紧的嘴唇,上下左右抹了几下,西子的嘴唇便生出无尽的妩媚来。
擎着镜子,西子不相信里面的那张脸是自己的。
矜子让西子站在门口的光亮处,自己则退后几步,仔细端详着那张脸。看着看着,矜子满意地笑着,脸上放出了奇异的光彩。
十五岁的矜子,那时也是这样一张小脸儿,葱嫩恬静,生动鲜活,一出《红娘》唱红了省城,连续演了半个月,天天满座。剧场门口的广告牌上,“小金花”三个字大得站老远都能看见。从此,矜子一跃成为团里的台柱子,剧团因为她而声名远扬,走一处,红一片。现在一切都反过来了,一夜之间,她成了资产阶级的代言人,腐化堕落的名演员。大字报贴了满院,满墙上都是打倒她再踏上一只脚的大字,名字上还打上红叉叉。批斗会开过无数次,翻来覆去就资产阶级腐化堕落那些事儿。那时候,她觉得这个世界一下子颠倒过来。一个演员,受点委屈能够承受,反正满世界挨批判的人多了去了,习惯了就无所谓了,关键是她从此不能再上台演戏,不能化妆了。那些油彩对她来说,就像各种颜色的血液,流动在她的身体里,色彩斑斓,生机勃勃,人活得精神,昂扬。现在没有了,凝固了,她的生命似乎也跟着停止了。
看着西子那张活脱脱俊美的小脸儿,她的生命又活了,活得痛快酣畅,活得肆无忌惮。她好想伸开嗓子大声唱几句,或者喊几口,只要能出口气就行。但她没有唱,也没有喊,像她这样的人是不能乱说乱唱的。她不能唱,也不能喊,但她可以把心里的喜悦搬运到脸上,她可以和悦而舞。舞是无声的,没有人能听见。矜子在晾衣绳上拽下两条毛巾,一手一条,抻开来,左右抖展,上下翻飞,满屋子风生水起,云飞霞舞。西子看得呆了,他没见过如此美妙的舞蹈,更没见过如此美妙的一个人儿。渐渐,舞动的矜子幻化成妈妈的影子——妈妈穿着雪白的大褂,像一只白色的蝴蝶,在他面前飘飞。
矜子舞得够了,丢了毛巾抱住西子,把一张脸贴在他的胸口,不停地摩挲着,眼里的泪大颗大颗滚落下来。
西子终于挣脱矜子的怀抱,走到院子里。
外面的阳光很灿烂,西子的脸在阳光里熠熠生辉,把整个院子耀得透亮。人们都看得呆在那里,木偶一般一动不动——从没见过如此标致粉嫩的一个人儿,浑然是不知何年何月了。唱彩旦的三凤扭着肥沃的臀,一步三摇,一惊一乍:娘娘哎,这小脸儿,俊得没边没沿了,莫不是仙童下凡了!
侯队长看着西子,目光变得呆滞,继而惊异。他想说点什么,嘴唇动了动,却没吐出半个字。他转眼看到站在房门口的矜子,眼睛一下子活了——矜子像换了一个人,目光熠熠,光彩照人,脸上还透出一种少有的温媚。侯队长咽了口唾沫,喉咙“咕噜咕噜”响了两下,眼睛不动声色地在矜子的脸和胸之间盘桓着。然后,侯队长正了色说道:“看什么看,都把个孩子画得妖精一般,像什么话!谁干的?是你吗矜子?都散了吧,该干嘛干嘛去。”
人散去了,院子里只剩下三个人——侯队长、矜子和西子。
“矜子,晚上到我办公室去一趟,看我怎么批判你!”侯队长撂下一句话转身走了。侯队长的目光冷峻而严肃,像刀子一样,西子被扎得一阵瑟缩。
矜子没工夫琢磨侯队长的话是祸是福,她已经习惯了这样没有来由的训斥。她三两步跑过去抱起西子,在院子里转起了圈子——一圈,两圈,三圈,无数圈……矜子飞起来了,西子飞起来了,天旋地转,风起云扬,一直飞到天上去了。
终于转得累了,矜子突然想起了什么,拉起西子,向大门外走去。正是中午,骄阳如火,街上的行人三三两两,显得很冷清,偶尔有两条狗追逐着穿街而过。矜子拉着西子一直朝街的深处走去,来到一座房子前,矜子停住了脚步。西子抬头看去,房子门口挂着一个牌子,上面写着:红星照相馆。矜子要给化了妆的西子照张相片,让西子俊俏的小脸变成永远。
照相的是个有些年纪的男人,他扳着西子的脸看过来看过去,总是看不够。男人粗声粗气地说:“这孩子的脸怎么长得,跟画上画的似的,这是您的孩子吗……我照了一辈子相,丑的俊的见得多了,从没见过这么水灵的孩子,啧,啧!”矜子微微笑着,不说是也不说不是,只是伸出手在西子头上轻轻抚摸着,一下一下,抚出了绵绵的爱意和满足。西子在矜子的抚摸下,温顺得如同一只羊羔,眼睛水汪汪的,化了一般。矜子说:“师傅,您费心好好给孩子照啊,多要钱我给。”男人呵呵一笑说,“你开了单子的,不会多收钱的。不用你说,我当然会好好照,这么俊的一张小脸,不好好照对不起这相机。再说,我自己要保留一张的,以后会有用的……”说着,男人让西子坐在一个凳子上,然后打开了灯光。西子的脸让灯光一耀,更是鲜亮灵动,光彩耀目。男人呆呆看了一会儿才醒过神来,走到照相机后边调整镜头。男人用照相机上的黑布把头严实地蒙了,砰砰喳喳摆弄了一阵,然后露出头来看着西子说:“好,很好,别动了孩子,看着我的手……”男人举起一只手在空中晃着,另一只手握着一个圆圆的东西。西子的目光跟过去,觉得那只手那么陌生,但又有一种说不出来的亲切。西子听到那男人隐隐的声音:“笑一笑……”西子微微抿起嘴,“咔嚓”一声,西子的小脸儿在那天的中午,永远地定格在那个男人的相机里了。
夜幕降临,柔和闲适的天色若有所思,星星若明若暗地点缀在天空。西子站在院子里,呆呆地望着天上,任思绪无边无沿地游荡。西子想起了妈妈,妈妈死了,永远也见不到了。妈妈曾说过,人死了会变成天上的星星,可哪颗星星是妈妈呢?西子又回想着白天发生的一切,真真切切,又朦朦胧胧……矜子怎么那么像妈妈呢?难道是妈妈死了后变成了矜子……终于想得累了,该睡觉了。西子舍不得自己的小脸儿,用一块干净的手帕蒙上,小心翼翼躺在床上,一动不动。西子做了一个梦,梦见自己也飞起来,和矜子一起,在月亮上载歌载舞。突然,他变成一只白兔,乖巧地依偎在矜子怀里。矜子翘起手指,在他的脸上轻轻描画……突然,矜子的身体急速向下坠落,云彩在他们身边,如同一片片棉花被撕碎,漫天飞扬。西子惊醒了,他打开灯,下床拿起镜子照着自己的脸,还是睡觉前的样子,明亮,鲜活。那晚,别的地方发生了什么,西子不知道,他只知道,自己还拥有一张明媚光鲜的脸。
西子站在院子里,早上的阳光照射在脸上,暖暖的,痒痒的。剧团的人隔了一夜,又看到了西子化了妆的脸。过了一夜,西子的脸还是那么水灵,灿烂。有人觉得,西子的脸可以永远这样,像一朵永不凋谢的花儿。这孩子的脸怎么长的呢?这永不褪色的妆是怎么化上去的呢?
西子站在院子里等待一个人,等待那个为他化了这张脸的人。
可那个人始终没有出现。西子眼睛里的光渐渐暗下来,心颤颤地发慌,像被什么东西一下一下揪着。
有人问:“西子,你站在那里一动不动,是在等什么人吧?”
西子仍然不动,一动不动,眼睛看着那个紧闭的房门,还有房门上那把锈迹斑斑的大铁锁。
“西子,矜子去剧场了,你在这里等不到她的。把脸洗了吧,油彩干了,扒在脸上蛮难受的,会伤皮肤。好孩子,乖乖,听话,啊。”一向泼辣的三凤在西子面前,竟然变得温柔无比。
西子看看三凤,再抬头看看太阳,他想:早晨的太阳是月亮变的,妈妈曾说过,月亮是水做的,它的光洒下来都会变成清凉的水,有水浸着,油彩不会干的,他的脸也不会干的。
侯队长走出办公室,他看到晨光里的西子。西子也看到了侯队长,他从这个男人的眼睛里读出了什么。西子一下就看穿了他的眼神,那是一种野兽吃饱喝足后,满足而慵懒的眼神。他敢肯定,昨晚,眼前这个男人一定对矜子做了什么,因为他白天那令人战栗的眼神一直让西子感到忐忑不安。究竟是什么,西子想不出来,但他知道,他的老师面对这个男人的时候,一定是一只羊面对着一只狼那样危险。西子顾不得多想,狠狠盯了那个男人一眼,然后拔腿向剧场的方向跑去。
剧场里空无一人,一排排的座椅冷清地呆坐着,死气沉沉,上面布满厚厚的灰垢。剧团一年中演不了几场戏,剧场时常空闲着。
西子从没进过剧场,这样的空旷和寂静让他感到害怕。
“西子,是你吗?”
矜子的声音似从天而降,在空旷的剧场里,荡起绵绵回音。
随后,西子看到,一个白色的精灵像一团雾飘落在舞台上。
矜子一袭白衣,如云似雪,玉树临风。长长的水袖缓缓拖在地上,如同两条瀑布飘然而落。西子看到,化了妆的矜子,姿容曼妙,亲切柔媚,那张脸竟然跟在镜子里看到的自己一模一样。
西子一步步向着舞台走去,矜子身上似乎有一根无形的线,牵引着他。西子看到,舞台上站着的竟然是妈妈,穿着白大褂的妈妈。
“西子,你为什么不把脸洗了?”
西子一惊,妈妈又变成了矜子。
“西子,老师在问你话呢,你怎么不说话?你怎么不把脸洗了?时间长了会伤皮肤的。”
“我想带着它一辈子,我喜欢老师给我化的妆。”
“西子,你呀——”矜子竟然一阵哽咽。
“老师,你也化了妆,真好看,你是在演戏吗?”
“西子,老师不是演戏,他们不让老师演戏了,老师永远不能演戏了……老师要走了,老师要上天去了呀——”
话音未落,矜子双手并举,修长的水袖直指云天,一旋,一抖,随即飘飘忽忽,水一般落下来。又见矜子莲步轻移,似一朵云霞在舞台上飞扬起来。
凌空驭气出凡尘
又见王爷随后跟
急急忙忙往前进
回看下界雾沉沉
行来觉得星辰近
也不知何处可安身
矜子的声音忽而清朗,明亮,悠悠扬扬;忽而悲戚,暗淡,如泣如诉。矜子的身影如蝴蝶一般飘逸,在舞台上飞来飞去,悄无声息,如影似幻。
西子看得呆了,浑然不知自己是在天上,还是人间。
西子看到,阵阵香风从舞台上飘落,一阵浓似一阵,撒满了整个剧场。西子惊叹:原来香气是可以看到的。西子恍惚间,感觉自己也飘上了天空,忽上忽下,左右飘曳……
“且住,适才饮酒之间,见那人间夫妇,对对成双,团圆叙乐;想我嫦娥终日在这广寒宫内,清清冷冷,冷冷清清,思想起来,好不烦闷人也!”
碧玉阶前莲步移
水晶帘下看端的
人间夫妇多和美
鲜瓜旨酒庆佳期
……
想嫦娥独坐寒宫里
清清冷冷有谁知
矜子的声音充满悲凉,如风如流,在空荡荡的剧场里穿插,游荡。
突然,矜子的声音戛然而止,像被一刀砍断了似的。西子一声惊叫,然后从天空坠落而下,两行清泪顺腮流泻,脸上的油彩变得含混不清。
西子低下头不敢再看台上的矜子,他希望矜子永远呆在天上,不要下来。
西子抬起头时,已经看不到矜子的飞舞,矜子像一朵云跌落尘埃。
“老师——”西子扑上舞台——他看到,矜子倒卧在地,嘴边一摊殷红的血,花儿一样灿烂绽放。再看时,竟然是一轮血红的月亮,在地上慢慢浸开。
突然,阳光从剧场顶端的天窗上倾泻而下,霎时之间,光灿鲜明。
西子相信,矜子已经飞到月亮上去了。
若干年后,西子成了剧团的头牌青衣,他是那个地区内众多剧团中,惟一的一个男旦演员。西子的成名作是《嫦娥奔月》。
责任编辑:段玉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