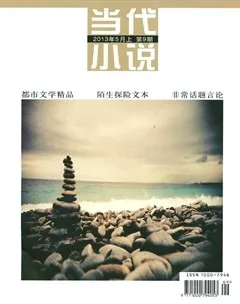享福
小河在群山间袅绕,七弯八拐,绕出了一条条山弯,一簇簇村落;受地势所限,这些村落大多单家独户,山下有一户,山上有一户,半山坡里还隐了一户,伸着半截墙瓦。一个村的十几户人家住得分散,可是能伸伸腿儿的地方并不多,你家不如意,人家也不一定就过得快活。可龙田和那儿,那河坎儿上,一棵老桑树下的一幢低矮的土坯房,却是大伙儿伸腿便去的一个好场所。
一个单身汉,上无老,下无小,没有老人要讲礼节,也无小孩怕受吵扰,进门更不担心要看女主人的脸色,他欢迎,那一家就欢迎,他快活,那一家就快活,一跨进那门槛儿,那一屋劣质的香烟雾中,没有哪一张不是开心的脸。串个门儿,无非图个开心畅快!
主人龙田和更是一个畅快人,好客,大方又风趣。时常提着一个叮当响的瓷茶壶,站在院坎儿上倒茶叶,见了人就在远远地打招呼,不管你是扛着一把锄头从他门口过,还是特意来串门儿,他都连说带笑请进门,递上一杯热茶,敬上一枝香烟,好像他屋的茶随时都备着,那香烟也是抽不完,他热情的邀请中带着只有伙计们才有的调侃和玩笑,让你觉得不进他的门就像对不住人;如果来的是伙计的女人呢,瞥见那胸前的两坨走得一抛一抛的,可上面却撑着一张紧绷的脸,知道来他家串门的伙计坐得久了,误了家里的活了,婆娘来找麻烦了。站在院坎儿边上,正涮洗茶壶的龙田和就一笑,出口的玩笑就开得大了,开得无遮无拦,开得原汁原味儿,开得那一张紧绷的脸,一不注意就挣断了藏在面皮里的橡皮筋儿,本是气势汹汹的女人便在噗哧一笑中,骂一句狗日的龙麻子,撵上前举手就要打要捶。结果是引来一阵更开心的大笑。这一笑就好了,你一笑,他一笑,什么烦,什么恼,都丢到爪哇国了。
孩子也爱到这里来玩儿,远远地,一群小蛆就会对着他的门喊:
今天我出门,
碰到一个人,
满脸的酱油麻子真是吓死人。
大的像菠萝,
小的像面窝,
最小最小的像个钢精锅。
这个人是谁?
就是龙田和!
龙田和开始还张着耳朵听稀奇,不知这些孩子们又学了什么新儿歌,可听着听着就抓起地上的一根儿高粱秸儿,脚一跌,撵上前去嗔骂道:小杂种们的!一群小蛆撒腿儿就跑,像撵着一院场的鸡。
左邻右舍,男男女女,老老少少,都爱到老桑树下的这小屋里来凑个热闹。除了孩子们的疯闹,哪家打工的又给家里汇了款,哪个出门做生意又发了一笔什么财,哪家的小子说了一门亲,亲戚哪天要过门;中央又开了什么会,对农村又有什么好政策,上至国家人事,下至鸡毛蒜皮,都是这里讲座的主题。
来串门儿的,有的纯粹是来散淡散淡,来听听山弯外面的消息,来说一说闲话的。也有什么也不为,只是冲着龙田和的热情,那一杯一杯的茶,那一根一根的烟的。也有伙计们先约好,来打打小牌的。那多半是农闲,该种的种了,该收的收了,或者是连天的阴雨让人下不了田,呆在屋里身上疼了,腿脚酸了,心里也快长霉了,人就是贱嘛,一天到晚不做个什么,手中不摸着个什么活儿就不舒坦,于是站在这山一喊,那山一叫,这边拱出一个,那边冒出一个,打伞的打伞,戴斗笠的戴斗笠,或者就披一床塑料,水淋淋地踩着一脚的泥,朝这老桑树下来了。
玩乐的工具,龙田和自然备得齐,什么扑克,花牌,上大人,玩破了,他又到村头小卖店拿新的,这样的小生意他一年不知要跟人家做多少回。麻将?那没有,也不备,大伙儿只是在一起混时间,顶多一块两块意思意思,小打小闹,说说笑笑,不能搞赌博坏了和气。
家家户户少不了外出打工的,打工的人一走,孩子一上学,家里就只剩下老头儿老妪了,还有年轻些的,也都是背在开始驼,眼在开始花的了。眼望到哪儿都是一幅衰老的景象,男人憋得慌,女人也感到了闷,男人前脚走,女人后脚也跟出了门,抓起纳了一半儿的鞋底儿,也想出门去转转,串串门儿。可三转两转,像有一根绳儿牵着,脚下都不自觉地扯向老桑树下的人家来了。
男人围在一起打牌,女人就坐在一边观战,手里纳着鞋底儿,那绳子一抽一抽地。要不就打毛线,嘴里说笑,手里忙个不停,万忙之中,还时时不忘伸一下脖子去望男人手里的牌,操心着他们的输赢。身旁有一两个女人观战,打牌的男人们就更活跃,全像打了什么兴奋剂,手里的牌抛得山响,愚笨的头脑也突然变得聪明,离奇的想象一个赛似一个,一张普普通通的牌,到了这胡子拉碴的汉子嘴里,就能吐出充满挑逗的丰富内涵来。于是这纳鞋的女人就举着手里的鞋板来打,那边的男人忙将椅子上的身子一歪,嘻嘻哈哈地躲闪。
不够角儿的时候,龙田和自然也上场,不过总是输多赢少;只要一有人跨进了门,他就会站起来,将手里的一把牌忙递过去:来来来,我正好起了一把好牌。来人喜颠颠接过去,低头一扫,马上一脸苦相:龙田和,你个王八蛋——
王八蛋像什么诡计得逞似的一脸坏笑,脸上的麻子挤成了一团,放出灿烂的红光,一边忙着笑嘻嘻地拿起放在桌上的烟盒,抽出一根递上去,嘴里不忘回应着俏皮话;女人被满屋的烟子熏得呛了起来,用手在脸前挥了挥,你们几个烟囱,不抽不行吗?
有打牌的,见女人一旁唠叨个不停,就说,龙田和,把烟也给她一根,把她的嘴堵上!
有了新客,龙田和已重新泡了一壶茶,给抽烟的人又重新上了一遍烟,自己也不忘抽出一支点上,听了这话就笑着眯起了眼,烟我有啊,不知堵不堵得上啊。
就有人起哄,龙田和,你是根什么烟,旱(汉)烟吧?
大伙儿一笑,妇人就知道自己又吃了亏,又把鞋板举起来,就又荡开满屋的笑声。
这一说一笑的,时间就过得快了,感觉是没有坐上好大会儿呢,又到了吃饭的时间了,龙田和就把大伙儿留下来,让大伙儿吃了再接着玩儿。吃也很简单,炖了满满一锅腊骨头,或者漂满一层油的腊肉,下着辣椒,蒜苗,旁边还放了一盆洗好的青菜,瞧那个个红光满面、兴高采烈的劲头儿,像吃着什么山珍海味。
你们倒不客气,说吃就吃上了!有时正围着火笼里的炉子,端着一杯小酒正喝得起劲儿,来喊男人回家吃饭的女人突然出现在门口。女人对自己的男人满嘴的嗔怪,那是在替自己的男人做些客套,可见了一个个狼吞虎咽、红光满面的样子,心想人多吃饭就是抢食,在家吃饭,两人一人坐一方,你弄一桌菜,他总是皱着眉头这碗扒扒,那碗夹夹,一副挑谷子择米的样子,好像一桌的菜都是苦的,咸的,没有一样合他的胃口。
人家又是烟又是茶,男人在人家那里吃了上顿吃下顿,男人脸皮厚,无所谓,可女人脸上却挂不住了,人家一个单身汉,条件再好,也没有供他们白吃、白喝的理儿。做人也讲究个礼义来往,人情往返。于是过了几天,不是这家的女人送来一捆才轧的面条,就是那家的婆娘提来一块腊肉;谁家包了包面,做了包子馒头,弄了不常吃的,也不忘端一碗来。龙田和倒也来者不拒,能吃的就吃了,一时不能吃的也一概收下,到了哪一天伙计们又在一起玩儿,他就指着其中的一个说,张三,我这里有某某某拿来的一块腊骨头,你去把你桂花喊来,给我们弄顿饭。不大一会儿,那叫桂花的女人,必定又叫了一个帮手,两个女人跨进门来了。一阵说笑之后,龙田和告诉那两个女人,米油在老地方,要多少自己去拿,一边乐哈哈地享一回有女人的饭来张口的清福。
本来,这饭来张口的清福,甚至比这还要好的鸿福,在大伙儿看来,那完全是要在蜂蜜罐儿里过的日子,他却不愿去享,宁愿守在这山里,过他这鳏夫寡男的生活;别人梦寐以求的城市生活他却不屑一顾。
龙田和是个麻子,长得丑,可他原来的女人却漂亮,漂亮的女人出门去打工,看上了一个不是麻子的男人。离了婚,他的刚上学的儿子判给了他。也许是心痛儿子没有了母亲,也许这个孤人更看重这惟一的亲情,龙田和对儿子是超出常人的疼爱,下雨下雪,他总是背去背来,送他上学,儿子上下干干爽爽,他却淋湿了一身,天冷下雪,儿子穿得暖暖和和,他还只是一条单裤,背着儿子,一双光裸的脚背却踩在冰碴中。儿子读到了小学三年级,离婚的女人说要把儿子接到城里去读书。女人与他离婚了,父子两人就相依为命,现在儿子要离他而去,无疑是在割他心头的肉。可是为了儿子的前途,他龙田和不要说割肉,就是舍命也愿意。
儿子走的那天,龙田和一天没吃也没有喝,人们看见,自从上午出门来望着那女人牵走了他的宝贝儿子,他就坐在那棵老桑树下的根儿上,一直没挪窝,只是望着那绕出山弯的小河不停抽烟。伙计们知道他心里难受,把他拉到自己家里去,可是这个平时很随和的人,却哪家也不去。到了吃饭的时候,一个伙计的女人要男人端去了一碗饭,伙计去了,才发现那地上已放着一碗饭了,扣着的碗上放着一双筷子,可那饭没有动。伙计放下了手中的碗,给了他一支烟,一句话也不说,陪着他在那里坐,后来又来了一个伙计,也端来饭菜,递给这老伙计一根烟,也陪着坐,抽着烟,都不说一句话。那一天,来了很多伙计,端来了各家最好的饭菜,石坎上摆了七八个碗,地上坐了一地的伙计,有的抽着烟,有的在内心叹息,都一声不响地望着那远去的溪流,那大山隔断的山外世界。远远望着的女人们,也难过得抹眼泪。那是桑树弯最安静的一天,没有说笑声,没有吵闹声,要吵嘴的两口子突然感到了自己的幸福。只有风吹树叶声,溪河的流动声。整个山弯都在为这个汉子难过。
他的儿子一去就没了音讯。人们渐渐忘记他有过老婆,有过儿子,有过家庭。有好心的人想给他撮合个家,可是他总是嘻嘻哈哈,没有一句真话。他人虽丑,却身体好,喂了一头猪,养了一群鸡,还有一头牛,除了没有老婆孩子,别人有的他不缺,别人没有的他也有。虽是土房,却一年四季收拾得整整洁洁,地上扫得干干净净,厨房灶台上洗过的碗还搭盖着纱巾。农忙时耕田拉耙,这家耕了耕那家,农闲时,有了什么副业,村里打段水泥路,修渠道要箍个涵洞,几个伙计一邀,出去个十天半月,门环上别着根棍子,家里的牲畜全靠左邻右舍了,谁要借个什么家具,抽出那门环上的棍子就可进屋找。门关着只是为防野物。
十几年就这么过来了。突然有一天,只给外出打工送钱送信,从不登他家门的乡邮政所的老王,骑着那辆绿色的自行车来到了这桑树下的人家院场,递给他一封信,还拿出一张汇款单,要龙田和在他的投递单上签字。龙田和拿使惯了锄头铁锨的手,拿着那邮递员塞给他手里的笔,显得十分笨拙,茫然无措。
还有什么不相信的,是你儿子给你汇钱来了!摊开投递单的老王催促他说。
一阵铃声,邮递员骑着自行车走了,龙田和拿着信和汇款单,带着疑惑,还像在云雾中。他没什么文化,但却认得那信封上那“龙田和 父亲收”几个字。他那咧着口的粗糙的手抖动了半天,才撕开那薄薄的信封,当他一看见那信纸抬头的一个字“爹”的时候,泪水就滚了出来,他撩起衣袖擦了一遍又一遍,才把那一页并不长的信看完。
龙田和的儿子来信了!龙田和的儿子寄钱来了!得到喜讯的人们比龙田和还高兴还兴奋,大伙儿挤满了那间小屋,争相传看着那封来信。
龙田和,你苦日子到头了,要享福了!
龙田和,准备什么时候走啊?
龙田和笑得合不拢嘴,忙着给来祝贺的人倒茶上烟,说等定好火车票就去。
原来,他那个被女人牵走的儿子,已是一家公司的小老板儿了,能挣钱了,他一直没有忘记这个山弯,这山弯里的爹。他一直没有跟父亲联系,是想等自己有了出息,有了赡养能力的时候,再来报答他。现在他有这个能力了,自己刚安顿好一个家,买了一幢房,谈了一个女朋友也要结婚了,就想把山弯的父亲接进城,去跟他生活,进城去养老。儿子写了信,寄了钱,信上说了,寄来的钱一是要他买些衣服,二是作进城的路费。
儿子在信中告诉了他结婚的日期,这就是说,他这个当爹的要当公公了。进城去的准备是在一弯人的参与下完成的,这个说穿什么样的衣服好看,那个说该配什么样的裤子,有的甚至说既是进城,就要打扮得洋气些,还拿来了一条儿子用过的领带。所有的主意都要受到嘲笑,挑剔,引起一番争论,龙田和成了一个局外人,笑眯眯地望望这个,望望那个,望着那些争得脸红脖子粗,似乎比谁都懂,都内行的伙计们。
最后还是请来了村里的一个裁缝吴老头,请他评判出主意。吴裁缝先是抽着烟,吐着烟雾眯着眼,听大伙儿七嘴八舌说完这做新衣的重要性,然后才睁开眼,那目光像一把尺,把龙田和上上下下打量,像在进行比划。人家当裁缝的就是见多识广,量体裁衣不知经过多少回,打量了两遍,张口就说出这个颜色那个布,还配一顶蓝布帽,人们的面前马上出现一个村干部的形象来。龙田和穿上那身衣服果然是好,要身分合身分,要脸面有脸面,龙田和穿上那套新缝制的衣服,翅膀一样伸开膀子转过去转过来,得到了大伙儿的一致认同。
牛请别人喂——一头牛是放,两头牛也是放;鸡呢,发了鸡瘟,几只鸡都死了,剩下的两个公鸡杀了请大伙儿吃了一顿;一头准备过年的大肥猪,找来了猪贩子,一辆摩托拖走了。儿子结的新媳妇,当公公的不能没有见面礼。
龙田和要走了,村人们有的羡慕,有的嫉妒,失去了这个好伙计,大伙儿也难免难离难舍。这个孤人,这个单身汉终于熬出了头,大家又都替他高兴,况且山不转水转的,说不定哪一天大伙到了那城市,抬头也有一个熟人,一个伸腿路嘛。
龙田和啊,什么时候回来呀?伙计的女人们关切地问。
穿上了新衣服的家伙不改往日的本性,一脸坏笑,怎么,想我呀?嘻嘻——
龙田和走了,人们很不习惯。吃着吃着饭,就不由说起了他。
看人家,老了老了,还成了城里人,多有福!女人无不羡慕地说。
男人一撇嘴,要是我,八抬大轿我都不去——哪比得这家里散淡,空气又好!
女人便露出一脸的不屑:你是吃不着葡萄说葡萄酸!你没人家那个命!夫妻俩说着说着叮起嘴来。
下了雨,或者闲着无事,脚下走着走着,不知不觉又到了那棵老桑树下,龙田和的家门口了。一抬头,见那门关着,门环上别着一根竹棍儿,院场也是久不见打扫的样子,才猛然记起人家早进城享福去了。
没有哪个不这样想,那龙田和是去跟儿子住,是进城定居去了,甚至有人说,那电视中夕阳红的节目里,城里那个打门球的老头儿,好像就是龙田和。
没想到,不到半个月,那龙田和却挎着两个大包回来了。一个帆布大包塞满了旧衣服,龙田和说,儿子媳妇要当垃圾扔,他见都是没有补过一回的,就留下了。做事还可以穿穿么,看得上的,你们挑两件!龙田和拉开了拉链,露出花花绿绿的男式女式的,拿起来抖一抖,果然还是一个补丁也没有的。还有一个包,装的是各式各样的糖果饼干,拿出来摆了一大桌,龙田和一面介绍,一面大把大把地抓起来朝人们手里塞,说,这是我儿子媳妇叫我带回来,请大伯大婶侄子们的。
女人们挑选了一件旧毛衣,或是一条半新的裤子,一手挽在胳膊上,嘴里品尝糖果,见那龙田和不似往日的活跃,病了的庄稼样无精打采,原先脸上那油亮的麻子也像干瘪了的糠壳儿,就关心地问是不是病了。龙田和说,没有啊,我这不是好得很么。
伙计们就委婉地说,那儿子媳妇——
龙田和听出了人们的弦外之音。他说,儿子媳妇对他很好,很孝顺,每天儿子都塞给他钱,叫他自己上街去转,想买个什么买什么,想吃个什么吃什么,媳妇每天把早餐都给他买回来。可是我住不惯,龙田和说,不是儿子媳妇强行留着多住几天,我早就回来了——还是我们这山里好!他以久别重逢的目光,欣喜地望着这小溪流淌的山弯,总结似的说。
这话有人爱听,那个曾经和自己女人叮嘴的男人得意地望了老婆一眼,那神气是说,我说嘛,怎么样?还是山里好吧!
女人却不望男人,接着问龙田和:有吃有喝,又有钱用,你到城里是去享清福,还哪点儿不好?
龙田和这才吐出一口气,向伙计们掏出心窝的话:那地板是媳妇跪着在地上擦的,照得见人影子,伸脚都怕踩脏了,吐口痰都要憋半天!他们一上班,门一关,我像在坐牢,想出去转转,半个人毛认不到,问个路,言语不通,一句话要费力地比划半天。还有一句话龙田和没有说,自己这张脸,这个打扮来打扮去都是一副邋遢相,左邻右舍见了,也会给儿子媳妇丢脸。还是这山弯里好,怎么都好,都舒坦!说着,龙田和像是憋了很久似的,清了清喉咙,很放松,很响亮地啐了一口痰。
从此,龙田和又过上了和以往一样的单身汉的生活,农忙时耕田拉耙,他是耕田的好把式,这一弯的田他包了大半,帮谁家做事,吃饭的问题就解决了。农闲时,有副业就和伙计们出去搞几天,赚几个现钱。没事搞,邀请了一屋人,打打牌,说说笑话,既乌烟瘴气又高兴快活。敬的烟还是大众化的烟,只是敬得更勤,你一支还没抽完,他又一支递上来了,地上是满屋的烟头儿。一天要站在院坎儿边上涮几次茶壶,来一个客,总要重新泡一回,过几天,就会去一趟村里的小卖部,不是买两副牌,就是抱两条烟,两包茶叶。见了伙计的女人仍是嘻嘻哈哈,从没个正经。他们在一起玩,总会有两个女人在那里帮忙弄饭,这回这家提一块肉,下回那家出一回菜。回家没有几天,无精打采的龙田和又活了,能吃能睡了,这个六十多岁的老头儿,是越活越精神,越活越快活,儿子寄钱回来了,媳妇给他寄新衣服了,都是他请一回客,弄一桌菜的理由,吃饭的时候,他还会从衣兜里掏出孙子的照片,给这个看给那个看,如果有人拿着照片,看看照片,看看龙田和,说龙田和,你看这小子的额头,这鼻子,真和你一模一样呃,龙田和就会笑得合不拢嘴,一面骂道,是像我的儿子,哪是像老子!一边却高兴地举起小酒杯,来来来,再干一杯!
大伙儿知道龙田和的儿子有钱,对老子也大方,这龙田和的手头比谁都活泛,谁打着了急,孩子上学,老人看病,或是差钱买种子买农药,只要开了口,三十五十,一百两百,龙田和就是手头没有现钱,也不会折了别人的手指头,他会许你一个期,儿子的钱汇来了,就会取了送上门。什么时候有了,什么时候还,如果你忘记了,他也从不催,见了面照样嘻嘻哈哈,好像他已把借钱的事儿忘记了。人们到他这里玩,烟,茶,那是免费供应,虽然伙计们有时也会出些菜,但是他拿出的总是多数,烟酒茶,看着是些小事儿,但一年下来也是不大不小的一笔账,可是他似乎从没在意过。别人几天不到他家里来,他就会站在院坎上吆喝,仿佛他的茶,他的烟,别人不来,他就喝不下,抽不香似的。
这是一个春天,油菜花儿黄了,桃花也开了,田里的小麦在拔节,院场上的桑树发出了新芽。绿的草,红的花,把一个山弯点缀得多姿多彩。这是春耕到来前的一段农闲时间,大伙儿又凑在龙田和家里抛扑克,笑声一浪一浪地从那低矮的土房滚出来。
正玩得起劲,突然听见了小轿车的喇叭声——如今乡村公路修到了家门口,有小车开进山弯已不奇怪了。眼尖的望了两眼,说:
龙田和,小轿车朝你门口来了!
龙田和,该不是你儿子得旺回来了?
儿子自从出了这个山弯,就从没回来过一回。后来结了婚,有了媳妇,有了孩子,就更不想回来了,他说山里的老家去个人,吃得好,玩得好,空气也好,可就是洗澡不方便,上厕所不方便,两块板子搭在一个粪坑上,人家还怕掉进厕所去。还有猫啊狗的,一有空儿就往床上跳,身上的跳蚤落到了床上,想起来身上就痒。总之过惯了城市生活的儿子对乡村的一切都不习惯了,儿子不回来看他,他能理解,因为他到城里也生活不惯。水稻高粱,各有各生长的地方嘛。儿子就从没有说要回来的话,怎么会是他?
可是,儿子真的就出现在他眼前。随同儿子一起下车的,还有一个打扮娇贵的女人,一个穿着光鲜时髦的小孩子,人们知道那是龙田和的媳妇和孙子。
那个媳妇倒大方,望着龙田和叫了一声爹,然后牵着那孩子的手指着龙田和说,快,叫爷爷!
那小子瞪着滴溜溜的眼睛望了龙田和一眼,说,他不是我爷爷——他这么丑!
你!?媳妇举起手就要打,那小子哇的一声哭了。龙田和忙说,不叫就不叫,别把孩子吓着了。
龙田和的儿子龙得旺,那年轻的主人一进门,一屋的人全都站了起来。那媳妇环望着众人,点一点头,算是打个招呼,可这招呼中分明有一种居高临下的感觉。龙田和的儿子呢,虽然成了人,穿着打扮都是有钱人的样子,曾经像一头鸡窝的头发,现在梳得光滑闪亮,一根根数都数得清,但是那脸相一看还是认得出来,也许大伙儿都老了,他认不出这些人了,他腋下夹着一个鼓鼓的大皮包,见了一屋的人,他谁也没有叫,你主动说一句得旺你回来了,他顶多冲你点点头,下了车就肿着个脸,像谁欠他三升陈大麦似的。这就让人坐不住了,一个个推说有事要回家。龙田和还留着客,可那当了老板儿的小子油光水滑的头却扭在一边。这桑树屋下,辞别的场面头一回显得生硬而尴尬。
不一会儿,一屋的人都走光了,屋里就只留下这一家人了。龙田和这才记起没有给儿子媳妇倒茶,这才慌忙拿起茶杯,用水涮了涮,又抓起晾在墙边竹竿儿上的毛巾擦了擦,要去倒水倒茶。媳妇说,爹,你别忙了,我们有。说着就举起了手里的一瓶矿泉水。龙田和这才注意到,儿子媳妇喝的都自己带着。
那小子见妈也不像真的要打,哭了几声就停了,对放在屋檐下形状怪异的农具感了兴趣。看着那一个木马似的东西,问妈妈这是什么?是风戽。风戽是干什么用的?是车谷用的。什么叫车谷?于是母亲走过去摇了几摇。那孩子玩玩具似的摇着风戽,摇出了一阵风,开心地大笑。
望见了两个圆石盘放在一个架子上,好奇的孩子又问母亲,妈妈,那是什么?是石磨。石磨是干什么用的?于是年轻的母亲走过去取下磨拐作示范,石磨发出了吱吱声。媳妇也曾在农村生活过一段时间,对这些农具自然都不陌生。孩子看着很新奇,很有趣儿,跑过去非要接过母亲手里的磨拐,却没有磨拐高,更不用说推动它。
当爷爷的看见孙子对这些农具感兴趣儿,刚才的不快一扫而光。他傻乎乎地站在那里,望着玩弄农具的孙子笑着,嘴一张一张的,仿佛是在帮推磨的孙子使劲儿。突然想起还要招待一下这个小祖宗,忙端起葫芦瓢,进房屋端出了满满一瓢山里人招待客人的东西:山枣,柿皮,过年粘的米子糖,炒的苕皮子。
爷爷拿起瓢里的东西,向孙子炫耀着,那孩子丢掉失去了兴趣的磨拐,跑过来。
我要吃——他拿起那柿皮,以为是果冻,就要咬起来,这时母亲走过来,打了下他的手:
还没有洗手!——不能吃这柿皮,会得结石的!母亲一把打掉孩子手里的东西,孩子哭起来。母亲捡起几个山枣,要吃吃这,绿色食品。走,我们到河里洗了吃!
母亲牵着孩子出了门,下河洗枣儿去了,屋里就剩下了父子俩。那当儿子的进门来,眼睛就望着这掉了一块又一块的墙壁,那支着几块板子,几根柴,充作楼板的透风的屋顶,这潮湿的丢了一地烟头的地面,这破败又狼藉的老房,脸色越来越难看。
爹,这样的房子,你就住着这么舒服?儿子开口说话了,我们现在又不是没有条件,你怎么就愿意还受这个苦?于是儿子开始回忆父子俩一起走过的艰难日子,讲那些刻骨铭心的当父亲对他这个儿子的疼爱,讲自己怎么发奋,一定要过上城市人的生活,要把他这个吃了一辈子苦的老子接进城享福的雄心壮志,讲那些城里退休的老人是怎样享福,是怎样打发日子过着快快活活的幸福晚年——怎么着都比和一帮老头子窝在乌烟瘴气的土屋里强。儿子所说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动员他进城去享福,不能让别人骂他自己发了财,当爹的还孤独一人在乡下受苦,住这土房子,没孝心。而且您年纪也不轻了,身体会一年不如一年,跟我到城里去,生活怎么说都会有保障,受苦受累一辈子,老了也该好好享几天福——
儿子不能说没孝心,儿子的话也不能说不语重心长,在儿子的面前,龙田和就像一个小学生,一直低垂着头。在儿子回忆父子俩人相依为命的日子里,低垂着头的龙田和也忍不住哽咽两声,动了感情,擦了两下眼睛,捏了一下鼻涕擦在鞋帮上。可说到最后,儿子问到愿不愿意跟他们到城里去生活时,龙田和还是摇了摇头。
真是不可救药!
儿子站起来,带着一种激愤在屋里走去走来,他望一眼他那一身寒酸的老子,满脸是不知好歹,稀泥巴糊不上墙的痛心疾首的样儿。他寄回的钱这当爹的从来舍不得用,他寄多少回来,到了孙子过生的时候,他就会寄多少钱去,有时还有多的,说是给孙子将来读书用的。买给他的新衣服,他总是舍不得穿,至今身上那一套还是他结婚时,收回来的他穿过的旧衣服,问他为什么不穿,说那新衣服等着他死了装棺椁用,免得他们再花钱缝!看看这个有些不知好歹的老子,真是不知说他什么好!
儿子正教训着老子,突然听见门外传来几声喇叭声,知道是老婆等得急了。这次回来,表面上是给住在县城的丈母娘做生的,实际上是他心里是放心不下这个倔强的老子在怎么一人生活,这才千里迢迢开了一辆车回来。他估计自己说服不了父亲,这一趟回家会毫无结果,果然这老子凭他磨破嘴皮,也不肯跟他到省城里去居住。计划好今天要赶到县城的丈母娘家吃晚饭的,这时老婆是在外面催了。
临走,当老板的儿子望着自己曾经生活过的老屋,很不满意地恨了两声,不知道这破土屋就怎么这么有吸引力,一面从皮包里拿出一大包钱来,仍是教训的口气对老子说:再给你寄的钱,你就用,不要再攒着汇回去——军儿读书也不差你给的这几个钱!这钱给你,请人把这破房子推了再做,做它两层楼,钱不够我再给——你就不怕得风湿?!什么热水器,太空灶,彩板门,都装上!
儿子丢下一包钱,走了。过了一会儿,有伙计抱着胳膊踅进屋来。
公子走了?
这土屋,住不好啊。龙田和有些魂不守舍的样儿。
又几年没见着了吧,父子俩关在屋里说了些什么?——原来,大伙儿的眼都盯着呢。
龙田和嘴一呶,对着那桌上的几万块钱说,那,他要我做一幢楼房。
哟?!还要安热水器,太空灶?铺地面砖?那不就是你儿子的别墅了吧——来的伙计嘴上很热情,但眼里望着那钱的目光明显是冷了,像望着一个陌生而富有的外乡人一样。
第二天,下起了雨,这是开春后的第一场春雨,落在那些新开的油菜花上,山坡上那些不知名的碎花上。看那烟雨朦胧的架势,怕是没有两三天就不会停的样子。
按照惯例,这雨天伙计们就会睡到上午十点,从被窝里爬起来,三三两两就要到他这里来报到,这屋里不一会儿又会热闹起来。龙田和烧上了开水,拿出了几截香肠,一块腊肉,洗了煮上了,又拿出昨天儿子媳妇带回来的一根什么火腿,还有其它一些稀奇菜,准备请来串门的伙计们吃顿饭。儿子媳妇孙子,头一回齐齐整整回家来了,总是件喜事。媳妇还给他买回了一条好烟,两瓶好酒,这些他都要和伙计们细细品尝。
可是,当他把一桌丰盛的佳肴端上了桌,摆上了特意准备的好烟,特意准备的好酒,本应热热闹闹、嘻嘻哈哈的时候仍是冷冷清清,不见一个人上门。
他望着炖着香喷喷的腊肉的火锅先是咕咕地响着,冒着腾腾的热气,后来声音就渐渐地小了,没有声息了,最后的一烟热气从锅沿边袅了几袅,倏地扯断了。
守着一桌菜、等着客人上门的龙田和,有些失落地望着门外的春雨,淅淅沥沥、淅淅沥沥洒落进云雾中的小河里了。
责任编辑:李 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