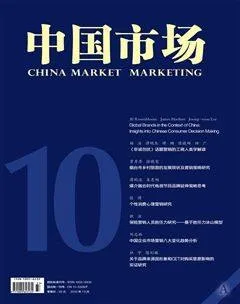都市文学与大众文化
[摘要]都市文学是指20世纪末在北京、上海、南京、广州等大城市出现的一种文学现象,通过绘写现代都市景观,展示都市人在现代社会的生存状态、文化性格,反映都市情绪,彰显都市精神。在整个人类文化发展长河中,都市文学及其所属的大众文化在某种意义上是文化艺术的必然。
[关键词]都市文学;都市文化;大众文化
[中图分类号]I20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6432(2013)37-0165-02
1前言
都市文学在我们国家的现实情况是指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北京、上海、南京、广州等这样的一批大城市里出现的一种文学现象。它产生的文化背景是上世纪末中国社会文化的转型。伴随着中国经济、社会、文化的快速发展与转型,中国社会、尤其是城市,由于经济基础的变动,呈现出一种前所未有的社会—文化形态,即 “消费社会”、“后现代”的社会形态。20世纪90年代文化形态和历史语境的急骤变化,同时带来了文学观念、文学创作、审美风尚的嬗变。基于这一背景,一种不同于早前的文学创作样式—都市文学应运而生。它以当下时代为背景,以现代都市为场景,抒写都市生活,塑造都市新人,并揭示出了一定的现代都市的内在情绪和独有的精神风韵。这是一种与20世纪三四十年代以及20世纪80年代都市文学有着文学渊源但又迥别于上述文学形态的一种新的文学—文化现象。都市文学植根于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中国都市文化,通过绘写现代都市景观,展示都市人在现代社会的生存状态、文化性格,反映都市情绪,彰显都市精神,从而表现出丰富而独特的文化与美学内涵。都市文学已经并将继续表征并催生着中国现代都市文化的转型、生成与建构。
2都市文学的生存状态
从历史上看,都市文学不是空穴来风,,它是传统中国文学从清末的“市民小说”到后来的“城市文学”(都市文学)的一个合理的承续和发展,有着丰厚的文学资源和明确的文学个性。就现实来讲,90年代以来所倡导并有不同程度文学实践的“新写实”、“新状态文学”、“新体验文学”、“新生代(或曰晚生代)小说”,乃至以性别区划的“女性写作”。这些文学实践都成为都市文学的背景和重要构成方面。这类小说对“欲望化生存”的表现,对于“欲望化”的“仰视”、 “顺应”,态度。让人联想到20世纪30年代的新感觉派小说。在新感觉派那里,对于“十里洋场”的灯红酒绿,夜半歌声,奢靡与贪欲,赏玩多于针砭。在一个日益物化的社会里,人为“商品”而生活,“消费”成了人的唯一存在和灵魂,从消费“物”(商品)到消费“身体”(另一种“物”),直到消费“生命”、消费“爱情”……这畸形的现象也反映在那些以上海人生为对象的都市文学。①
20世纪90年代以前的中国城市文化大略可分两段去看。即以1949年新中国成立为界,分为前后两期。这两个历史阶段的中国城市,其共同点是,除开上海这样的少数城市,内陆大多数城市作为经济中心的功能并不突出,主要是作为政治(战时是作为军事)的中心而存在,中国城市乃至整个社会经济比较落后。城市的物质生产、经济生活,并没有从本质上改变中国城市的文化生产和其留居者的精神存在方式。居住在城市的大多数人,就其生活方式而言,基本上是乡村式的。80年代末至90年代是中国社会的一大变局。社会政治的巨大变动,以政治文化为中心的观察社会的视角的变化;市场经济(商品经济)的初步形成,社会物质财富的相对增加,消费主义倾向的萌芽,大众文化的逞盛,最先在城市尤其是部分发展较快的城市得到了反映。都市文学因此有了新的背景和坐标。大众文化语境赋予了都市小说以新的审美特征,文学生产机制的转变催发了新都市文学的发展,而都市文学对大众文化的合谋与反叛,文学关于城市的想象与城市人的实际存在状态的绘写,都市与性别关系的互动等等,在某种程度上又深化了都市小说的内涵。中国都市小说方兴未艾,就其处理生活及其叙事方式而言,还未完全摆脱市井气;就其表达的观念而言,还沾染着现代派的余韵;仅就是在对城市的反讽性描写和对更粗鄙的生活状态的表现方面,才展示了新的都市景观。
我们对于当下都市文化意义上的文学艺术持强烈批判态度,其根本的原因是什么呢?为什么我们认为有价值的严肃文学如此地迅速衰退,而我们极力排斥的作为大众文化的都市文学却广为接受,这难道仅仅是梅内尔意义上的“好的艺术并不是总是流行的”吗?②毫无疑问,当下大众文化意义上的文学艺术的市场化导向、内容的媚俗与形式的粗制滥造等等都是为批评家所诟病的,最基本的原因就是它不同于传统文学或严肃文学审美价值的性质。这里所谓的传统文学或严肃文学,更多的是指自“五四”以来的以启蒙和救亡为主导的新文学,它是西方近现代科学、民主意义上的启蒙主义和在民族危机关头以救亡为己任的国家民族主义文学,尽管它和我国古代传统的讲究修、齐、治、平,讲究立德、立言,讲究经国之大业的文章有所不同,但他们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把大众放在受教育的对立面,传达出强烈的功利目的和说教意识,强调大众应如何如何。如果说在近百年中国历史的特定语境下,这种文学不仅是必须的,也是合理的。而对于现代化过程中今天日益世俗化的大众,则似乎显得不合时宜。他们现在所需要的是实实在在的物质的享受、各种欲望的追逐和满足以及闲暇的娱乐性消遣。对于长期生活在虚假意识形态下的人们来说,无论是以国家、民族名义所设计的乌托邦工程,还是启蒙主义的理想与自由,在世俗欲望的享受与满足面前,都褪去了往昔的色彩,不再对大众具有吸引力。而大众文学所表达出来的对于各种世俗欲望的关怀与肯定,对于生活的游戏态度和十分轻松的娱乐方式,却极大地符合了大众的口味。不过,客观地说,任何一种文化,无论其表现如何世俗,都包含有一种价值关怀。大众文学所表现出来的各种世俗欲望。虽然为传统或精英所抵斥,但却为大众所接受,这也是非常可以理解的。古今中外,处于社会上层的统治阶层或精英阶层,出于自己利益的考虑,总是扼制大众的欲望,这当然一方面是社会物质生产的欠发达,另一方面也是出于自身统治的需要,而他们自己则通过占有大众的劳动来满足自己的各种欲望:食、色、虚荣、贪欲。同时在文化上炮制出一套“存天理、灭人欲”的迷雾来愚弄老百姓以维持社会秩序。事实上,历史上每一次人的解放,不仅仅是精神和思想的解放,也是人的欲望和身体的解放。古希腊时代、文艺复兴时代、魏晋南北朝时代,每一次在一定的程度上世俗欲望都得到较大的肯定。
现代社会工商业高度繁荣,实际上使大众世俗欲望的满足成为可能,大众对物质欲望的要求自然而然超出传统社会统治阶层或精英们所允许的范围,传统和精英们所炮制的抵制大众世俗欲望的精神文化价值系统遭大众遗弃。而大众文化所表现出的对世欲欲望的肯定,应该说是具有历史的合理性的,马克思在其《经济学手稿(1857—1858)》中曾把人类社会发展描述为三个阶段,即人的依赖、物的依赖和个性自由的时代。人的依赖是指个体不能独立,只能依靠群体和他人才能生存,物的依赖是以物的依赖为基础的独立性的时代,个体从人的依赖关系中独立出来,却又堕入物的关系之中。③这一阶段也是为人类进入个性自由时代所必经的物质条件和精神生成所须经历的一个阶段。
3大众文化时代
对于大众文化时代的艺术创作,最为人诟病的就是艺术创作为市场所左右而沦为商品,因而失去了艺术的“自律”。用阿多诺的话说即是从“自为存在”成为“为他存在”。阿多诺本人就是对大众文化持激烈批判的最典型人物。阿多诺关于大众文化的理论被中国当前许多人拿来当作当前文化批判的武器cZludOF0XefTQNQdIrPv3w==。
问题是传统文学创作(大众文化之前)的“自为存在”真的是真正的“自为”吗?无论是西方还是中国,实际上这都不可能,西方的“寓教于乐”和中国的“文以载道”都说明了这一点。传统文学创作更多的是为帝王、为权贵、为上流社会、为宗教、为精英,总之是眼睛朝上,为王牧民。然而牧人和羊的关系又能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呢?艺术没有成为当代工商业社会意义上的商品,但无疑是一种谋生工具,为稻粮谋,图个好身价,或作进身之阶,这是历史上的事实。另一方面,目的不外是维持既定秩序和既得利益。传统社会,受教育作为一种特权,能够创作艺术、欣赏艺术本身就是上层社会的事情……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中国近现代社会向市场经济转型过程中,许多有识之士渴望知识分子通过市场可以养活自己,可以摆脱依附地位获得人身独立和自由……
大众文化时代,艺术成为一种商品,艺术家要得到认可在更大程度上需要大众的认同,退一步说,迎合大众和迎合权贵,在今天看来,后者并不更值得推崇。究竟什么是迎合,我想,不论是传统的迎合权贵,还是今天的迎合大众,决不仅仅是艺术的献媚。无论是得到少数上层社会和精英的肯定,还是得到大众的市场,重要的是骨子里站在哪一方的立场去创作,关键是艺术创作的立场取向。如果这也称迎合的话,那么几乎所有真正艺术家在某种程度上都不得不去迎合。一个作家在某种意义上总是代表一定阶级、一定阶层、一定群体来说话。而表面上的一味献媚和取悦无论在为少数人的传统艺术,还是在今天的大众文化中都不可能取得成功。今天大众文化的精品,为大众承认的艺术品绝不仅是表面的、肤浅的、不关痛痒的媚俗与搞笑,它是从大众立场出发,含有一种平民化的、对大众世俗生活的人文关怀,当然不同于精英社会的高高在上和颐指气使,更不是牧人和羊的关系。④另一方面,大众文化中确实也存在大量粗陋的作品,这正是为精英所批判的,但并不能代表全部。好莱坞影片固然有不菲的商业价值,但其成功绝不能被简单地理解为迎合、媚俗,其众多影片获奥斯卡金奖就是明证。在整个人类文化发展长河中,我们应该认识到,大众文化是历史的必然趋势,是社会发展、民主发展的必然。
参考文献:
[1]茅盾.茅盾全集 [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
[2][英]梅内尔著.审美价值的本性[M]. 刘敏,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
[3]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 第46卷(上),北京:人民出版社,1961.
[4]赵金凤.林语堂翻译转向的原因[J].济南大学学报,2013(1).
[作者简介]宁秀丽(1976—)女,济南大学历史与文化产业学院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