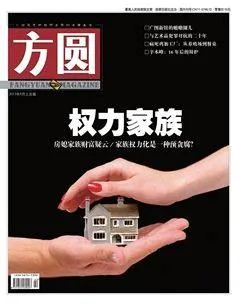伯克利的张爱玲
【√】1995年9月8日,她在公寓里孤独的死去,死后七天才被邻居发现。她死的时候,家徒四壁
在美国访学快一年了,才知道加州伯克利大学还曾经驻足过一位非著名女学者——张爱玲。张爱玲虽然少年得志,说出“成名要趁早”的豪言,但真正蜚声国际,离不开哥伦比亚大学的夏志清教授。
夏志清的文学批评巨著《中国现代小说史》至少挖掘出现代小说史上三位巨匠:张爱玲、钱钟书和沈从文。酒香也怕巷子深,好小说家也需要好评论家,可以说,没有夏志清,就没有张爱玲。夏教授对赴美的张爱玲的帮助也是不遗余力的,帮她作序、写评论、写推荐信,乃至租房子、找工作……
张爱玲来到伯克利也是受益于夏,经过夏引荐,1969年丧偶而潦倒的张爱玲来到加州伯克利大学任中国研究中心的研究员,这也是我做访问学者的研究机构。让一个风华绝代的女作家撰写学术论文和研究报告,显然是明珠暗投,结果可想而知。据夏志清在张爱玲给他信的按语中说,“这封长信是爱玲两年间在加大中国研究中心的工作报告,也可以说是她在美国奋斗了十六年,遭受了一个最大打击的报告。”据说张爱玲在柏克莱期间的写作兴趣,是放在《红楼梦》考证上,因为她有机会在大学图书馆看到脂本《红楼梦》。不难想象出这幅图景,上世纪六十年代,大陆文革席卷神州,美国大学校园内的学生运动也如火如荼,一个寂寥孤清的身影埋首于故纸堆里,醉心于自己的红楼梦世界,隔绝于窗外万丈红尘的喧嚣。
其实,张爱玲不乏洞察力,文学家的时代敏锐性往往高于学者,例如奥威尔的《一九八四》对极权主义的刻画没有哪个学者的论文堪与比肩。从这一点来看,张爱玲可以说是一个先知。看过张爱玲自传体电影《滚滚红尘》的都知道,她1949年留在了上海,1950年还参加上海文艺代表团到苏北农村参加土改两个月,可是林妹妹无法爱上焦大,鸳鸯蝴蝶派的妙笔也无法写出《暴风骤雨》、《小二黑结婚》那种大气磅礴的“歌德”式作品。张爱玲观察到的是土改中农民内心的恐惧和压抑,以至于离开大陆之后,在香港创作出小说《秧歌》与《赤地之恋》,深入刻画了极权体制和有组织暴力渗入乡村社会之后农民个体的生活和命运,为那个时代做了不同于众的记录和背书。
一个敏感而聪明的人注定是个不合时宜的人。张爱玲在1944年到1947年如日中天之际却和有妇之夫的汪伪汉奸胡兰成进行了三年轰轰烈烈的恋爱,爱得很惨烈,她送给胡兰成照片背面写着那句著名的话:“见了他,她变得很低很低,低到尘埃里;但她心里是欢喜的,从尘埃里开出花来。”可胡兰成回报她的是不停的另觅新欢,还连累她差点背上文化汉奸的污名。1955年,张爱玲乘坐克利夫兰总统号来到美国,在新罕布什尔州的麦道伟文艺营遇到了第二任丈夫、65岁的落拓作家赖雅。两人相依为命,赖雅年老多病,中风多次,瘫痪在床,张爱玲不得不从名门闺秀变成了食人间烟火的家庭主妇。
自古美人如名将,不许人间见白头。晚年的张爱玲是潦倒的,两次婚姻不幸,经济拮据,文学创作力萎缩,为了谋生只能给香港电影公司写剧本,消耗了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在晚年的信件中,张爱玲写道“天天上午忙搬家,下午远道上城,有时候回来已经过午夜了,最后一班公交车停驶,要叫汽车,剩下的时间只够吃睡……”被伯克利大学解聘后,张爱玲移居洛杉矶,度过了她的最后岁月。1995年9月8日,她在公寓里孤独的死去,死后七天才被邻居发现。她死的时候,家徒四壁。
我想探寻张爱玲在伯克利的居所,但始终没有找到。让人缅怀的是张爱玲17岁时说过的话:“生命是一袭华美的衣袍,爬满了虱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