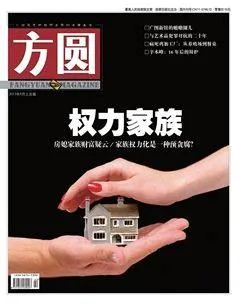大数据时代下,我们还有隐私吗

【√】在社交网络、云计算技术日益成熟,个人信息随时随地都可能被记录下来的今天,我们还有隐私吗
最近一段时间,“棱镜门”事件成为全球关注的热点。据美国中情局前职员爱德华·斯诺登爆料:“棱镜”窃听计划,始于2007年的小布什时期,美国情报机构一直在包括微软、雅虎、谷歌、苹果等在内的九家美国互联网公司中进行数据挖掘工作,从音视频、图片、邮件、文档以及连接信息中分析个人的联系方式与行动。其中包括两个秘密监视项目,一是监视、监听民众电话的通话记录,二是监视民众的网络活动。
消息一出,从美国国内民众到美国盟友乃至全球都产生了强烈反应。在质疑美国政府是否正在使用大数据对公民隐私进行侵犯的同时,人们也在关注另一个问题:在社交网络、云计算技术日益成熟,个人信息随时随地都可能被记录下来的今天,我们还有隐私吗?
隐私权:个人私事免受干扰的权利
提及隐私,现代人可能会想到个人日记、通信通话等个人的隐秘事项,也可能会想到夫妻生活、消费开支等个人的私密事务,甚至还会想到身高体重、电话号码、邮箱地址等个人不愿公开的资料等。没错,这些不愿外人知道、不愿外人干涉的个人私事就是隐私。
当人类开始使用树叶做遮羞布的时候,“隐私”概念就已经在人脑中形成。而“家丑不可外扬”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人们希望个人的隐私得到保护。只不过,受交通、通信等手段和技术的限制,古时的生活不像现在这么开放,“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式的相对“隐居”隔离使人们并没有将隐私视为一种“权利”,即使意识到隐私的重要,凭借自己的力量就足以保护。两次工业革命之后,人类的文明进程大跨步向前迈进。随着交通通讯的发达和交流的频繁,个人想要保护自己的隐私也就变得越来越困难。
适应社会发展的趋势,为对抗他人对个人隐私的干预,1890年,美国私法学者布兰代斯和沃伦在《哈佛法学评论》上发表了《论隐私权》一文,首次提出了隐私权(the right to privacy)的概念。在这篇论文中,布兰代斯和沃伦第一次将“隐私权”作为一种“不受别人干扰的权利”提出来,认为这项权利是个人自由的起点,只有通过界定这项“人类最广泛、文明最珍视”的权利,个人的“信仰、思想、情感和感受”才能得到保障。这种保障不仅仅意味着个人可以对抗他人对其自由的侵犯,也意味着个人享有不受新闻媒体、政府权力干扰和侵犯的自由。
此后,隐私权作为公民人格权利的重要内容,逐渐得到各国法律的确认和保护。进入20世纪后,美国、法国、德国、日本、台湾等国家和地区,先后以法律法规等形式,相继对传统意义上的隐私权、信息网络时代的隐私权等的保护做了针对性的规定。 1948年联合国大会通过了《世界人权宣言》,其第12条也明确规定:“任何人的私生活、家庭、住宅和通信不得任意干涉,他的荣誉和名誉不得加以攻击。”
对隐私的合理期待
“风能进,雨能进,国王不能进”。因家庭住所等相对封闭的个人空间集中了公民的较多隐私,早期的公民隐私权保护也就主要集中在以住所为代表的物力空间之上。
1928年,美国发生了隐私权历史上著名的奥姆斯泰德诉美国案。一位名叫奥姆斯泰德的普通公民涉嫌贩卖私酒,联邦调查局(FBI)的官员在没有获得搜查证的情况下通过对其住宅电话、办公电话的搭线监听,掌握了其犯罪的证据。奥姆斯泰德因此被法院判决有罪。根据美国宪法第四修正案的规定,任何人的人身、住宅、文件和财产不受无理搜查和查封。奥姆斯泰德认为:FBI的窃听行为违反了该条的规定,侵犯了公民的隐私权,所获得的证据应当被依法排除。官司打到最高法院后,最高法院9名大法官最后以5:4的比例驳回了奥姆斯泰德的上诉,理由是:“会话”不属于“人身、住宅、文件和财产”,不受宪法的保护。既然FBI的窃听装置在屋外,就不构成对奥姆斯泰德隐私权的侵犯。
这场官司虽以奥姆斯泰德的败诉告终,但布兰代斯大法官作为合审团的少数派,其发表的“异见”却引发广泛讨论。奥姆斯泰德大法官指出:由于新技术的产生和发展,对隐私权的侵犯已经不需要物理的、强制性侵入,这种新的侵犯正在以微妙的方式广泛地衍生。这种侵犯即使是国家行为,如果没有合法的审批,也应当被视为违宪。
1967年,美国再次发生隐私权历史上另一起著名的案件——卡兹诉美国案。在这个案件中,最高法院确立了“隐私的合理期待”保护标准,成为其后美国和世界其他国家界定“隐私权”的重要参考。与奥姆斯泰德诉美国案类似,卡兹诉美国案中,FBI也是在没有申请搜查令的情况下,在被告(卡兹)的公用电话亭外安装了一个电子窃听器,窃听被告与他人的通话,并获取了被告参与组织赌博活动的关键证据。卡兹被法院判决有罪后,以相同的理由上诉到最高法院。如果按照奥姆斯泰德的判决,FBI根本没有侵入被告住宅,也就不可能侵犯其隐私权。但当时的最高法院已经步入到“沃伦时代”,在首席大法官厄尔·沃伦的主导下,最高法院格外注重对民权的保护,最终认定FBI窃听获得的证据侵犯了公民的隐私权,应当依法予以排除。
卡兹诉美国案是隐私权历史上一个里程碑式的案件。在这一案件中,为扩大对隐私权的保护,判决提出了“隐私的合理期待”判断标准。具体分为主观和客观两个要件:前者是指个人必须表现出对其主张的隐私存在真实的主观的期待;后者则指该期待是社会愿意承认合理的。它把隐私权的保障从原来的住宅扩展到公共场所,强调隐私权保障的是“人”而不是“场所”。如果一个人有意将自己揭露于公众,即使在家中亦不受保障;如果他要维护其隐私,即使公共场所,仍会受到保障。即,已经公共暴露或者明知可能会公共暴露的情况下,公民不得通过主张其隐私权对抗别人的“干扰”。
按照这个标准,虽然住所在一般意义上意味着是可以享有隐私的地方,但如果一个人在自己家里大声交谈,被行人或正好从其房子旁边经过的警察听到,其谈话的内容就不是宪法第四修正案保护的隐私,因为大声讲话的人本身没有期望隐秘。相反,如果一个人在饭店的包厢里关上房门,他的谈话就属于宪法第四修正案保护的隐私。同理,在火车卧铺包厢里的交谈,在飞机上关上厕所门所进行的行为等都应是宪法第四修正案保护的对象,属于个人的隐私。
后来,在1971年的美国诉怀特案、1976年的美国诉米勒案、1986年的加利福尼亚州诉西若罗案、1988年的加利福尼亚州诉格林伍德案等案件中,最高法院通过一系列案例明确像线人窃听、电话银行记录、空中监测、垃圾检查等活动获得的被告“私事”都不属于宪法第四修正案保护的个人隐私权,因为这些“私事”的获得要么属于应当承担的“交流对方向第三人(警方)透漏的风险”(风险承担),要么属于“其他人可以不用花费许多人力、技巧或金钱即可以相对轻易接触到的”(公共暴露)。但是这些判决并非没有争议,也并非为其他国家所全盘接受。这是因为:虽然公共暴露理论具有合理性,但“公共暴露”的认定却并非易事。
“大数据”下重新审视隐私权
20世纪中期以来,随着计算机等相关技术的日益成熟与发展,人类的信息存储和处理能力不断得到扩展,10年前一个普通U盘的储存量只有128MB左右,10年后一个普通U盘的储存量即可达到8GB,是前者的60倍。为了更方便地从事社会管理、针对性地服务消费者等群体,越来越多的政府机构和商业组织重视对个人身份等信息的收集。现在,监视器、摄像头等布满整个城市的每个路口、公共场所、小区、电梯……;信用卡、借记卡、支付宝等消费于整个城市及虚拟网络的酒店、商场、医院……;个人电话、家庭成员、邮箱地址等广泛登记于政府、学校、社区组织……;等等,政府、非政府机构、商业组织以数字化的形式收集了我们各种各样的大量的信息。
当这些被存储的数字化信息达到1太字节(即TB,1TB=1024GB=2的40次方个字节)的时候,就形成了所谓的“大数据”。字节是计算机存储信息的基本物理单位,存储一个英文字母在计算机上其大小就是一个字节,截止2012年人类拥有的信息总量,包括网络日志、音频、视频、图片、地理位置信息等等大概是2.8泽字节(即ZB,1ZB=2的70次方个字节),而且据知名信息行业咨询服务商IDC称,这一数字将在2015年翻一番。
“大数据”不仅仅是数据容量之大,更是数据抓取、整合和分析之大,从本质上来看“大数据”与传统的统计学并无区别,只不过随网络、信息计算技术的发展,数据的搜集渠道多了、计算也更加方便了。例如,在东德,即使号称拥有最强大特情搜集能力的史塔西,也只能做到监控三分之一的东德人口。但在大数据时代,在美国这样的高科技国家,如同“棱镜门”事件所揭示出的那样,通过收集、整合几个跨国互联网公司的数据,就可以对世界上大多数的人口进行监控。
在“大数据”下,公民的“隐私”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第一,当我们被通过立法、电子交易等形式,将个人的相关数据信息以“同意”的名义存储于服务提供商时,按照“隐私的合理期待标准”这些数据信息本身能构成“隐私”吗?如果不能,是不是意味着服务提供商可以随便向第三人披露这些数据信息?例如,交警公开摄像头拍下的行人违章视频是否属于侵犯隐私权的行为?如果不属于,怎能保证不发生类似前两年中国大陆发生的“高速袭胸门”事件?
第二,当我们在公开的互联网上发布个人的生活碎片时,按照“隐私的合理期待标准”这些数字形式存在的生活碎片显然不构成“隐私”,但将这些碎片进行整合分析得出来的个人相关数据信息是否也不构成“隐私”?如果不构成,是不是意味着第三人可以披露这些整合了公共暴露的信息基础上的个人数据信息?例如,根据我们在个人微博上发布的照片、文字,对文字、照片上保护的公共信息知晓第三人或许可以轻易地判断出我们的家庭住址、工作单位甚至电话号码等个人事项,对此第三人如果披露是否会侵犯我们的“隐私权”?
第三,当我们在特定目的下针对特定对象公开了个人的信息后,第三人是否可以对此进行“人肉”并将这些已经公开了的个人信息进行完整地公开呢?如同前一段时间,网上热议的丁某到此一游事件,网友根据其在特定情形下公开的个人信息而披露其“××人,19××年×月×日出生,毕业于××市××小学,现就读于××中学”是不是侵犯了丁某的隐私权呢?
对于上述这三个问题,为保证个人生活的安宁,减少不必要的干扰,或许我们需要重新审视“隐私的合理期待”标准。1988年,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BS)的一名新闻记者根据《信息自由法》向司法部下辖的联邦调查局(FBI)提出申请,要求公开一名犯罪嫌疑人麦迪科(Charles Medico)的犯罪记录。由于个人的罪案记录属于隐私,FBI拒绝了CBS的要求,CBS遂将司法部告上了法院。官司打到最高法院后,CBS提出:FBI的犯罪记录只是各个执法部门记录的一个加总,麦迪科的这些信息,都曾经在某个特定的时候公开过,不能算作隐私。但是最高法院的9名大法官一致否定了这一抗辩理由,他们在判词中陈述道:“在一个有组织的社会里,几乎每一则信息都在不同的时候以不同的形式公开过。但是,就个人隐私而言,不同时期零散地公开和一次性完整地公开,即使内容相同,也有本质的区别。”由此可见,在大数据时代下,存储于“数据库”中的个人数据完全属于法律保护的个人隐私,任何人都应享有控制、编辑、管理和删除关于自己的信息,并决定何时何地、以何种方式公开这种信息的权利。
该怎样保护我们的隐私权
互联网技术的发展使得个人信息存储得时间更久,但搜索起来却更为容易。在特定情形下发布的一些个人信息,过一段时间之后,发布人或许早已忘却,但其他人却很容易在相关事件发生时瞬间搜索到并发布至互联网上。作为享有数据隐私权的个人对此事实上很难阻止。而且,大数据时代下,个人隐私被传播的速度明显加快,个人隐私权在受到侵犯后其后果难有挽回的可能。像丁某到此一游事件,由于他的家庭住址、学校、父母单位等信息已经被公开,并瞬间扩散至全球各地,其想躲避根本不现实。
另一方面,丰厚的商业利润也很难阻止拥有数据库的商业组织不会将收集到的个人数据进行整合、分析和变卖。毫无疑问,大数据的应用给公众带来了巨大的便利,但我们在享受这些便利的同时也将自己的数据信息交给了相关的数据服务商。而服务商之所以不断提高“大数据”收集、整合能力给我们带来便利,其动力之源还在于商业利用。换句话来说,在某种程度上,我们是在以隐私权换取便利,在以牺牲隐私权推动“大数据”技术的日益成熟与发展。
然而,更让人担心的还不是个人、商业组织对隐私权的侵害,而是政府以“国家安全”为名对个人数据信息的随时监控和检视。就像“棱镜门”事件那样,在我们不知道、不经意间,我们的通话通讯记录等个人隐私已为公权力所掌握,而民众对此却难以进行监督。
所以,在大数据时代下,尽管我们的隐私权保护已经扩展到了个人数据,但因这些数据并不存储于我们个人手中,而是掌握在政府、非政府机构以及商业组织的数据库中,保护公民的个人隐私权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困难。但这也不意味着在大数据时代保护我们的隐私权毫无作为可言。
目前,全世界已有近二十个国家制定了专门保护个人隐私的法律,像美国、法国、欧盟等还专门针对信息时代制定了隐私方面的法规。例如,针对政府收集到的个人信息,美国1974年制定的《隐私法》明确规定:行政机关收集保存的公民个人信息,只能用于信息收集时的既定目的;未经本人许可,不得用于其他目的;个人有权知道其信息的使用情况,还可以查询、核对、修改自己被行政机关收集记录的个人信息;针对如何管理与个人隐私相关的数据,美国还制定有《电子交流隐私法》、《计算机查对和隐私保护法》、《联邦信息安全管理法》等。中国也于2012年12月28日通过了《关于加强网络信息保护的决定》,并出台了《信息安全技术公共及商用服务信息系统个人信息保护指南》对大数据时代的个人数据信息管理进行了原则性的规定。
此外,除了期待法律的完善外,作为公民个人也要加强自我保护和监督。要不断提高自己的计算机使用水平,通过密码设置、Cookie管理等来减少甚至防止个人数据遭收集和盗取;更要提高自己的隐私权意识和公民意识,在个人隐私权遭到侵犯时及时根据现有的法律法规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并运用法律法规和网络行业规范中的知悉权及时跟踪自己的个人数据信息,监督政府、网络运营商以及其他网络用户对自己个人信息的使用情况。正如《大数据》一书的作者涂子沛在扉页中提到的那样:一个真正的信息社会,首先是一个公民社会。相信有了公民的监督,类似“棱镜门”事件等大数据时代下的个人隐私权保护终究会找到一个解决的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