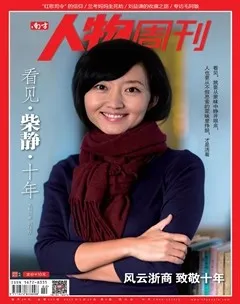柴静这个名字是一场幻觉

大家喊这个名字的时候,其实并不是在喊我
人物周刊:你觉得成名给你带来了什么?
柴静:跟我20岁的时候一样。我在第一本书里面写过,20岁去大学做讲座,大家一起大声喊我的名字,玻璃和桌椅被挤坏了,以至于讲座开不成。保卫处的人送我出来,所有人跟在我后面一起送我。这不叫成名。柴静这个名字是一场幻觉。大家喊这个名字的时候,其实并不是在喊我,我自己很清楚。我看重的是实质,心灵的一种相遇。我知道,人们对我有所认同,是因为我做的这个事情本身的那种特质。我接下来要做的就是好好看护住这份特质。它跟我没有关系。我这个名字怎么被使用、怎么被评论都没有关系,但我把事情看得很重。
人物周刊:怎么看许多年轻人对你的崇敬?比如称呼你为“女神”。
柴静:我觉得不要紧吧。比如说我当年看法拉奇的时候,也有崇敬之心。那个感觉强烈到需要用某一个比较严重的词来表达。然后过一个阶段,可能我又看到她的弱点,试图想要颠覆她、解构她。再过一个阶段,我又会觉得我那样太轻狂了,太骄慢了,又回过头来看人家好的地方,又一点一滴学习。所以人就是这样,你不断地向别人学习,不断地推翻,那你也会经历一个被别人这样的过程。我觉得这样就好啊,这个世界的相互往来才比较丰富。
人物周刊:你以前是好胜心比较强的人吗?
柴静:哪叫好胜心,我这么一个从小在失败中长大的小孩。从小有成就感的一般两类人:一类非常优秀,令人瞩目,我考试从来没进过前10名,不会在这个层面上被注意;一类调皮捣蛋,老师也很喜欢。我就属于最大多数的沉默的人。一切中不溜,从来没有混成班干部,很悲催。一直到上大学,读会计,也是这样,因为你没有这个天分,一堆数字。你就总是泡在失败感里面。
十六七岁读大学,根本不知道职业是什么,甚至不知道生活和工作是什么。更多的是父母的一个想法。那时候除了感兴趣跟同班男生之间的那点微妙感情,啥都不知道。实际上,谁都是这样。你做的好多努力不是为了得到乐趣,比如说你第一个到学校等着开门,或者每天兢兢业业,从来不敢逃学,仅仅是为了不太糟糕,或者说不要被别人注意到你的糟糕。这有什么好胜心可言?是很悲催的人生。
第一排的小女生是最乏味的小女生
人物周刊:书里有一段写,老范老郝去拍你妈妈的视频,你妈妈说,没想到小时候孤僻害羞的你,居然当了记者,居然有了一群好朋友。小时候真这样啊?
柴静:可能我妈都没怎么见过我带同学回家。我4岁上学,太早了,别的孩子至少比你大三四岁。你比别人矮很多,跑也跑不动,话也不那么会讲,不是很聪明。因为矮,我永远都是第一排,一直到高中。第一排的小女生是最乏味的小女生,除了头上落满了老师的白粉笔末之外,没有任何特点可言。别人在那儿跳皮筋,你举个皮筋都举不起来,只能背着手靠在墙边看着。所以我觉得跳皮筋和玩沙包特别好玩。为什么我书里面写老郝给我缝沙包,我们玩得特别开心,那种感觉就像补一场童年一样。
人物周刊:可你没毕业就做电台主持,这是一个很需要跟人心理沟通的职业。这个转换是怎么做到的呢?
柴静:可能这个恰好是因果吧。你内心的渴望是一样的,对吧?你得到的关注不多,你倾诉的机会也不多,但人都是渴望沟通和认同的。做电台,实际上是想建构一个自己的世界,就像一个小孩从来就没有过的东西,他要自己像搭积木一样把它建起来。这是一场幻觉。但这个幻觉成为我真实的一个支撑。我在一个城市里面什么都没有,也不认识任何人,也没有什么钱,那你为了什么,就是为了这场幻觉。
那4年里面,做这个节目我一场都没有耽误过,不管是大年三十,还是冰天雪地。有时候发洪水,从住处出不去,只有翻一座公园小山才能过去。我拿一把伞,勾着树往上爬,腿上全是蚊子包。但也没有自怜,不是说我在做一件很厉害的事。
人物周刊:是觉得应该到那儿去?
柴静:不是应该,是我渴望,我离不开这个,这是我生活里最重要的东西。
人物周刊:在电台的时候除了周末档节目还做什么?
柴静:我比较悲催的地方,我在现实处境里一直混得不咋地,可能就在于,我太不懂人在现实里应该要做一些不一定是你乐意做、但是又必须要做的事。我那时候承担太少了,现在想起来是不对的。台里安排我做节目,我只想做我喜欢的。那你忽略了作为员工的责任吗?那时候我一直到辞职,才去过我们领导家里一次,去告别。他说,哎呀,小柴,三四年了,你才来见过我一次。当时人家还挺不容易把我留在电台里面,我连个基本的人情世故都没有,想起来也不对。开会的时候还老爱背对领导,你说能行吗?
人物周刊:为什么背对领导?
柴静:我桌子就是那样的嘛!大家都是转过身去看着领导,我就在那儿拆观众的信,听就行了。没有人生经验到这个程度,也没有人教我,不自知,只有眼前这一点东西。他们也还算容忍,所以也就傻乎乎的,基本上就做那一个节目。
把生活审美化,人可能得到纾解
人物周刊:跟唐涤非(柴静早年同事)聊,她讲到带你入电台的尚能自杀之后那段时间,做夜间节目的女孩都挺害怕。你那时害怕吗?
柴静:没有。我对尚能更多是心疼。我见过他坐在一个大桌子前,桌子上全是烟灰,可能他抽了很长时间。觉得那应该是他内心特别困难的时候,但我那时候太小了,他也不会跟我说,我也不能冒昧问。怎么讲呢?人们即使是悼念一个逝去的人,也非常容易把他概念化。比如我写陈虻,是要把他生命里原来亮的那部分,再擦亮一下,这个人就在文字之间还活着。尚能也是这样,我记得的都是他的瞬间。他接一个电话,那个男孩一上来就说要自杀,尚能的处理是说:“嗯,那你等一下啊,我点根烟。”正在直播呢!他点一根烟,抽两口,问他,“你抽烟吗?”那个男孩一下子愣住了,说抽。“那你抽什么牌子的呀?”就这样开始谈。这是他自己,谁都替代不了的尚能。我觉得能够记住这些,这个人才能活着,否则凭口而说悼念二字,我觉得是空谈。
人物周刊:你觉得是这些细节构成了他?
柴静:是这些细节里面饱含了这个人的特质。他逝去之后,这些东西不应该逝去。我不赞成把人作为一个工具来使用。比如说,陈虻去世了,媒体来采访,就问:那你是不是觉得他太不注重健康,所以得了胃病?那你觉得尚能是不是太不注重心理健康得了抑郁症?这是不是夜间主持人的通病?我觉得这些问题目的性非常强,我为我的健康杂志或者心理健康杂志在服务,你就把人当工具来使用了,你已经触摸不到他的本质了。我会很戒备这样的东西,也会提醒我自己,我采访的时候不要利用别人,要去感受他。
人物周刊:唐涤非觉得夜间节目的故事常有许多负能量,你化解得挺好。
柴静:我那个节目其实不是谈话节目。谈话节目需要扮演一个教化的东西,或者心理医生的作用,要给对方进行疏导。但我的节目从头到尾就没有过。如果一定要定义的话,应该是把人生的经验审美化了。对生活中发生的事情不是进行干预,而是进行理解来分担。这个分担有时候是用音乐完成的。很多时候我接听热线一个字都不说。
把生活审美化的过程中,人可能得到纾解。这很奇怪。但你看文学或者艺术,力量就在于这儿,它解决不了什么事情,但它又把很多化掉了。就像我昨天在路上看到一个陌生人走过来跟我聊,说我看了你的书,哪个部分我掉眼泪了,他说不是因为你写得好,是因为你写的这个我曾经体会过,可是我没有说出来,你说出来了。我理解这就是共鸣。
六哥他们也不知道我的私生活
人物周刊:原来博客红火的时代,博客名人大都是把个人生活和工作穿插着写。但你写的基本上都是工作内容。你是一开始就有意识地把它当作一个工作平台来使用吗?
柴静:我十几岁就开始做传播了。所以从一开始写博客,就比较清楚这个公共性。我就是一个有机会去采访的人,把大众想知道的信息放到这里。博客就是一个平台,不是属于我的,我的角色是服务。我不是为了让自己成为一个明星人物,也不是为了表述我自己。
其实我做电台也是这样,每天比如说用4/5的时间读大家来信,也会有一个部分,比如开场白是我自己写的,跟我个人的感受和经验有关。我觉得就是个人和私人的区分。什么叫个人?就是我写出来跟大众有共鸣的部分,是我可以放在这个平台上的个人经验。至于我是什么星座,爱吃什么口味,爱蓝色还是白色,大家没有必要、也不会有人有兴趣知道,这个叫私人,根本没有必要与人分享,也没有必要拿出来沾沾自赏。
人物周刊:你对隐私保护得特别好,是很早就有这种观念吗?
柴静:对。不是因为我自己重要,我只是想用这个方式来说,我们中国人素来对公共生活和私人生活的界限不分明。我不光面对媒体是这样,在我生活中也一样。我跟六哥(张立宪)跟罗永浩他们这些这么好的朋友,会互相倾诉内心最深处的东西,但他们也不知道我的私生活。六哥说过一个原则,对你的私生活叫——不好奇、不打听、不传播。你幸福或者不幸福,你有疑问什么,这个可以交流。至于具体内容是什么,不重要。
人物周刊:那跟闺蜜会谈吗?
柴静:比如老范、老郝她们?那会的。因为我们一块长大的,互相拉扯着长的,所以什么都知道。但这样的人世界上有一两个就足够了。她们的我也都参与了。我跟老郝一块推着她娃,在西湖边走来走去,看着她,娃跟我也很亲。血肉长在一块的。有她们就够了。
真正煽情的报道都是无情的人做的
人物周刊:你说自己做新闻初期的时候,更关注于事件本身。后来怎么越来越更感兴趣其中的人?
柴静:因为我后来发现事件是人的结果,是人的欲望、爱憎,互相交织冲突的结果,而不是原因。年轻的时候我认为这是原因,以为一件事发生了,所以人有一个情绪,后来才发现是人有一种诉求,它才产生了事件。那你就回到原点那儿去。所有的认识,其实都从这儿生发出来。什么政治、经济、教育这种宏大的命题,现在问我,我觉得背后也就是人,它是人的心灵和欲望产生交织冲突的结果。那你就回到这个层面上来认识事物好了。
人物周刊:你做《新闻调查》的时候,选题都是猛题,“烈度高、对抗强”要“大地为之颤动”。现在做《看见》,会有一部分社会类题,一部分文化或体育类题。你觉得这两种会有什么不一样?
柴静:可能在新闻价值上,按大家通常的看法有差异,但对我来说差别不大。我觉得每一个人对我来说都是一样的,都是一个了解的机会。人对我来讲永远是一个寻常。调查类的,我去做药家鑫也好,做日本留学生刺母也好,做归真堂也好,都是这里面的人对我来说最重要。以前做调查报道,我只关心得失成败,关键性证据有没有拿到什么的,让我现在再去采可能就会有一些不太一样的地方。回过头来说,李安也好,李娜也好,李永波也好,对我来说也是寻常人。把那份寻常做出来,我觉得就可以。

人物周刊:你很少出来对公共事件发表评论,基本上都是在节目中。为什么?
柴静:我的身份本来就不是评论员,是报道记者。一个新事件出来了,感兴趣最好去研究,去报道,别急着发评论或者上情绪。别刚上了火车,就说我要去某地了,我要采访某人了。第一,有悖于新闻伦理,第二,为什么要大声叫喊呢?你做出来的东西本身才是最重要的。这也是对自己的一个戒备,别让你那点小念头起来就把一个事给毁了。
偶尔也有没忍住的时候,比如说针对“杨武案”在博客上写了《没忍住》。因为那个照片太刺激了,杨武的妻子翻身向那个床的里面,所有的话筒都对着她,照片上有女记者涂的红指甲和戴的玉镯子。她不管这个女人处于一个被强暴之后绝对的内心困境。在自家床上被逼着问最隐私的问题,这是很残忍的。
当时我是没忍住,后来我回想,比如说我是一个20岁出头的女记者,还没有受到过规范的洗礼,也没有来得及太多去感受,突然接到一个指令,让你去采访这个人,第二天要拿回来。我就对善恶重新有一个判断,就是所谓的恶,它未见得是自觉自知的,可能仅仅是因为目的性太强,或者目的太狭隘,此时她看不见别的。也不见得一定要去批判她,而是一个提醒。每个人都是人,也只是人。也不是说要赦免谁或者怎么样,你也没有这个权力,就是批评每一个人的时候,要看到他角色的困境,这需要一个沉淀的时间。
人物周刊:现在常有一个方向,事件的传播很容易悲情主义,不仅新闻如此。你很警惕这个?
柴静:所谓悲情、悲痛,它是一个善恶对立的二元观,它的问题在于它太简陋了。情感本身没有错,新闻不是无情的。其实你看真正煽情的报道都是无情的人做的,他对这个人没有感情,所以他要利用你、消费你。他要煽动,用你来当作一个工具。眼泪掉下来,立刻特写推上去。这是无情的人才能做得出来的。
悲情的人还好点,不一定是为了煽动,是认知的一个模式启动之后造成的。要破解这个模式还是要靠事实,更多的事实使我们看法成熟。
不管是悲情还是武断都是因为太急了,要急着表态,急着宣泄情绪,不如稍微从容一点,慢一点
就像我刚做的江西幼儿园校车落水的事,有11个小孩遇难。我们调查下来,一环扣一环,全是无奈。那条路塌了很长时间,当天有人在那儿铺石子和沙子,幼儿园园长停下来查看了路,一看对面有车子能过去,他就也过,忘了车超载太沉了。但如果那天没人铺石子就不会有事。我们又找到铺石子的人,他说他没修过路,也不知道石子是需要压实的。是有人给他100块钱让他来做这事,他就做了。我们又找到给他100块钱的人,结果是一帮基督徒,看见路已经塌了一年多,怕车出危险,十几个老人只凑得出100块钱,只能买得起这一车沙子,雇人往那儿一摊。他们也很痛苦。再问路为什么塌了一年多没人管,因为底下有个涵洞, 村里养鱼要把那个涵洞挖开让水流出去,水土这么一点点流失。为什么不修呢?因为村公路,国家只能投很少一部分钱,基本全靠村民自己,人均收入才7000块钱一年,没这个钱。你看到的是整个农村的资源困境。但看了这些孩子的眼神,你就不能光停留在这种对悲剧的感叹上面。你还要责问,责问自己,所谓成年人的这个世界到底应该如何建设。
如果用悲情模式,上来就说为什么国家不投标准校车给农村学前教育。但我们的采访车在这个路上一碰到泥水就陷在里面,如果标准校车来了连头都调不了。光有校车有用吗?你说我要求一个有资质的人驾车才可能,它能做到吗?村办幼儿园,一个月工资700块钱不到。你说这是镇政府应该承担的事情。这些事实的复杂结构应该梳理清楚。我觉得不管是悲情还是武断都是因为太急了,要急着表态,急着宣泄情绪,不如稍微从容一点,慢一点。
归属就是创造
人物周刊:《新闻调查》那几年对你来说是很重要的一段时间吗?
柴静:我书里面的大部分内容跟《新闻调查》有关,不光因为它是一个节目吧,也是因为你所谓的青春期最重要的成长,都在那里度过,直接泡在里面,你最强烈的体验都在那儿发生。
人物周刊:这种生活跟以前做电台或者做《新青年》的时候比起来,你更喜欢哪种?
柴静:肯定还是《新闻调查》吧。
人物周刊:喜欢什么呢?
柴静:以前那种,就像我坐在泳池边上,腿在那儿晃荡着,玩一玩什么的。现在是整个人就按在水里了,就没出来过,那种感觉。你全方位,你所有的感官都是跟世界有接触的,而不是原来那样,有塑料膜那样。
人物周刊:喜欢这样更有意思一些?
柴静:当然。你原来有顾虑、有不安什么的,现在也没了,就是全部投入在里面。而且也很重要的是,跟《新闻调查》这些同伴的感情是我以前没有过的。我以前随便去哪儿都行,也不道别,跟谁合作都还不错,但说走就走了。在《新闻调查》不行,出一个差,就跟亲人一样,天天在一起。我也没想到这个工作对生活影响那么深。
人物周刊:2009年离开《新闻调查》的时候会恐惧吗?你说这件事是你写书的一个重要原因。
柴静:恐惧倒没有,眷恋是有的。我是不会那么直截了当去表达的人。所以实际上是隔了3年吧,我今天才把给《新闻调查》同事们的书准备好,给他们每个人送。
人物周刊:为什么离开?
柴静:突然接到通知,台里工作安排,需要调动。
,人物周刊:没有告诉理由吗?
柴静:我觉得也不需要理由,也不用去问。我生活的几个关口,我去《新闻调查》,我离开《新闻调查》,包括陈虻选择我,我都没有问过。只要不是我自己能力所及范围内的事情我不问。
人物周刊:这个心态蛮好。
柴静:我觉得外在永远都是波涛一样起伏,对吧?如果你心有定见,实际上是不会随之摆荡的。如果你感到恐惧,只能是因为你对外界认识不足,对自身认识不足。昨天卢安克给我写信还说到这个,他说他现在也处在一个所谓没有保障的生活里,但他会感到,没有保障的时候人就不会再向外界索求更多,反而更专注内在。他问我是不是有类似的感受,我就想起2009年这次,还有陈虻的去世。对我来讲是离开人,其实去哪儿工作不是那么重要,我对人有眷恋。既然这样,它也会有一个帮助,让你体会什么叫真正的独立,就是世间只有你一人,你会怎么样。
人物周刊:卢安克说,归属比规则更重要。你很认同。这样的事会打破你的归属吗?
柴静:它会重建我对归属的定义。以前我认为归属是在一个集体当中,有志同道合、价值观相同的人做事情。我现在觉得,归属就是创造,就是当一个人能有所创造的时候,你创造的这个东西里面才有你真正的归属。那么回头来看,我们过去在《新闻调查》的归属,也并不仅仅是因为我们几个人的感情了,是因为我们一起创造了一件事情,然后我们同时都属于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