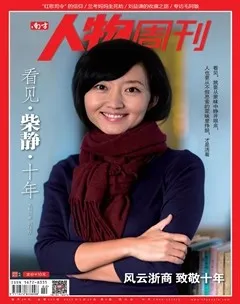父亲林永贵之死
16年前的情人节,父亲乘风而去。十年生死两茫茫:于死者,魂魄已虚无缥缈;对生者,怅惘却未有尽头。
无论是少年求学,还是青年从政,父亲都可算人中翘楚。他是浙江航务学校第一届优秀毕业生,年刚而立,就当上地区某直属部门负责人。在那个讲究成分的年代,他是根正苗红、业务拔尖的代表。他又是非常热心的人,因为在交通部门工作,一年为人代买上海的船票就数以百计。在母亲眼中,他是恋家的好男人;在我们童年记忆里,他是很有学问的人,几乎无所不知。他身上有那个时代很深的印记,他能背诵所有的毛泽东诗词和许多毛选的经典段落。
然而,父亲的形象并不总是高大的。80年代以后,改革渐入佳境,人们的生活和观念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腰包鼓了,房子大了,家电新了,打扮时尚了,说话的声音也渐渐响了。而我们家还是死水微澜,父亲还是言必称毛主席。他好像一个巨人,还来不及调整新的脚步,就被绊倒了。他的目光渐渐暗淡了,他在现实面前退缩了,他不再谈笑风生了,他慢慢成了一个装在套子里的人,活在自己的思想体系里面。刚刚40岁,他的头上已花果飘零了。
改革开放是一项前无古人的事业,对置身于这浪潮中的每个人来说,都是一次洗礼和融合。大浪淘沙,为什么很多人都顺利走过了这一关,而父亲这么优秀的人却始终无法完成他的跨越,这是一个难解之谜。最令父亲尴尬的一幕发生了。母亲在市中心地段开了一家百货店,生意马马虎虎。老街的店面,关门开门都是一件力气活,家里只有父亲能够胜任。父亲也一直在默默地做着,每天起早贪黑,不辞辛劳。尽管赚得不多,可他们都很满意,每天晚上八九点钟关上店门以后,两个人都是说说笑笑回家,也带给我们一屋子的温暖。有一天,母亲左等右等,等不到父亲的踪影,一直到11点才见父亲回来。原来,已到店门口的父亲,碰到了一个熟人,那人随意说笑了几句,父亲支吾以对,红着脸绕回了家。到了深夜,不放心的父亲又折了回来。母亲数落了他几句,父亲先还能够应付,到了最后顶不过,便仰起头,说:我是国家干部,怎么能做违法的事情。到此地步,母亲也只能摇头叹息了。从此以后,父亲再也没有迈到店门半步,百货店很快关门大吉。
在家庭生活中,父亲很民主,我和大哥经常在饭桌上发表与他不同的见解,甚至为了逗他,故意唱反调。他却非常宽容,从未喝斥过我们。我们今天能够拥有平等的心态和别人交流,父亲是有功劳的。然而,民主很快失衡了。在当时中国的思想体系里,改革是争论的主题。温州作为改革开放桥头堡,它的发展又是我们议论的焦点。有一次,我们触犯了父亲的底线。在争论毛公和邓公的历史功绩究竟谁更大时,我们各执一辞。我顶撞父亲:你的观点已经过时了,有本事你到五马街(市中心最热闹的一条街)去叫,看看谁听你的。父亲的眼睛暗淡了下来,接着大哥大概又说了一句对毛不敬的话。父亲气得全身发抖,腾地站起身来,打了大哥一个嘴巴。我们都傻了。

其实,这种事情是迟早要发生的。父亲的这一巴掌,打出了威风,但他明白,他的最后一个阵地也失守了。
自那次家庭风波以后,父亲更加沉沦了。他学会了用酒精来麻醉自己。到最后,他一天要喝6次酒,甚至在上班的时候,关上办公室,用牛肉干和花生米也能凑合着来一顿。每到星期天,他把大大小小的毛主席纪念章拿出来,一边欣赏,一边赞叹,眼中发出柔和的光芒。他真的是“躲进小楼成一统,管他春夏与春秋”了,那一年他才47岁。以至于后来家庭卷入抬会风波,他身患绝症时,我们的心理承受能力已经很强了。康有为先生死后,他的弟子顾颉刚先生说自己是“淡然置之”,因为康有为的学术生命,早在36岁就死了。而父亲在我们的眼中,他的生命仿佛也就定格在47岁,以后的挣扎,主要偏向物质,而非精神上的徘徊了。
1927年,国学大师王国维自沉于昆明湖。陈寅恪先生认定他的死是“文化殉情”。凡被一种文化或价值观所化的人,在文化或者价值观裂变的时代,他是非常痛苦的。他受这种影响越深,他的痛苦就越烈。在我看来,父亲亦如是。
中年退缩的父亲曾经有过惊人之举。“文革”中,父亲和他的同事们在当时温州最高最繁华的建筑温州大酒家上垂下一条十几米长的用草席制成的条幅,向伟大领袖表决心。血沸腾。他还花了6个月的工资,买了一个毛主席像章,送给母亲,作为礼物。一向清醒、沉稳的父亲,为何会有这种宗教式的虔诚,这也是一个谜。
为文化或价值观所影响的人,在时代变革的洪流中,他要做出怎样的选择?是否会因太讲适应而失之圆滑,抑或会因太讲坚持而无法跨越?这是父亲给我们留下的迷惘,也是大变革时代每个人都应面对的一项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