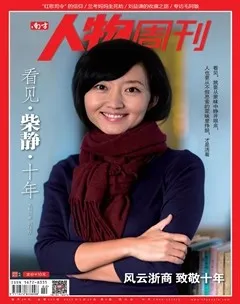东亚的“自杀文化”
去年12月底,当我徜徉于首尔街头,穿行在庆祝朴槿惠当选首位韩国女总统的人群中时,内心的担忧远大于期待。我不想去预测这个被称为“世界最高危职业”的继任者将带给韩国一个怎样的未来,因为这些已经暂时脱离了我的思考范围。
在冬日的寒风中,我的思绪被带回到4年前。
在去年写的一篇《我爱茉莉花》中,我回顾了“9·11”事件之后采访韩国前总统卢武铉的一些轶事。这位谦逊的“平民总统”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当2009年5月23日我接到卢武铉总统自杀的消息时,我首先想到的是臧克家先生那句,“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

卢武铉的确还活着,即使是现在,他也经常会被怀念他的人提起。那一年,在一系列抹黑式的指控面前,他以跳崖的方式结束生命,只给夫人和女儿留下了一封遗书。
“不要太过于悲伤,生和死不都是自然的一个形式?”
“不要道歉,也不要埋怨谁,都是命。”
这封遗书,文字简短而深刻,除了表明自己的清白,一句“毋需怀怨,生死同一”似乎也说明了他面对死亡时的超然。
卢武铉的以死谢罪,只是韩国,甚至整个东亚社会的一个缩影。在这一地区,除了缺乏数据的朝鲜之外,同受儒家文化影响的中日韩三国的自杀率,在近几十年始终居高不下。这就引出一个值得深思的话题——即自杀与儒教,以及东亚传统文化之间有着怎样的联系。
一方面,儒家尊重生命,强调孝道和对家族血缘传承的责任。因此,尽管古代缺少数据的支持,但一般认为在传统的儒家社会,自杀率是极低的。
而另一方面,儒家思想中又有着“士可杀不可辱”的信条。孔子说,“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号召以献出生命来成就仁德。因此,在涉及到社会的一部分阶层时,舍生取义、杀身成仁也成了儒家所支持的行为。
两千多年前,楚国的三闾大夫屈原投江殉国,为后来的仁人志士在绝境中用自戕的方式来表达立场提供了参照;1905年12月,一个绝望的爱国青年在日本东京大森海湾蹈海自尽——他就是写下《猛回头》和《警世钟》的革命派人士陈天华。在中国的历史长河中,这样一个又一个悲壮的故事也为这片土地的自杀文化蒙上了一层浪漫的色彩。
以死明志这种悲壮的气节,往往是坚守儒家理念的士人们的最终选择。当对人格的侮辱达到峰值,当他们的道德判断被不可逆转地推翻,或当矛盾无法解决时,他们就会选择自我解决,用自杀来体现道德。而东亚的英雄主义情结也为这种行为提供了支持,人固有一死,在重于泰山与轻于鸿毛间,士人们通常会做出这样悲怆而壮美的选择。
韩国人的生死观与中国人不同。他们认为,人死之后什么事情都将结束,会摆脱世俗的烦恼,就更助长了自杀风气在社会中的流行。于是,在这个文化怪圈里,明星、政客、企业家都难以幸免。
而文化相近的日本,除儒家文化之外,还受根深蒂固的武士精神影响。武士忠于君主,以切腹作为对自己的最终了断,把死亡当作一种责任去执行。尽管这种制度在历史的进程中逐渐消亡了,但“武士精神”却被日本国民崇尚至今。
因此,与其认为东亚有自杀的传统,不如说“好面子,重原则”的特点和本土的传统文化对自杀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钱锺书说,自杀是一个“弃置而复依恋,无不可忍而又不忍;欲去还留,难留而亦不易去”的过程,一语道出了自杀者的淡定与纠结。但不能否认的是,无论屈原、陈天华还是卢武铉,他们为一个事业而生,远比为之而死更有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