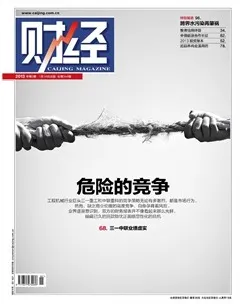“苦力班子”中的老右派
2012年12月12日,雪后天晴,异常寒冷。北京小汤山一家养老院,一间布置简单的房子隔开了门外走廊的吵吵闹闹,年过八旬的老右派张万琨独自一人在门内阅读书报,等待记者的到来。
退休前,张万琨在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委员会(后更名为法制工作委员会,下称法制委)工作,老同事们说他“喜欢抬杠”,是大理想主义者——这也是他参加立法工作的原因。
在法制委,张万琨遇到了一群经历类似的老右派:郭道晖、左羽、王文、江流等。他们一生经历坎坷,青年时期参加地下党干革命,解放初期事业一度顺利,而立之年却被错划为右派,年近“黄昏”才开始从零起步学习法律,进入法制委参与立法。
如今他们中的一部分人已经离世,在世者都白发苍苍,有人卧于病榻,有人仍在为法治而奔走。
在中国百年法治进程中,法制委扮演了具有转折意义的角色。“文革”后的中国,依赖法制委的高效工作,全国人大迅速出台了多部法律,奠定了改革开放以后中国法治基础。比如,仅仅在1979年3月至5月三个月时间内,全国人大常委会以奇迹般的速度出台了七部重要的法律,包括《选举法》《地方组织法》《法院组织法》《检察院组织法》《刑法》《刑诉法》和《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这些法律至今仍然发挥重要作用,前期的立法重担则主要落在法制委身上。
在曾担任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下称法工委)研究室巡视员的周晓红看来,“当时的法制委充满着理想主义,目的非常清楚,就是推动国家的法治进程。”法制委刚刚成立时,周晓红是里面的年轻人,而今她也年近花甲。
在“运动”频繁的国家,树立法律的至上权威并不容易。带着对“文革”后中国向何处去的思索,法制委的老右派们参与到立法进程之中。这是他们人生中最后的工作舞台,在这个舞台上,他们逐渐建立起中国的法律体系,国家由此实现由乱入治。
“苦力班子”
天安门广场西侧的人民大会堂,是中国法治进程的见证者。1979年3月13日上午9时,法制委第一次全体会议在大会堂南段三楼会议室召开。
在“文革”中吃了苦头的老干部们誓言要通过民主和法治,建立起一套能抵挡住“文革”的制度。时年77岁的彭真在这次会议上发表讲话。彭真曾在国民党时期坐了六年牢,在共产党的监狱里则坐了九年半。他曾多次讲,“我从进监狱第一天起就开始思考,这个事是如何发生的,原因就是缺乏法治。”
1949年后,彭真担任政务院政治法律委员会副主任、中央政法小组组长,并兼任北京市委书记。1954年,第一届全国人大召开后,他又担任全国人大秘书长,属于人大的老领导。“文革”开始后,彭真失去党政一切职务和人身自由。1979年复出后,当年6月,彭真当选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并兼任法制委主任,负责立法工作。
解放初期追随彭真的部下,包括顾昂然、王汉斌等人,也在这时重新聚集到他的身边。顾昂然不到20岁就在彭真办公室担任秘书,第一届全国人大召开时,他参加了会务工作,负责出简报。1993年后,他在法工委主任任上一待就是十年。
王汉斌,彭真的政治秘书之一,曾担任北京市委副秘书长,后来出任香港特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副主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1979年王汉斌担任法制委副秘书长兼办公室主任,他曾对《法制日报》记者回忆,法制委成立前,邓小平和华国锋对彭真说,“将来的立法工作就交给你了,由你做主,你要找谁就找谁,你要找哪个部门协助工作就找哪个部门协助。”
王汉斌是第一个被调到法制委工作的干部。彭真最初让他去时,他并不想去,“法律太枯燥了”。彭真就让他到大会堂参加会议,他说进不去大会堂,彭真就用车接他进去。去了之后,他就留下了。
当时的法制委是个老人班子,80名成员,平均年龄70岁。曾任法工委秘书长的岳祥对《财经》记者说,当时“文革”刚刚结束,许多老同志还没有工作,被安排去了法制委。正因为此,当时法制委规格非常高,“各民主党派的负责人、曾在中央书记处的一些人员,都在这个委员会里面”。
据《彭真传》(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记载,彭真认为,只有一个法制委是不行的,还要建立一个为之提供服务、做参谋助手的工作班子,并称之为“苦力班子”。顾昂然回忆,彭真曾对他讲,“目前的重点是抓立法,首先是有法可依。立法任务非常重,我岁数大了,但我也不偷懒,还要有苦力。”
从“和尚打伞、无法无天”到有法可依,立法过程充满艰辛。当时机关的氛围较为简单,内部上下级之间,也很少以职务相称。年轻人称呼年纪大的就加上一个“老”字,曾任法工委研究室主任的高锴是“老高”,顾昂然是“老顾”,甚至学彭真喊他的秘书杨景宇“小杨”。后来,氛围渐渐发生变化,一位已退休的法工委工作人员说,“主任主任的叫,也不知是从谁开始的。机关人员出访去机场还要有人接送,不送还不高兴。”
顾昂然回忆那段紧张的岁月说:“每天很晚才骑自行车回家,还要带上一大包材料接着干。”加夜班时,周晓红会从大会堂的南头走到北头,去买几毛钱一碗的肉丝面。晚上回不去,架起椅子就睡在资料室。
工作班底
法制委的框架搭起来后,急需调人。王汉斌回忆:“我做的第一项工作就是调干部,组建工作班子。”
当时,戴了20多年右派帽子的老干部们正在被平反,陆续回到工作岗位。岳祥说,除了年轻人,一些“有能力、能干苦活”的老右派被重新召集到这里,走到立法的岗位上来。对这些人而言,这是退休前的最后一份工作。
这群人,并非如法制委委员那样位高权重,在“苦力班子”中默默工作,为了理念和理想还会互相争吵。
郭道晖因为偶然的机遇进入法制委,“半百之年开始学法律”。地下党时期,王汉斌妻子彭云是清华大学地下党总支委员兼理工支部书记,郭道晖是宣传委员。王汉斌到法制委后,让彭云写信约郭道晖到家里谈。起初郭道晖不愿意去搞法律,理由同样是“法律太枯燥”,前后谈了三次,都没有谈成。
当时,郭道晖在清华大学校史研究室工作,还没有被平反,对于“反右运动”依然记忆犹新。“反右”中,他被打成以袁永熙为首的党内反党右派集团的一员,上了《北京日报》头版头条和《人民日报》二版头条。所加罪名,一是他兼任校刊《新清华》总编辑,“坚决抗拒中央暴露右派的方针”,亦即抗拒毛泽东的“阳谋”; 二是所谓“顽固坚持反党的右派立场”,指“反右”前一天他在党委领导核心内部会议上,坚持认为不能把群众帮党整风当作“阶级斗争”“敌我矛盾”对待,不同意以反右斗争为主,认为绝大多数知识分子是爱国的,不赞成把某些教授打成右派,并明确声明保留意见。在会上,他独自一人与六位书记、副书记辩论三个多钟头,结果在1958年2月被划为“右派”,时年29岁。
王汉斌了解郭道晖完全是被“错划”,且颇有文才,就以彭真的名义找清华大学党委要求调人。郭道晖恭敬不如从命,于1979年到法制委工作。
到法制委后,郭道晖做的第一件工作是为起草《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做立法准备。当时,成立于1980年5月的深圳特区开始将土地出租给外商开发,但反对意见很大,一些人认为这是出卖国土,搞“新租界”,是走资本主义道路。他花了三天时间,到图书馆遍查《列宁全集》有关论述,写出一篇6000多字的长文《列宁论租赁制》,从“老祖宗”那里找到了理论依据,反驳了对合资企业立法的非难。这份材料后来呈送中央政治局,作为中央政治局审议《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的参考材料,获得好评。
当时,郭道晖白天细心记录人代会和内部研讨会上有关立法的讨论,广泛阅读报刊有关法治的信息和对立法的意见,写简报和意见;晚上回去整理第一手资料,著书立说。在调离后来的法工委时,他出版了《中国立法制度》和《民主、法制、法律意识》两本专著。
与郭道晖不同,张万琨一开始并未被看中。当时,法制委研究室需要懂日文的人员翻译日文资料。大连人张万琨清华大学毕业,日语好。他性格耿直,批判思维强,这在他工作过的机关单位都出了名。1957年“反右”高潮时,张万琨还安然无恙,但次年“反右补课”被补上。被划为右派后,每次政治运动他都提不同意见,于是不断挨整。至于当时为什么被划为右派,他自己也不知道。直到要平反时,才有人将他的右派言论抄送给他,“仅摘要就有三四页”。
摘帽后,张万琨在北京市经贸委工作,听说去法制委是搞立法,他说:“我想要搞法治建设,在中国有希望。我抱着理想去了。”
解放初期在北京市委和王汉斌一起担任彭真政治秘书的王文,也来到了法制委,负责信访工作。彭真的几位政治秘书,如张文松、崔月犁和王汉斌,后来都位高权重,王文仅官至处级,退休后享受司局级待遇。
“反右”开始后,王文在中共中央办公厅负责信访工作,因为接待右派林希苓时说了几句安慰话,也被划为右派。
同被划为右派的左羽,原名黄钟羽, 1979年4月被调去全国人大常委会研究室工作,先后任欧美处副处长、处长。
在北京大学地下党时期,王汉斌是联系左羽的单线领导人。左羽曾对高锴说:“我怎么会是右派?我是真正的左派,我是研究社会主义的。”郭道晖曾在《一个坚贞于真正马克思理论的人》一文中,称左羽“对马克思主义有着非常执著的信念和深刻的见解,而且是坚持原汁原味的真正的马克思主义”。
1957年,他受到批判,被误认为已被划为右派,“享受”右派待遇,下放劳改,妻离子散,直至平反时查档案才发现并没有被划,以致连要“改正”都无所据。“划右”后左羽曾被安排在清华大学宿舍楼当门卫,负责接听电话。但他不改初衷,在电话本下面放英文版马克思原著和批判斯大林的文集,一有空就学英文,阅读英文著作,探讨社会主义究竟出了什么毛病。
另外一位老右派江流,被“划右”后也妻离子散,一度流落街头,有家不能回。因为身体不适,他的家人婉拒了采访。
法律与政治
“文革”期间,法治脱轨,1949年后制定的一些法律,也被践踏。在一个缺乏基本法治理念的年代,建立法治是一项艰难的工作。法制委委员和工作班子中的老右派们,大多也没有法律基础。
在提出要制定民法通则时,许多老干部连“法人”的概念也不懂。高锴回忆,在讨论时,一位全国人大的高层领导不明白“法人”为何意,年轻人在台下窃笑。
为了满足对法律人才的需求,北京市司法局举办了法律夜校。法制委的一些年轻人通过招考进入夜校学习,白天工作晚上学习。周晓红和宋大涵、付洋一起上过夜校。宋大涵现在是国务院法制办主任,付洋现在是北京一家律师事务所的主任。
当时出国的机会很少,但立法要参考国外和台湾地区的立法经验,法制委调来了许多外语人才负责各种外文资料的搜集翻译工作。这些老右派中,张万琨懂日语,王文懂英文。为了参考以前的经验,连国民党时期的“六法全书”也被找出来。
针对“文革”的混乱局面,1979年版的《刑法》,出现了诸如“禁止‘打砸抢’”、禁止“以‘大字报’‘小字报’公然侮辱他人或者捏造事实诽谤他人”等内容。这些词汇大多具有时代特征,并不是法律用语,此后在修订中被删去。
岳祥介绍,“王汉斌主持法工委时,各个室的主任坐在一起,所有的法都一条一条读,每条读完就问大家有什么意见。提完意见后,主持这个法起草的研究室主任再拿回去修改。”
许多法律草案并非法制委就能决定,需要交给中央讨论。比如,《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各级政府组织法》的立法时涉及革委会是否保留的问题,在法制委反复讨论后,彭真专门向中央领导打报告,最后确定取消这一组织。
在有些问题上,即使中央领导同意了,但到下面还是有很多意见。比如结婚年龄的问题,虽然中央同意了“男22岁、女20岁”,但是计生委不同意,最后投票表决,中央的意见仍然占多数。
1982年,受法制委指派,王文列席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主持的《计划生育法》起草小组的会议。为了搞明白计划生育问题,他经常独自一人骑车去调研。有一次,法制委接到一个电话,一个村子里说抓到一个冒充干部的人,接电话的人说,王文是我们这的人。他这才脱身。早在1984年,王文就对一胎化政策提出过不同意见。
对于一些前沿的法律问题,左羽、张万琨提出过许多意见,比如土地所有制的问题,至今仍未破题。在讨论《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监督法》时,不少人提到人大对党的监督问题,但这一问题最后还是被搁置下来。
部委利益同样可能成为立法的巨大阻力。法工委多位人士举例,《海上交通安全法》出台前,交通部认为其下属港务监督执法机构是代表国家执法,“是挂国徽的机关”,于是在草案中规定,当事人如不服上级行政机关的复议裁决,不允许向法院提起诉讼。据曾担任法制委副主任的宋汝棼在其著作《参加立法工作琐记》记载,最后经过反复磋商、协调(其中一次是五位副委员长出面协调),才修改这一规定。
《海关法》是耗费张万琨最多精力的一部法律,对于走私如何定性存在激烈的争论。根据国外一些经验,凡不经过海关即为走私。但中国存在一些特例,如军队的进出口不通过海关,还有一些领导从国外买一些东西,海关都没法查。当时海关总署的领导表示希望开一个口子,后来出台的法律增加了例外规定。
如今已白发苍苍的张万琨,觉得朋友对他“大理想主义者”的评价是对的:法制委的立法工作,空凭理想并不可行,需要考虑部委利益在内的各种现实利益关系,这点让张万琨颇感失望。
由于法制委组成人员年龄偏大,许多人后来逐步身兼人大、政协的职务。岳祥说,到1982年前后时,“法制委开会就20多人,还不过半数,这就不好办了。”
当年年底,《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组织法》出台,其中规定常务委员会可以根据需要设立工作委员会。于是,法制委员会更名为法制工作委员会,“法工委实际没有委员,这些工作班子既是法工委党组,也是成员。”
过去的“苦力班子”,由此成为了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五大下属机构之一。此后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逐渐形成,立法的任务相对初期大大减弱,几个月之内出台多部重要法律的情况不可能再现。
至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这群老右派慢慢都离开了法工委。退休前,国家提倡干部年轻化,他们的官职都不高。1998年,退休后的王文独自一人骑车外出调研、旅游,倒在了辽宁昌图县境内的公路上,从此再也没有醒来;左羽也在这一年去世;张万琨得以在小汤山的养老院中颐养天年;郭道晖1987年被调往中国法学会,退休后,他一直为法治而奔走,为宪政而呼吁,和李步云、江平一起被誉为“法治三老”,如今以85岁高龄,活跃在中国法学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