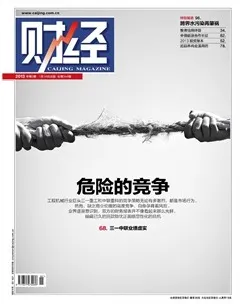肥差硕鼠
盛宣怀在1911年1月当上邮传部尚书时,绝没有想到,自己也逃不过前任们的宿命,任职十月后匆匆下台。
盛氏倒台的原因有二:上任不久强势推行铁路国有,得罪强大的既得利益集团;盛本人贪声卓著,所谓“一只手捞十八颗夜明珠”,授人以柄。
铁路国有化,原是朝野一致拥护的政策,争议焦点只在如何补偿。但对各省18家所谓“商办”、实际靠公权强行推行的铁路公司来说,此次国有化是高管最后捞一笔的机会。但这非分要求遭遇盛宣怀强势阻挠,盛氏和邮传部因此成为众矢之的。
寄生于“商办”铁路的利益集团,在修筑铁路方面毫无政绩,却擅长利用双重身份点火煽风。在他们策动下,湘鄂川粤四省便显得“民怨”沸腾,在长沙召集的粤汉铁路湖南公司声讨大会上,竟有个叫贾武的与会者,激愤之下切掉一根手指,誓与盛宣怀不共戴天。
邮传部因官员流动频繁,素有“运动部”之诨名,而之所以“运动”多,皆因油水太过丰足
既得利益者不便指责盛宣怀挡住其财路,只能将火力对准盛主持下的铁路建设大借款。这是指国有诏书发布后11天,清廷与美、英、法、德四国银行签订的借款合同,旨在举债1000万英镑用于铁路建设。
盛氏主持下签订的贷款合同,对中国十分有利:年利率为5%,尚不足国内钱庄和票号贷款利率的一半;删除了原定四国有权参与建造若干支路的条款;规定所用铁轨必须使用国货,其他原材料也要进行国际招投标,不再由外方指定。
但借款协议被攻击为政府“卖国”——尽管攻击者中的不少人,也私下接触外人,试探能否获得额外“补偿”。
邮传部的“恶名”帮了他们大忙。此部因官员流动频繁,素有“运动部”之诨名,之所以“运动”多,皆因油水太过丰足。
邮传部总共五年半的历史中,连盛宣怀在内,共有12人出任了13任部长(其中唐绍仪两任),个个都是响当当的知名人物。通算下来,人均在位仅五个月,以至于坊间流传一种说法,“邮传部不利堂官”。
作为大清国改革的产物,邮传部是权势最大的中央经济部门,管理铁路、航运、邮政、电信(电报、电话、无线电)四大产业,其所掌控的资源和资金之庞大,独步朝野。
“油桶”这么大,难免生出尺寸相应的硕鼠。众位流水般上任的部长中,最耐久者当属陈璧,在职20个月。他最后遭弹劾的罪名有一串:“虚糜国帑、徇私纳贿,订借洋款、秘密分润,开设粮行、公行贿赂”。此人发财手法花样翻新,主要包括:经手国际贷款时收受巨额回扣;利用职权卖官,致使凡欲占邮传部一席职位者,非运动不可。英国《泰晤士报》估计,陈璧的涉案金额有585万英镑之巨。而他的法定年薪仅白银360两。能捞大钱的不只是部长,据英国记者莫理循记载,铁路总办梁士诒和津浦路北段总办李德勋,也分别聚敛1300万英镑及142.5万英镑。
另一明星部长唐绍仪,虽没有确切的捞钱证据,其营私舞弊和重用亲戚的做法,在当时昏聩无度的官员中也算登峰造极。在海关、铁路或邮传部里的空缺,只要能捞到手的都被他安插了自家亲戚或广东同乡。
当然,邮传部尚书这个肥缺不是谁都能抢到手,除能力和资历外,还要看背景和后台。有传言说,陈璧当部长,除借袁世凯之力外,曾一次送给奕“五万金”并拜干爹。在12名部长中,岑春煊和徐世昌直接从封疆大吏调任,此前岑是两广总督,徐是东三省总督,两人皆八面威风。
因为有巨大的政治和经济利益,邮传部的班子里充斥着不同山头和路线之间的“运动”式斗争。徐世昌在当了部长后感慨:“邮传部事难办在权限不一,即用人犹如此掣肘,况兼交涉更须与外务部会办,无怪历任尚书无久任者。”
关于晚清的改革,尤其是干部人事体制改革,梁启超曾评价道:“徒为权位之争夺,势力之倾轧。贿赂公行,朋党各树,而庶政不举。” 后成为著名学者的邮传部司员曾鲲化,在其《中国铁路史》一书中坦承,邮传部“运动”不断,正是“政务之所以不振”的原因。
多种因素的合力,致使清廷顺乎朝野共识的铁路国有政策推出后,激起商办铁路既得利益集团的反弹。盛宣怀和“运动部”曾经的恶名,就此成为最好的投枪和匕首,一场“保路运动”随即滚滚而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