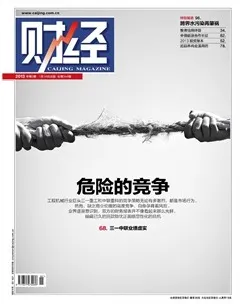非现实
在苏联、东欧国家,曾有过一种奇特的现象,那就是人们生活于其中的现实要么被掩盖,要么被虚构。
人们对现实与非现实的判断,并不依赖经验常识,而是依赖于某种辩证思维。历史上发生过的事可以没有发生,没有发生过的也可以发生。因此,在这些国家最严重的问题往往是真相问题。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东欧各国兴起的“萨米亚特”(地下出版物),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为了揭示真相。
波兰“卡廷惨案”就是被掩盖的现实。1940年春,在卡廷森林、加里宁等地,约有2.2万名波兰军人遭苏联军队屠杀,而苏联官方一直宣称这是德国纳粹所为。直到1990年,苏方才正式表示对此惨案负全部责任。许多波兰人私下早已知道事件真相。上世纪50年代初,诗人米沃什就在《被浮获的心灵》中公开指认“卡廷惨案”的罪魁祸首是苏联。整个世界却装作不知道。战后,纽伦堡审判回避对此事明确表态。
虚构现实会败坏人性,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后极权社会的道德重建才总是从恢复真相开始
1976年在波兰历史上具有重要地位,这一年当局审判拉多姆市的罢工工人,激起知识分子普遍抗议,成立“保卫工人委员会”,并创办波兰第一份“萨米亚特”刊物《记录》。作家布兰迪斯便是创刊者之一,他于1966年就因抗议当局迫害学者柯拉柯夫斯基而退党,此时刚写完纪实体小说《回旋曲》,正在创作《一个关于真实的问题》,并最终通过萨米亚特出版。两本书都涉及对虚构现实的探讨,即在波兰这样的极权国家,非现实如何变成了现实。
《回旋曲》的开头是叙事者写给一家历史刊物的信,要求纠正一个史实错误;《一个关于真实的问题》则用采访形式,描写一位学者按照调查表所做的一系列采访。两书之间有前后相承的关系,后者直白地表达了作者的意图。在作者那里,纪实体不再是出于文学实验,而是探讨非现实的有效方式。
叙事者是一位法律专业的学生,热爱戏剧表演。他爱上了一位女演员,为满足女演员对崇高的激情,他在战争爆发后以历史和想象为资料,虚构出一个地下抵抗组织,让女演员加入其中。她每天接受指示,递送情报。而实际上,她小心翼翼递送的手提箱里只不过装着废报纸。这样神秘而高尚的行动,让她找到了自己的人生角色,且无任何危险。但不久,该组织在抵抗运动中成了一个重要角色,危险也变成了真的。最后,另一地下组织杀害了一位无辜的老演员,女演员认为这要归咎于这位法律专业学生,也就是叙事者,因为她坚信后者有能力指挥所有地下活动。
战后,由于新政权对该组织一无所知,叙事者只在监狱里关了几年。然而,制度中普遍存在的非现实性,却很容易就承认了他所创造的非现实。叙事者虚构的地下组织成为历史学家研究的题目,正如书中所说:“他们几乎全都具有一个令人震惊的特点,真与假的界线在他们那里是弹性的。在每个判断上他们都具有一种高度发达的相对观(那个时候,这被称作辩证思维),但事实上缺乏内在的基础。”后来叙事者想重回真实,决定写信说明这一切都不是真的,从而获得女演员的原谅和爱,但已没有人听他讲述,非现实早已成了现实。
布兰迪斯想要探讨的不是历史怎么被掩盖,而是历史怎么被虚构。在苏联、东欧国家,人们自幼从教科书里学习许多英勇事迹,它们多是当局出于宣传目的编造加工而来。因为离开了虚构,意识形态就无法证明自己。
叙事者最终意识到,人性本是一团混沌,自己无法让它充满意义。在极权体制下,是谎言创造出现实中的种种秩序,而人们制造传说并让自己对幻象深信不疑。现实中根本就不存在真实,所有的叙述和描写都只是阐释罢了。被虚构的历史与被掩盖的历史一道,构成了极权社会特有的非现实世界。
生活在这样的非现实社会,人们如同生活在一个价值颠倒的世界。一个人在其中长大,如果他没有其他的信息源,没有学会思考,一生的知识大部分都将是无意义的。他既不会用常识去观察现实,也无法理解真实的情感。当真相到来,他要么躲避,要么蜕变成虚无主义者,并坚信这世界根本就不存在真实。这就是为何在一个极权制度衰落时,人们常会看到社会道德沦丧。
虚构现实会败坏人性,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后极权社会的道德重建才总是从恢复真相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