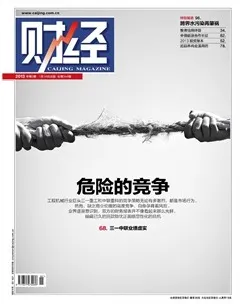贝雅特·西洛塔
贝雅特·西洛塔(Beate Sirota)第一次到日本时年仅5岁。1929年,她随父母从海参崴乘船到横滨。小西洛塔对这个国度十分不解,码头上的人全是黑头发、黑眼珠,西洛塔分辨不出他们长相有何区别,好奇地问母亲:“他们是一家人吗?”
十余年后再到日本,西洛塔所见已不复当初,战争狼烟席卷之处,满眼断壁残垣。她亦不再是那个天真的小女孩,而是盟军最高司令部民政局的文职人员。时年22岁的她,参与了一场改变日本历史的事件:草拟日本战后宪法。
西洛塔于1923年10月25日出生在维也纳,其父是国际知名钢琴家。5岁那年,父亲受邀前往日本东京音乐学院任教,西洛塔和家人在那里度过快乐的十年。随着她对日本的认识日益深刻,发现这里不仅有富士山和樱花,更有阳光下的不公——女人被视为财产,难以享受与男性相同的权利。
1939年,西洛塔16岁生日前,父母将她送往美国密尔斯女子大学读书,随后返回日本工作。没想到一家人不久便天各一方。
“珍珠港事件”爆发后,她与父母失去联系,终日忧心忡忡。为掌握日本的情况,也因为会说流利的日语,西洛塔加入美国战时情报局,撰写对日宣传文章、监听日本广播。她还利用空闲时间继续学业,于1943年从密尔斯女子大学当代语言专业毕业,两年后加入美国国籍。此时,她已学会六种语言。
日本投降后,平民暂时无法前往日本,她于是加入麦克阿瑟将军的团队,于1945年平安夜抵达东京。父母位于日本的住所已成焦土,只剩烟囱与断壁。她设法找到了被拘禁于乡村的父母。但这还不是西洛塔日本之行的终点。
战争结束前,盟国发布《波茨坦公告》,提出战后日本应“成立一倾向和平及负责之政府”。麦克阿瑟随后表示,欲达此目的,须修改日本宪法。到1946年初,麦氏着手所谓占领日本后“最重要的一项成就”,即以新宪法取代1890年开始施行的日本“明治宪法”。
1946年3月,宪法草案作为日本政府的自创成果被公布,之后提交国会审议通过。实际上,此宪法草案出自最高司令部民政局人员之手,由他们在东京“第一生命”大厦秘密奋战一周拟就。如最高司令部的内部备忘录所载,此宪法将“明治宪法”掏空,仅留下“结构和标题”,重新填入欧美民主理念。在新宪法下,日本放弃了发动战争的国家权利。
西洛塔是25人宪法起草委员会中唯一的女性。她被分配到人权法案小组,负责起草女性权利条款。受命之后,西洛塔来不及思考此事之重大,便投身其中,决心为日本女性订出细致而清晰的权利保障条款,以免将来被曲解或利用。
她征用一辆吉普车奔波于东京街头,光顾所有在轰炸中幸存的图书馆,搜集到魏玛共和国宪法、苏联宪法、美国宪法、瑞典宪法等法律文本。随后,她潜心研究,昼夜奋战,七天后用一台安德伍德打字机写出日本宪法草案中的两项条款:全体国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在政治、经济以及社会关系中,皆不得以人种、信仰、性别、社会身份或出身而有所差别;女性的择偶权、财产权、继承权、永久居住权、离婚以及相关事项等方面的权利应受保护。
日本新宪法于1947年5月生效,迄今仍是最优秀的法律之一。西洛塔的努力,让新宪法保障了“两性的实质平等”,而这在美国宪法中都未曾给出明确规定。西洛塔后来回忆,她从未试图借修宪教导日本人。她只是出于良知,而这良知完全基于对日本妇女所受不公待遇的同情与共鸣。
出于对日本及其他亚洲国家的热爱,西洛塔在20世纪50年代加入位于纽约的日本协会,70年代又供职于纽约的亚洲协会,1991年退休。她曾走进亚洲国家的偏远乡村,探访那些被忽视的文化艺术精粹。她是最早将这些东方艺术系统引介至北美国家的人之一。
世人记住了亚洲艺术推广者西洛塔,可她为日本妇女解放所付出的努力却被长久埋藏。西洛塔不曾谈及此事,起初为保密,后来则是不想让自己以22岁的年龄参与制定宪法以及美国公民的身份等事实,被日本保守分子利用来攻击“和平宪法”,后者长期不遗余力地鼓噪修宪。1995年,西洛塔出版回忆录,披露这段鲜为人知的个人经历,迅即在日本成为名人,她的故事也被拍成纪录片《贝雅特的礼物》。
尽管日本新宪法带有征服者的印记,并使日本的保守派震惊,它却以令人瞩目的方式,植入了民众对和平与民主的热望。近年来,日本保守势力针对“和平宪法”有种种批评,西洛塔则奋勇回击。曾有人说此宪法乃舶来品,西洛塔毫不客气地回应,日本文化中许多元素都深受外国影响,甚至包括其文字。
西洛塔常在各种场合展示颈上的围巾,上面用六国语言印着相同含义的字句,正是她当年在打字机上所写:全体国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