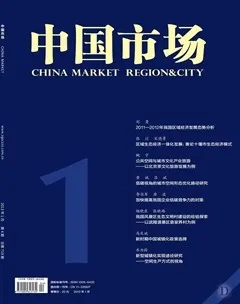2011—2012年我国区域经济发展态势分析
[摘 要]2011年我国区域经济增长速度普遍放缓。从地区比较看,我国中西部经济增长速度连续5年超过东部,远西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继续超过各省区平均水平,东西部差距继续向趋缓方向发展。从增长、总量和发展水平三大区域格局看,区域增长速度格局再次变为“远西部、大中部、新东部”的排序,东西部增长速度差继续逆向扩大;区域经济总量格局继续呈“东部大、中西部小”态势;区域经济发展水平格局继续呈“新东部和远西部高、大中部低”态势。2012年在世界金融危机继续深化,特别是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继续发酵演变的情况下,我国区域经济可能继续趋缓,各地区增长速度大体在150%~75%;区域差距将继续保持“相对差距略有缩小、绝对差扩速放缓”态势;2012年我国区域经济呈现出各地区经济增速继续有所放缓、一些重大基础设施项目建成使区域投资环境得到改善、经济和城镇化重点地区将呈现新变化等基本趋势,为保持区域经济协调发展良好势头提出进一步制定和出台一些急需的空间规划、出台有利于中小城镇发展的经济社会政策、利用结构性减税的机会建立我国地区差异化税收体制、建立全国性生态补偿机制等若干条对策建议。
[关键词]2011—2012年;区域经济;态势分析
[中图分类号]F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6432(2013)4-0006-08
2011年是我国经济增长最不确定的一年,是“十二五”规划的头一年。世界经济仍然处于困境之中,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突然显现使世界金融危机继续深化,预计未来若干年也难以走出低谷的局面。随着4万亿元一揽子刺激政策逐步退出和防止恶性通货膨胀政策实施,我国经济增长速度从提速转向适度回落,走了个前高后低,全年达93%,比2010年下降11个百分点,GDP达472882万亿元,人均GDP为35097万元。同期,我国区域经济也普遍有所回落,多数地区都由提速转为减速。2011年各省区经济增长速度合计为118%(按GRP加权平均),低于2010年13个百分点(高出全国统计25个百分点);各省区GRP合计为518194万亿元(比全国统计高出45312万亿元);各省区人均GRP合计为38777元(比全国统计高出3680元)。
1 区域经济增长的格局演变及特点
2011年我国区域经济增长、总量和水平格局总体态势为,中西部增速继续快于东部,总量和水平格局继续有所改善。
11 区域经济增长格局继续呈“中西部快、东部慢”态势,远西部、长江中上游和天津增长速度最快 从三大地带看,2011年我国中西部连续5年超过东部且超幅继续扩大,前者比后者快259个百分点;远西部快于大中部,再次形成远西部、大中部和新东部的排序,而且东西部增长速度差继续呈现出逆向扩大态势。这些反映了欧债危机对东部的影响,以及国家对新疆投资力度加大正在起作用。
从“7+1”综合经济区看,快于各省区平均的地区变为长江中上游(重庆的发展并未受到影响,大型国有企业支持力度加大)、远西部、珠江中上游、东北地区和黄河中上游,慢于各省区平均的地区变为华东沿海、东南沿海和华北沿海,表明欧洲债务危机导致出口下降,再次给我国沿海地区带来巨大冲击,这次受冲击最大的是华东沿海(2008年是东南沿海)。(参见表1)。
从各省区看,2011年在各省区合计经济增长平均速度为1182%,比2010年低133个百分点的总体情况下,除贵州、云南、西藏、甘肃和新疆5省区外,其余省区增速均慢于2010年(其中海南降速最大,为40个百分点)。各省区增长速度天津和重庆并列第一,达164%(低于2010年天津10个百分点),最慢省区是北京,为81%(低于2010年并列最后一位的上海和北京22个百分点),幅度整体下移10个百分点,幅度范围扩大12个百分点。各省区快于和慢于平均速度的省区之比为23∶8,说明各省区合计增速主要由低于平均水平的少数关键省区决定(如广东、山东、江苏和浙江4省区组成的所谓“两东两江”地区)。各省区增速排序变化较大,其中:升位省区12个,升幅最大的贵州和云南达14位;降位省区11个,降幅最大的海南为18位;位次未变省区6个。
经济增长快于各省区平均又高于140%的有天津、重庆、四川、贵州和内蒙古5省区。天津增速放缓但仍保持了全国第一,滨海新区继续快速发展;重庆也略低于2010年,与居首位的天津同速,国企投资力度不断加大;四川由降转升前移2位,自主增长开始发力;贵州由降转升前移14位(与云南同为前移最大省区),是增速超上年的少数几个省区之一且超幅最大,实现了“弯道超车”,成为一匹黑马;内蒙古由降转升前移1位,仍然处于第一增长方阵中。这些都表明我国区域增长重心继续向北向西移动。
经济增长在各省区平均周围界于140%~100%的有陕西、湖北、云南、吉林、青海、安徽、山西、湖南、西藏、江西、甘肃、广西、黑龙江、福建、辽宁、新疆、宁夏和海南,河南、河北、江苏、山东和广东23省区。云南、甘肃和西藏都由降转升分别前移14、12和10位,增速也都超过2010年,得益于西部大开发的深化;吉林由连续下降转为上升前移8位,得益于长吉图区域规划的实施和汽车工业的回暖;新疆继续上升前移6位,得益于国家投资力度的加大,煤炭资源的开发;陕西由连续下降转为上升前移2位,缘于陕北能矿资源开发;山西和黑龙江均继续上升都前移2位,前者为煤炭开采,后者为装备工业发展;河北继续上升前移1位,得益于曹妃甸仍处在建设时期。湖北和安徽由升转保,维持了相对较快的速度。海南和青海都经历了大起大落由升变降分别后移18位(后移最多)和7位,前者明显受欧债危机和国际局势动荡影响,国外游客剧减,后者则因为玉树灾后重建接近尾声;辽宁继续大幅后移9位,装备出口受阻严重;江苏由保转降大幅后移7位,广东继续大幅后移6位,均反映欧债危机对出口大省区的影响;广西继续大幅下降5位,明显受外需不足影响,宁夏由升转降也后移5位;湖南继续下降后移4位,福建由保转降也后移4位;河南由升转降后移3位;江西继续下降后移2位。
经济增长慢于各省区平均又慢于100%的有浙江、上海和北京3省区。浙江连续数年下降又后移2位,成为外需萎缩最大受害者之一。北京和上海继续处于最后两位,其中北京依然垫底(参见表2)。
12 区域经济总量格局继续呈“东部大、中西部小”态势,变化依然是东部比重略降中西部略升 从三大地带看,2011年新东部经济总量达314319亿元,占全国比重为607%,比2010年降10个百分点;中西部经济总量达167518亿元,比重为393%,比2010年增10个百分点。在中西部中:大中部经济总量达148551亿元,比重为349%,比2010年增09个百分点;远西部22961亿元,比重为44%,比2010年提高01个百分点。可以看出,东部与中西部总量相对差继续缩小,缩小幅度比2010年略大。
从“7+1”综合经济区看,总量比重高于125%的有华东沿海、华北沿海、长江中上游和东南沿海4大区,其中三个沿海地区比重分别降为193%、187%和140%,降幅分别为04、03和04个百分点;长江中上游比重升为187%,升幅为06个百分点。总量比重小于125%的有黄河中上游、东北地区、珠江中上游和远西部4大区,他们的比重均继续比2010年有所提高,分别提高到110%、87%、50%和44%,提高幅度分别为02、01、01和01个百分点。(见表3)。
从各省区看,在各省区经济总量平均为16716亿元,比上年名义增加2618亿元的背景下,2011年各省区总量都比上年有所增加,其中增加最多的是江苏,增加7179亿元。各省区总量幅度为52674亿(广东,比2010年广东增加6661亿元)~606亿元(西藏,比2010年西藏增加98亿元),整体上移98亿元,幅度则增加6563亿元。大于和小于总量平均的省区之比为12∶19,排序变化很少,仅有湖南和湖北同时前移1位,上海继续后移2位(见表4)。
经济总量大于各省区平均又大于30000亿元的仍然是广东、江苏、山东和浙江4省区,组成“两东两江”地区,排序未变。
经济总量在平均周围界于30000亿~10000亿元之间的有河南、河北,辽宁、上海、四川、湖南、湖北和福建,北京、安徽、内蒙古、黑龙江、陕西、广西、江西、天津、山西、吉林和重庆19省区,比2010年减少1个。只有湖南和湖北同时前移1位,上海继续后移2位,其余排序未变。
经济总量小于各省区平均又小于10000亿元的有云南、新疆、贵州、甘肃、海南、宁夏、青海和西藏8省区,比2010年多1个,但排序无变化。
13 区域经济发展水平格局继续呈“东西部高、大中部低”的V字形态势,新东部与中西部继续呈现相对差缩小绝对差扩大状态 从三大地带看,2011年新东部和远西部人均GRP均高于各省区平均,分别达50866元和41424元,分别是平均值的131倍和107倍,前者比2010年继续下降003倍,后者则比2010年继续提升003倍。大中部人均GRP依然低于各省区平均,仅为27271元,仅为平均值的070,但继续比2010年略提高002倍(与人口变动有关)。总之,新东部与中西部继续呈现相对差缩小绝对差扩大状态。
从“7+1”大综合经济区看,人均GRP高于各省区平均的有华东沿海、华北沿海、华南沿海、远西部和东北地区5大区,前三者与平均之比继续有所下降;后两者则略有提高,远西部继续提高003倍,东北由持平变升002个百分点。人均GRP低于各省区平均的有黄河中上游、长江中上游和珠江中上游3大区,均属大中部,前两者分别继续提升001倍和003倍,后者由持平转为上升003倍。(参见表5)。
从各省区看,在各省区人均GRP平均达38777元,比2010年名义增加5751元的背景下,2011年各省区人均GRP均有所提高,其中增加最多的省区是天津,达11343元。各省区人均GRP变化幅度为84337(天津,比2010年上海名义增加8263元)~16413元(贵州,比2010年贵州名义增加3294元),整体上移3294元,幅度扩大4969元;低平平差和低平极差分别为073和043(贵州),分别比2010年缩小002和003,也就是说各省区间相对差继续有所缩小绝对差则继续扩大。各省区人均GRP高于和低于各省区平均的省区比为10 ∶ 21,说明各省区人均GRP平均水平主要由大于平均的少数省区决定(实际上就是“两东两江”地区)。各省区人均GRP排序发生重大变化,最突出的是天津取代上海成为我国区域经济发展的龙头,这是21世纪以来我国区域经济增长重心不断北移西移的必然结果。(参见表6)。
人均GRP高于各省区平均又高于80000元的有天津、上海、北京3省区。天津前移2位成为新的龙头,上海和北京向后顺移1位。这是排序的重大变化。
人均GRP在各省区平均周围界于80000~30000元的是江苏、浙江、内蒙古、广东、辽宁、山东和福建,吉林、重庆、湖北、河北、陕西、黑龙江、宁夏和山西15省区,少了新疆。位次变化为辽宁和广东位次互换,辽宁继续前移1位,继去年超山东后再超广东(东北振兴作用明显的表现);重庆继续前移2位,保持了良好发展势头。广东继续后退1位;河北由持平变为后移2位。其余未变。
人均GRP低于各省区平均又低于30000元的有湖南、新疆、河南、青海、海南、四川、江西、安徽、广西、西藏、甘肃、云南和贵州13省区,多了新疆。湖南继续前进1位;四川由退变进前移1位。新疆继续后移1位(说明增长为外部投入带动,需引起思考),江西由进变退后移1位。
14 2011年我国区域经济发展格局基本特点
从以上三个格局的数据分析看,2011年我国区域经济发展格局有以下基本特点:一是天津成为区域经济发展的龙头。天津不仅已连续两年增速居全国第1位,而且人均GRP超过上海和北京,也一跃成为全国第1位,初步取得了全国区域经济发展的龙头地位。二是区域增长和总量重心继续向北向西移。区域增长格局继续呈现出“中西部快、东部慢”态势,华北地区发展热点明显多于华南地区,天津成为区域经济发展的龙头,这些都显示我国区域增长和总量重心继续向北向西移;有关我国区域增长和总量重心的转移分析也反映了这个特点。三是地区相对差距继续缩小,地区绝对差距依然扩大。地区间经济增速差决定了地区差距的变化方向。2011年我国区域经济增长东西部之间的距差继续呈现出逆向扩大态势,显示地区相对差以更大的幅度在缩小,但由于地区差距依然较大,地区绝对差距仍然在扩大。
2 2011年我国区域经济发展格局演变的原因分析
总体看,我国区域经济发展仍然是由投资和第二产业驱动,少数相对发达省区(上海、北京等)开始出现向消费和第三产业拉动转型的态势。
21 从区域总需求看,区域投资格局在区域经济发展格局中起着主要作用,但低速增长省区主要由最终消费拉动 从区域资本形成看,省区GDP增速越高资本形成拉动作用也越大,经济增长最快的几个省区,如天津、重庆、四川、贵州和内蒙古等投资带动作用十分明显;几个资本形成拉动峰值省区,如天津、内蒙古、云南、青海、广西和河南,都是增速排序升位较多的省区。也有一些省区经济增长主要由最终消费拉动,如广东、浙江、上海和北京等,这些都是经济增速最低的几个省区,显示了这些地区发展方式开始转变。
再从最终消费和净流出看,两者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不太密切。前者几乎不随经济增长变化,也就是说各省区最终消费拉动基本相同,均在5个百分点左右;后者则波动较大,大体上经济高增长省区多位于中西部,因此净流出带动较小,经济低增长省区多位于东部,因此净流出带动较大。
22 从区域总供给看,区域第二产业增长格局在区域经济发展格局中起主要作用,但低速增长省区主要由第三产业带动 从第二产业看,其带动作用明显高于其他产业,而且经济增速越高,第二产业带动作用越大;重庆和天津等增速最快省区第二产业带动作用也最大最明显;一些峰值省区,如内蒙古、贵州、青海、山西、甘肃、黑龙江和宁夏等都是经济增长排序前移较多的省区。
从第一产业和第三产业看,前者波动较小,后者变动较大。前者除海南、新疆和云南等少数省区外,其余省区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已经十分有限,主要起粮食安全和农业稳定基础的作用。后者则是各省区产业结构转型的重要抓手,表现为经济较发达地区,经济增长速度不高,主要由第三产业带动,如上海、北京等;一些第三产业峰值地区,如四川、西藏和海南等,也显示出第三产业的主要带动作用。
除以上因素以外,还有许多其他影响因素,如区域经济总量和人均水平都有可能影响区域增长格局,限于篇幅不再一一论述。
3 2012年我国区域经济展望与对策
31 2012年我国区域经济发展基本形势与趋势
2012年欧洲主权债务危机将继续笼罩世界经济发展,中国经济将面临又一次外需严重不足局面,其严重程度还难以准确预计,不少学者认为可能会比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还要严重,因此扩大内需就将再次成为保持我国经济稳定健康增长的最重要的战略选择之一。从国内看,我国经济已经进入工业化城镇化中后期阶段,经济增长适当放缓也是经济发展客观规律的要求;相应地,我国改革开放也面临新的机遇和考验,改革的顶层设计,开放的进一步深化,都将决定未来我国经济的宏观走势;在我国政府大换届之际,保持经济又好又快发展,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经济增长的政治周期起到重要作用。以上就是将影响我国区域经济发展的国内外主要因素。总体看,2012年我国区域经济继续保持协调发展态势,在促进国内外经济稳定增长中将继续发挥应有的作用。
一是受外需不足和扩大内需要有一个过程的影响,我国区域经济增长在继续保持协调增长态势的基础上,各地区经济增长速度将继续有所放缓。2012年各省区合计的经济增长将保持在9%左右,略低于2011年,各省区增长范围大约在140%~70%;中西部经济增长速度将继续超过东部,远西部经济发展水平将继续超过各省区平均水平,东部与中西部区域差距将继续有所缩小;区域经济增长的重心将继续北移和西移。
二是随着4万亿元投资形成的一批重大的基础设施、资源开发和生态保护项目的建成投产,我国区域经济发展环境将得到有效改善。2012年京汉客运专线将建成通车,形成世界最长的纵贯南北的京汉-汉广-广深-深港的高速铁路客运专线,将大大促进沿线地区经济发展。“南水北调”东线工程部分段落将竣工通水加上已经竣工投产的“西气东运”二期工程,将为东西部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创造更好的条件。即将进一步大规模实施的国家找矿工程将为我国经济的发展奠定更加坚实的基础;即将出台的新一轮国家级国土开发整治总体规划,将配合西部大开发和中部崛起,更加有效地保护和改善国土资源和环境。
三是在整体经济放缓形势下我国区域经济和城镇化重点地区将出现如下变化。首先,长江中上游地区将继续引领综合区增长。随着长江中游城镇群战略和成渝城乡一体化战略的深入实施,该地区成为我国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重点地区的地位日益突显。其次,一些新兴城镇群,如武汉都市圈、长株潭城镇群、中原城镇群等将成为新的增长亮点。最后,随着国家成片贫困地区整体开发战略的实施,中西部集中连片贫困地区将得到重点投资与发展。
32 若干问题与对策建议
一是我国区域经济发展仍然面临分工协作关系比较混乱的局面,要进一步制订和出台一些急需的空间规划。为应对世界金融危机,扩大内需,从2008年起,国家先后出台了几十个国家级重点发展地区的规划。据统计,2009年国家出台了12个有关区域规划和指导意见,2010年出台了两江新区、西部新10年规划、山西资源枯竭转型规划等近10项规划。2011年又出台了山东蓝色海洋经济规划、浙江海洋经济发展规划、成渝经济区规划、海峡西岸先行先试规划等。有人认为,我国区域规划太凌乱,区域政策也存在所谓“碎片化”问题。其实,这些不同类型
的区域规划和政策是需要的,是针对不同区域的不同问题制定和实施的,逐步建立起完善的区域规划和政策体系是一个需要不断努力的过程。事实上,区域规划大体上可能包括板块区、类型区、政策区和改革开放试点区等类型。未来进一步制订和出台一些急需的空间规划应以4大板块区和主体功能区划为龙头,规范和调整区划和规划体系。完整的区域规划体系由全国区域规划总体方案和若干重点规划组成。尽快制订和出台全国区域规划总体方案尤为重要。全国统一的、综合的、多层次的总体空间区划和发展规划方案内容包括:提出完整的全国空间区划体系(由多层次板块区和多方面类型区组成);综合考虑自然、经济、社会、文化以及行政区划等多方面因素,对不同层次和不同方面的区域面临的不同问题,提出不同的规划解决方案,包括指导思想、原则、重点和措施;区划和政策方案要做到动态性与稳定性有机结合等。
二是我国城镇化仍然严重滞后于工业化,稳妥推进城镇化进程,使其成为扩大内需最行之有效的途径,为此要出台一批有利于中小城镇发展和大城市郊区化的经济社会政策。目前,我国城镇规模结构不合理突出地表现为城镇“大的太大、小的太小、缺乏中间环节”上。中国不乏500万人,乃至上千万人口的超大规模城市,但这些大城市都已经面临严重的“城市病”困扰;而众多的建制镇和集镇规模太小,显示出破败的态势;中间规模的城镇数量严重缺乏,人口从农村向城市转移缺乏需要的选择和过渡环节。尽快出台一批有利于中小城镇发展的经济社会政策应该成为推进城镇化,改善城镇体系结构,促进内需扩大的首选对策之一。同时,为有效解决“城市病”问题,还必须高度重视和及时实施超大规模城市郊区化战略。一方面这是解决“城市病”问题的根本途径;另一方面也是因为我国城镇化已经到了郊区化发展阶段。通过实施郊区化战略,采取一切有利于疏散中心城区人口,有效改善城市居民生活环境和条件,从“以空间换时间”过渡到“以时间换空间”的城镇化模式上来。目前,阻碍大城市郊区化的因素还很多:首先是认识问题,许多人还没有认识到郊区化对大城市发展的重要性,其次是还存在大量的不利郊区化发展的体制机制和政策,需要加以改革和克服,如大城市周边地区高速公路收费、郊区化缺乏绿带控制出现“摊大饼”现象、卫星城必要的生活设施不配套等。
三是我国区域发展条件不平衡问题尚缺乏有效的干预对策,要充分利用结构性减税机会建立我国地区差异化税收体制框架。各地区由于客观存在的发展条件不同,会影响区域间的公平竞争,从而出现地区发展差距。通过实施差异化税收政策可在一定程度上消除由于自然环境和资源条件等客观形成的不公平竞争现象,从而有利于区域协调发展。为稳定增长,国家将出台结构性减税政策,可以利用这样的机会,在统一税制的前提下,根据地方资源环境条件和发展水平的不同,制定累计性差别化税率体系,以更加有效地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
四是总结各地区生态补偿方案,建立全国性生态补偿机制。区域可持续发展是未来我国区域经济发展的主要方向之一。实践表明,区域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实现离不开生态补偿机制的有力支持。目前,全国有许多地方性生态补偿机制,都取得了比较好的效果。但就全国而言,这些地区性生态补偿机制力度是不够的,迫切需要从国家层面上建立统一规范,力度更大的全国性生态补偿机制,以保障我国整体生态环境的改善和更高的生态文明目标的实现,促进我国区域可持续发展。
[基金项目]本研究得到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课题《中国区域发展形势报告》的资助。
[作者简介]刘勇(1963—),男,湖北武汉人,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博士,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博士后。现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发展战略和区域经济研究部研究室主任。研究方向:生态环境学、产业和区域经济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