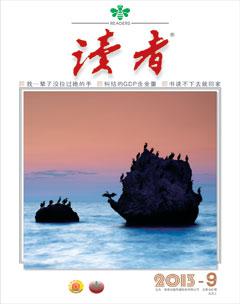改书名的艺术
张佳玮
美国文学界曾经流传一则笑话,主角多变,但情节如一:某作家巧遇玛格丽特·米切尔,自吹自擂如何著作等身,如何挥才如水。米阿姨到最后才磕磕巴巴地说:“啊,我,我也写过点东西的……”“啊,是吗?你写过什么呢?”“《飘》……”然后,某作家的眼镜就碎了。
姑不论故事真伪,《飘》的破坏力之大就那么吓人。1926年米切尔阿姨开始写此书,只为打发时光;到1935年此书出版时,广告语不过是“买本假期读读,5美元不亏”;发售一个月后,已经有人为了抢此书,去砸书店的橱窗了……电影播映时,开头用了开篇的那段句子来解释此书的命名,黯然销魂,但又严丝合缝。然而随你信不信:这书本来可能叫其他名字。
米切尔阿姨当年交书稿时,没想好书名,编辑催她,她就想以本书的经典台词来做书名:《明天就是另外一天了》,被编辑否了:“现在带‘明天俩字的书名太多了!”米切尔一寻思,就换成《军号歌唱真实的故事》《不在我们的星球上》,又被编辑们一一否掉。最后,定下来了《飘》。很多年后,亚特兰大有媒体曾笑言:“如果真叫做《不在我们的星球上》,乖乖,我去买这本书时一定会以为,这是本科幻书呢!”
如此这般,挑书名实在是个大工程。比如,2013年恰好是《傲慢与偏见》出版200周年,当初简·奥斯丁写完这书送交时,定的书名是《第一印象》。这个书名如今看来,活像个新闻透视节目。但奥斯丁起这书名自有其用意:书里的几对欢喜冤家,尤其是男女主角达西和伊丽莎白,都是因为“第一印象”,互相别扭开了:无非是你嫌我陈腐,我恨你傲慢,把一个可以三五页结束的故事,拖成了一本书。但此书名一如奥斯丁的风格:又尖锐,又嘲讽,还带点不易理解的幽默感,所以改成《傲慢与偏见》。
1925年,菲茨杰拉德出版了《了不起的盖茨比》,一举奠定他20世纪美国最伟大小说家之一的地位,但比这更富戏剧性的,是此书定名前后的故事。众所周知,菲茨杰拉德及其太太泽尔达,是20世纪20年代巴黎著名的金童玉女。海明威在《流动的圣节》里提到两个可怕的细节:其一,菲茨杰拉德每次企图写作时,泽尔达就拉着他到处寻欢作乐,连夜痛饮,不让他得丝毫安生;其二,泽尔达欺骗了菲茨杰拉德,让他相信自己性功能有障碍,换别的女人,根本不要他。菲茨杰拉德信以为真——简单说吧,泽尔达有疯狂的独占欲,“兀鹰不愿分食”。
就在菲茨杰拉德写作《了不起的盖茨比》时,泽尔达除了“兀鹰不愿分食”地搅扰他,还自顾自跑去海滩游泳、到舞会寻欢。最后她认识了一个男人,跑回来跟菲少爷要求离婚——奇妙的是,那男人还蒙在鼓里,全然不知道泽尔达会为了他闹离婚。
这事平息后不久,《了不起的盖茨比》要出版了。菲少爷原本想的书名是:《长岛的特立马乔》《特立马乔或盖茨比》《金帽盖茨比》《高跳爱人》。最后,泽尔达一锤定音,决定了《了不起的盖茨比》这个书名。这多少有些讽刺:这个小说描写了一个被所爱的任性女子操纵,摆出华丽场面邀其欢心,最后死去,只余空幻落寞的年轻人,和菲茨杰拉德自己如此相像。
海明威自己也经历过改书名的事儿。他在巴黎写作第一部长篇小说时,曾想起名为《嘉年华》——很多年后,他将自己巴黎时期的生活记为随笔出版时,就叫做《流动的圣节》,其意思有相似处。但后来,因为受了作家兼评论家斯泰因阿姨的言语刺激,给小说改名叫《迷惘的一代》。到真出版时,又改了一遭,叫《太阳照常升起》。
好笑的是,多年后海明威解释过这段话。“迷惘的一代”是斯泰因评价海明威这一代人的话,而海明威并不认同。实际上,因为斯泰因还冒失地小看了海明威推崇的作家舍伍德·安德森,海明威曾这么反讽斯泰因:“我想到斯泰因小姐和舍伍德·安德森,一想到与严格律己相对的自私态度和精神上的懒惰,究竟谁在说谁是迷惘的一代?”——当然,这种反讽没被文学评论家注意。如果海明威老老实实定了《嘉年华》为书名,也不要再提“迷惘的一代”这茬儿,现在的文学史上,估计会多出“嘉年华一代”呢。
(婉 婉摘自《世界博览》2013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