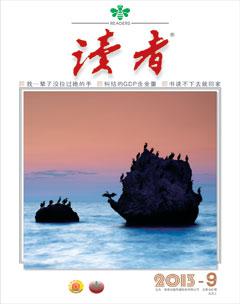我一辈子没拉过她的手
我的故事全世界的人都知道,其实《恋恋风尘》里阿远的原型就是我。我初中毕业到台北工作,那个叫阿真的女孩子晚我一年到台北。我们在村庄里时,双方父母就已经称对方为亲家了。那个女孩就是你跟她讲什么她都相信你,很典型的台湾女孩子,住在山上,不晓得外面,到台北来工作,就是一心想可以依靠我。
那时候我换了很多工作,什么都做过,在外面当学徒,连老板全家的衣服都要洗。我记得有一个雇主,他女儿念的是台北一个私立学校,叫“敬修女中”,我还帮她洗制服,一边洗一边吐痰在上面,发誓找女朋友一定不找敬修女中的。
后来我去当兵,她买了一千多个信封,准备写上她的地址,贴上邮票。那时候一张邮票两块钱,一千多张邮票是两千多块,她五个月的薪水。
那天晚上我本来要走,后来就陪着她写。她最后大概很累了——因为第二天还要上班,她在餐饮店工作,卖肉粽和汤圆——我就帮她写。最后她睡着了,我就拿了条小棉被帮她盖上。第二天她起来,我也写完了,就把信封捆好带去当兵。最后侯孝贤拍片时保留了“我们一起写信封”的镜头,其他的他就删掉了,因为觉得太煽情了,没有人相信。
我扛着一千多个信封去当兵,去金门要坐船,宪兵检查时说:“你以为金门没邮局吗?”我在金门最后的时间里,她跟别人结婚了。那时候我很生气,很想回去问她为什么,后来想想,又觉得我之前也没有承诺说要娶她。营长看我很辛苦,就说好吧,准你特假。因为在金门当兵是不能回去的,我在岛上待两年了,他想让我放假回去看看。
打包行李的时候,我说我回去要拿刺刀刺死她什么的。我乱讲一通,勤务兵很紧张,跑去跟营长讲,结果我到港口的时候宪兵不让我登船,说营长取消了我的假。我回来气得要死。后来想,算了,她既然都成了别人的太太,我又能改变什么呢?可是我当时很痛苦,之后就开始写小说,开始投稿。
我妹妹那时候念国中,很可爱,我经常跟她聊天,讲我在台北的时候,每天晚上去帮阿真收店,然后两个人就拿着肉粽去北门荡秋千,两人坐在秋千上看最后一班夜车过去了,然后我再回去,就尽讲这些细节。
有一天我叫她帮我寄个小说投稿,她就把我原来的名字“吴文钦”涂掉,写成“念真”,就这样寄出去了,登出来就是这个名字。
那时候阿真大概在报纸上辗转看到了这篇文章,她就打电话到我公司来找我。她不敢打电话问她们家的人,找到我就讲东讲西,偶尔讲到她在报纸上看到我写的小说,知道是我写的,她说:“你不要用那个名字,我看到很难过。”
后来我打电话跟报社讲,叫他们不要用那个名字了,因为我还有几篇稿子在那边。他们说:“大家都知道你叫‘念真了,你再改很麻烦啊。你加个‘吴嘛,就是‘没有啊。”就这样变成“吴念真”了。
完全没有想到这会造成以后恋爱的困难,没想到它会变成婚姻的障碍,也没想到侯孝贤有一天会拿来拍电影,而且拍得还不错。搞成这样真的很烦,拍完后有人到我家访问,我太太气得要死。不过她后来习惯了,结婚后只要有人打电话说“我找念真”,她就说:“等下!”如果有人讲“我找文钦”,她就说:“你等一下哦。”
现在再回头看那一段,真的是青春的沧桑啊。我想每个人如果有一段刻骨铭心的爱情在心里面记着也不坏,不然白走了这一遭。特别是几年后有一次开车去加油时碰到她,两个人就在那里聊天,一切都成为过去,就讲自己的家庭怎样。
她后来的命运不是很好,她先生的生意做得不好。她打电话跟我借钱,说她儿子在日本念书没钱了,要我借给她。我说:“好啊好啊,没问题啊。”她竟然跟我讲,欠我的钱等她退休时用保险金还我。我就用很脏的台湾话骂她,就像年轻时骂她一样。
后来就是这样,好几次帮她渡过难关。有一次我们一起去参加一个婚礼。人家知道我们的事,说:“怎样,现在看到阿真,会不会心脏咚咚咚?”我说:“不会啊,我现在看到她心想还好没和她结婚。”
人家问为什么,怎么这样讲。我说这样辗转发现旁边睡了一只大象,我会觉得很可怕——她后来变得很胖。因为很熟悉,所以非常亲近,可以开这种玩笑。一切都已经成为过去。
我一辈子没有拉过她的手。
(天 问摘,李 晨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