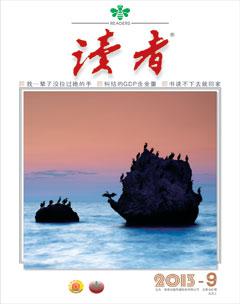谁喊住我
2013-12-25 02:12刘亮程
读者 2013年9期
刘亮程
当我走了,那滩芦苇会记得我。那棵被我无意踩倒又长起来、身子歪斜的碱蒿会记得我。那棵树会记得我。当树被砍掉,树根会记得我。根被挖了,留在地上的那个坑会记得我。树根下的土会记得我。
多少年后我如烟似风的魂儿飘过时,谁会喊住我?谁会依旧如故地让我认得我的前世?
能挡住我风一样的魂儿的,必定是那堵残破不倒的土墙。能缠住我烟一般的魂儿的,除了年复一年的草木,除了一朝一夕的炊烟,还会有谁呢?
我认识的人们不会再在那个时候站在村头。和他们相貌一样的子子孙孙会在这片土地上来回走动。他们说话的声音不会让我陌生。在那些院子和田野里,人们依旧干着多年前我干过的那些事,吃着多年前我吃过的那些食物。我依旧会在那时的微风里,闻到米饭和拉面的香味,闻到炒土豆和酸白菜的香味,闻到酒、烟叶和清茶的香味……我在虚无的飘游中必然被它们唤醒。我会激动,会无端地感激我曾实实在在经历的一切。这让风中缥缈的我逐渐有了意识,让早已成一缕烟、一粒尘土的我,突然间有别于其他的烟和尘土。
(冯国伟摘自《兰州晨报》2013年2月17日)
猜你喜欢
小学生学习指导·小军迷联盟(2021年2期)2021-03-24
金山(2021年3期)2021-03-24
少儿画王(7-10)(2020年11期)2020-09-13
作品(2020年8期)2020-08-06
安徽文学(2019年6期)2019-06-28
小溪流(画刊)(2018年3期)2018-06-29
扬子江(2018年1期)2018-01-26
艺术评论(2017年3期)2017-05-04
当代工人(2015年12期)2015-08-24
早期教育(美术教育)(2006年4期)2006-04-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