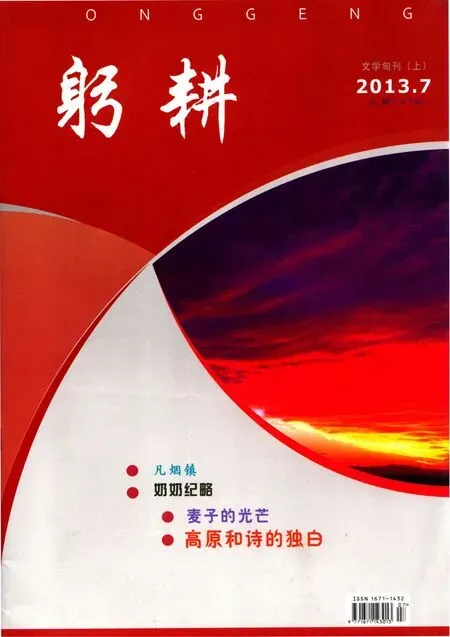院·庙·庵
◆ 石孝义
终南别业
唐 王维
中岁颇好道,晚家南山陲。兴来每独往,胜事空自知。
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偶然值林叟,谈笑无还期。
院
两块青灰色的屋顶在丛树掩映的缝隙里露出一片片瘦骨嶙峋的瓦片。沿着东墙外的一条小路一直下去快到山脚时,可以看到一座被风雨磨烛得斑驳不堪的石牌坊。从那里仰了头就可以看到树隙间的山门了。到处都是树,从密密匝匝的树叶间不经意地逃出来的几片赭红是寺院的山墙。午后的阳光正好从山门楼子的挂脊上斜照下来,景物在光晕中变得有些恍惚了。德胜院三个字只能看到一个胜字,其它就都掩到树影之中了。顺着山间小路一直爬到山门,往里瞧,原来离内院的正殿还有一段距离呢!仍是一条细瘦的小路像一条干瘪的肠子似的连上去,陡且滑。等站在正殿前的场院再回身看时,除了剩下门楼的半个挂角外,便只有挂角上的铜铃声若隐若现了。
院里看不到人,只有正偏三殿香炉里烧残的香仍旧寂寞地在花树与殿宇间飘渺着。三座大殿映衬出来的阴凉堆满了殿前的整个院子,深得像水,冷得像冰。人走进去就像淹到了湖水里,凉会从四面八方不由自主地一同朝你游来。进山十里的山路,游人走得热了、渴了、累了,极想找个地方休息一会儿。可放眼四周,殿房的门都开着,却没有一个人,空荡荡的使人感到寂寞。多好的清修地方啊!游人从心底里生起一丝眷顾。难道没有师父住庙?这样想着,朝四下里巡视了一圈。隐约感觉西侧的月亮门外有动静,游人信步走了过去,门口的地上趴了一条黑狗,已经睡得昏天黑地了。
出了月亮门后眼前忽然变得豁亮了,一块不大的菜园子,里面胡乱地种了些什么。几根竹枝搭起的架,却没见有爬架的植物。北面是一座用石头砌起的高台,两间青砖的瓦房就端端正正地坐落在上面。几声若隐若现的谈笑从高台上传了下来,抬眼望去刚好被一棵茂盛而粗大的柿子树挡住了!
走上石阶,几根拳头粗的竹篙围着柿树搭了一圈花架,满架的瓜藤中插了许多大朵大朵的绸布绒花,这或许是主人的兴趣所致吧!两张折叠的小方桌,上面摆了些花生水果和茶水。几位游人围坐在一位五十上下的老尼师周围听着她“闲话”论道。人群里不时地爆发出一阵阵笑声,游人站在树影外,静静地听着。在尼师脸上堆起的笑容仿佛夏日正午的骄阳,灿烂而不失慈悲!游人从人群后面拉过把凳子来悄悄地坐下来,惟恐惊扰了前面人们的谈兴,即是如此,还是没能逃过老尼师慈悲的眼睛,她微微地冲游人头了下头,可这已经包含进了所有的接待……
茶尽人散,游人总归是水,一定要流走的,小院安静下来时游人与尼师仿佛成了潮退后的沙礁,那一刻游人忽然感到有些凄冷。老尼师的笑容依旧不减,谈兴也不减。木讷的游人只是静静地听、默默地喝水,偶尔插上两句也多是附和。高台下的小路上忽然有了人影,一位六十多岁、瘦小枯干的老和尚佝偻着身子一步一步地爬了上来。游人起身相迎,老和尚却是始终垂着头、低了眼不理不睬,仿佛是睡着了。和尚走到里边的一间小屋门前一闪身,哐地带上了小门。老尼师笑着说:“老修行是从江西过来的,在这闭关已经有一年多了,每天除了解手出去,一天基本都在打座修行中……”游人哦了一声,心里竟一下子生起许多的崇敬,不觉抬眼又往那间小屋里多看了几眼,可黑洞洞的只是没有半点的声响。“我们这里正筹备修建一座十方寺院,你再进山时恐怕已经看到了。这里只是作为一个临时的筹备处,等寺院真正建起来了……”尼师提到这些仿佛有着无限的快乐与憧憬。游人静静地聆听着尼师的介绍,一缕山风吹来,花架南侧的竹竿上几件尘世女孩子的衣服随风飘荡了起来,一件绸丝的白色短衫上刺绣的红蝴蝶是那么的抢人眼睛。“或许是尼师的女儿的吧!”游人在心里默默地猜想,眼睛从那上面只略微定格了一下,就赶忙匆匆地收回来远远地投向了山那边的铁塔。
“师父——”游人的背后传来一声稚嫩的声音。游人回了眼,一个十七八岁的小尼姑正举着一本经书站在那里。这会儿见有生人在,怯生生的只是远远地喊着师父却不敢过来。尼师招手,小尼师这才腼腆地举步走过去。走过来的一瞬,游人看到一张苍白得没有一丝血色的脸,灰色的僧袍穿在身上显得那么不合体,可淡淡的却透露出来一丝超凡脱俗的清纯。
“师父这个字念什么?”小尼师端着经书指给师父看。
“看里面的注音。”
“可这个字有两个字音,在另一本经里还有一个读音。”
“这里注的什么就念什么!”
“唉。那我先去地藏殿忏悔去了!”
“去吧!回头拿几本《金刚心总持论》来给这位施主。”
“唉——”
老尼师慈爱地注视着小尼师欢快地跑下高岗一闪身跑进月亮门里去了。不大功夫,小尼师又轻快地跑了来,手里举了两本红皮的经书。
师父说,“给这位施主一本!”
“唉——”依然那么清脆的答应。
游人到过许多道场,却总没见到过像这般清纯超俗的小师父。正愣神呢,小尼师已经将手里的一本经书递了过来。
“多谢师兄!”游人接过经书忙双手合十道了一声谢。小尼师却一下子羞红了脸,呢哝着低声说:“人家是女孩儿——”
“女孩儿也叫师兄!”老尼师接话。
游人笑着点头,小尼师忙腼腆地道了声,“我先下去了。”便像只小鸟儿一样跑走了。在她转身的一瞬,游人看到小尼师头皮上还没有落戒疤,便问道:“刚刚出家,还没受戒?”老尼师说:“哪儿啊,她还不是沙弥尼呢。月前才来,本来是被父母带着去北京看病,顺路一家来这里游玩,和我搭了会儿话,这孩子就发心非要留下出家。他父母开始舍不得,后来也禁不住这孩子的软磨硬泡,最后也同意了!我只是给她先剃了发,实际上还没真正入佛门呢,现在让她先自己熟悉一下佛门的规矩。”游人默默地点了点头,一阵清香飘来,游人的心里莫名地有些怅惘……“哎,说起来,这孩子的命挺苦的!”说着尼师压低了声音对游人说:“她妈偷着告诉我,这孩子的病挺难治的!家里尽管有钱,所有该想的法也都想到了,可始终是不见效,到如今家里也不抱什么想法了,就想她自己愿意做点什么就做点什么吧!只是这孩子的心气还挺高的,什么都好奇,什么都想尝试,那天还和我说,等我的业障消了,我就去普度众生!唉,也毕竟啊,才刚刚十八岁,一切还都没开始呢!”说罢,小院里一下子陷进了沉默。又坐了一会儿,不知不觉中西山已见半抹红云。游人收拾起背囊又重新准备上路了,尼师将游人一直送下了高台,依旧是那副灿烂无欺的笑容,仿佛将夕阳下的红霞都映衬得越发绚丽了。
山风习习,从小沙石路往下走时。游人看到远处赭红色的山墙下,那位落剃的少女正端坐在一块大青石上,手里捧着一本经书正在细声地诵读着。那苍白的面容此刻被西天的云霞染成了艳艳的桃红,漂亮却依旧那么清纯。晚风中的“小沙弥尼”悠然地抬起头时,却意外地发现山路上游人那定定的目光,不由得羞红了脸,忙将头扭向了西边苍茫的群山……天色愈发深沉了,夜来临之前,游人想,“晨钟暮鼓声中,那女孩又该是个什么样儿呢?”
庙
直上直下的山像柱子一样立在那里,难怪人们管它叫丫髻山,真的像丫环头上梳起的高高发髻。游人的越野摩托还是疯叫着一直开上了半山。山道旁,一所青砖青瓦的青色院落像是被冷落了到了一边,蚁群般从院前经过的信众们都是匆匆赶往山顶的玉清观。偶尔会有廖廖几个游人从青砖的院门里溜达出来,带出的仿佛都是一股寂静。
游人整理了一下大大的背囊,用手指梳了一下有些潮湿的头发,迈步走进了小院。进门的一瞬他仰头看到门首的牌匾上写着“东岳庙”三个金字。依然没有人,只有寂静无处不在。青砖地上的砖缝里已长出了许多蒿草。回香亭正殿的门大开着,黑洞洞的,走进去一股咸潮味儿扑面迎过来。桌案上早已积了一层厚厚的灰土,还有一些散乱的香灰也不知是什么年月的了。庄重和寂静衍生出一种森严在殿内四处游行着。转过回香亭,灵官殿前的庭院忽然变得开阔起来,两厢排列着十几个小号似的单间,间间里面都露出面目狰狞或痛苦不堪的泥像。游人的视觉被新奇牵动了,手里的相机就像疯了一样横扫了过去。“站远些拍——”一个女人圆润的声音从身后传来。游人回头,一袭藏青色的道袍,头上戴着一顶黑色的圆顶道冠,原来是位四十左右岁的白面道姑!游人不失时机地按动了相机的快门,道姑的步子稍稍慢了下来,面对游人的镜头,不但没有嗔怒反倒莞尔笑了:“没看到吗?十八层地狱,超度亡灵的地儿——站得别太近,太近了晦气!”说话间,人已到了角门处,一闪身不见了。游人回味着刚才的话语,回转头再去看时,发现厢下那一组组动人心魄的“地狱”景象,真就让人生起一种恐惧来。他这才明白,为什么来这里进香的人会这么少了。想到这,他也就拎起相机,一溜烟似的随着中年道姑的身影跑去了。
东岳庙,门首正中的殿名竟然与山门牌额上的一样,大概这座道观就叫东岳庙吧!刚刚进了角门,就听到了右手侧面的法物流通处里有说话声。游人循声走过去,满屋墙上贴的都是符咒,地上则东一堆西一处地堆满了各种法器。在靠东墙的沙发上两个女人正在交谈着。却是一俗一道,俗的是位六十上下岁的老太太,脚底下放着一支提袋,里面都是些香烛供品。道,便是刚刚那位师父。见游人进来,道姑微微笑着指指旁边的一只凳子示意游人坐下。老太太正在喋喋不休地述说着自己与自家的诸多不如意,表情愁苦而肯切。道姑的表情却自始至终都是微笑着的,偶尔会轻声插上两句,但大多是在倾听,宁静的面颊上流淌着一种像玉一样的温婉。
游人在一边静静地坐了一会,似乎有些厌烦了老太太的絮絮叨叨,便要起身离去。正巧窗外一阵清脆的木鱼声传了进来。游人去听,是从东岳庙的大殿中传来了。隔窗望去,殿门里黑洞洞一片什么也看不清。再听,木鱼声中已揉进了一份温婉圆润的女孩子的诵经声。“那是我徒弟在上早课,”身后的道姑大概看出了游人的好奇,说道:“刚刚出家不久,你听那声音还有些涩!”老太太的唠叨被打断了,游人从窗外收回眼神。“这会儿好了,你听木鱼声变得流畅了!这孩子开头念的总是不太熟。在这处道场里,因为有阴司所以诵经做道场时可不敢马虎一点,感召很厉害的……”道姑的脸上仍是那副淡淡的笑,白净的面颊上流露着平静。游人的好奇心使他有些急不可奈了:“我过去看看,可以吧!”道姑淡淡地笑着点点头。
殿内只有近门的地方才挤进一米阳光。就在阳光边缘的红色跪垫上,一位十七八岁披着大红色斗风的小道姑正跪在那里诵经。她左手的竹签插在翻折的经本里不停地翻动着,经本便仿佛像条活蹦乱跳的鱼在桌案上跳动起来。沙沙沙的声响伴着木鱼声,一同绞进了念诵声中去了。游人蹑手蹑脚地走到小道姑的身侧,悄悄地端起了相机。大红的披风在昏暗的大殿内显得有些扎眼,高高挽起的发髻,飘红的发带,游人的脑子里莫名其妙地忽然想起风尘三侠里的红佛女。高高的神像觑着眼慈悲地俯看着大殿,小道姑嘴里的经文几乎全是平音念诵出来的,她的眼睛在经卷间飞快地流动着,可隐约的总让人感觉那眼神中掩饰着一股幽深的悲戚。“铛——”引磬响了,师父刚好一步迈进殿来,背着手在门口的光亮中站立着。小道姑的头没有回,或许是她对身后的师父太熟稔了,也许是置身世外的她已将这个红通通的世界早已丢弃了。只是自己默默地向神座上的娘娘做着礼;慢慢地合上经卷;脱下身上大红的披风;收拾好桌上法器。师父的眼睛忽然落到案桌上的一张黄表纸上,眉头一下子蹙了起来,她快步走上前,一把从桌案上将纸抓了起来,迅速地扫了一眼,然后怒气冲冲地冲着小道姑喝斥到:“给我烧了!”说罢丢下纸就走,可刚走了两步又一下子回过身来冷冷地加了一句:“——别忘了,你已经出家了!”小道姑的脸上由忧郁变成了悲戚,进而眼泪扑簌簌地掉了下来:“昨天,朋友来电话。他在工地上因为事故去世了!”师父的脚步一下子僵住了。她这才想起,自己刚刚抓起的纸是超度亡人的表文。她木讷地转过身来望着徒弟,想伸出手去抚一下徒弟流满泪水的脸,可伸出的手刚刚触到徒弟的面颊却又像被蜂蛰了一般迅速地抽了回来……
庵
石头小路和庵庙的木碑都被埋进了繁茂的树丛与荆棘之中。所以若不是半山的钟声,是不会有人注意到在这深山老林里竟然还隐匿着这么一块清静的去处。
左手追着石头小路逶迤而上的是一条赭红色的矮墙。像是一条乡下女儿新婚陪嫁的花被不小心丢在了山路上。偶尔会有桑树从小路的一边闪跳出来,满枝头的桑葚招引得游人不管不顾地拼命去撷摘,兜里、塑料袋里、嘴里装的哪儿都是。树荫盖住了山路,阴凉得仿佛是一条刚刚冰融后的小溪从山颠奔腾而下。再往上走就少有游人了,脚底下踩到的石阶发出咚咚的声响,山便有了回声,心也就在午后那片光亮的世界中越发越变得宁静下来。
那直直的百十阶石阶是执意要将山门楼子顶上天呢!满世界肆虐狂行的绿被来自四面八方的山驼着挤压过来,逼迫得那座小小的、红赭色的门楼没得办法了,只得孤傲地高耸起来。瓦蓝瓦蓝的天空中便又多出了一条横亘出世的飞檐,于是凡是来此朝山拜庙的人,也就不管你地位有多么显赫还是腰缠多少黄金,一律得让你仰了头去看,低下头去走才肯放你进到庵中!
站到庵门下,有一种高高在上的感觉,正殿前一座黑色圆铁香炉刚好挡住敞开的殿门。庵院里不见有香,不见有人,不见有声响,只有一棵山楂树在山门楼子的东侧旺盛地生长着,投下的一片长长的树影一直慢慢地攀爬到游人脚底下的石头台阶上。一院子的阳光装得满满的,仿佛要溢了,要泄了。满满的光亮因为长久没有人的打扰,竟也沉淀出一股子静来,让人不忍轻易去踢破它。东侧客堂的竹门帘“啪——”的一下挑起。一位身着灰布僧袍的尼姑,闪身院内。三十上下岁的年纪,脚底下步履匆匆,只是在那举手投足之间分明携带着一股直率。游人的好奇心趋使他快速地掀动了相机的快门,闪光灯亮处,大概是惊扰了出家人的那份宁静。“删了——”一声短喝。一刹那间,游人看到了一张扭过来的冰冷面容。“是啊!毕竟没有经过人家同意!”游人有些惶恐。想着,游人的手指便不由自主地摸向删除健,可随即又是一声喝斥传来:“——听到了没有,删了!”从这位尼师的神色中游人分明感到了一种欺凌,游人的自尊心一下子被剌激了,他嘴里冷冷地哼了一声,甩手丢下那位尼师大步流星地走进了东侧的般若殿。
般若殿也是法物流通处,满架子摆放的都是学佛的启蒙书和入门的光盘。桌上点着一支长长的檀香,檀香与书香混凝着竟调出了另外一份尘世外的安静来!游人心里刚刚点燃的那丝不快,在这清香里竟默默地有些消融了。游人抽出一本憨山大师的经论翻阅着,不知什么时候身后传来一阵细碎的脚步声。“这本书不错!”游人回过头去,来人竟然就是刚才的那位尼师,她手里正举了一本《太上感应篇》递过来。“哦,看过!”游人一下子拉下脸,冷漠地答道。尼师一时显得有些尴尬,但脸上已然没了刚才那付凌人的怒气。“这张光盘也不错!”游人看都没看就顺手递给了旁边一位正在翻书的老者:“这盘是不错,我看过了,您看看!”尼师无语了,只得无奈地摇摇头转身迈步出了殿房。游人看着她的背影,刚刚那股怨气忽然一下子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又闲溜了一会,游人朝着西侧的斋堂走去,还没到门口呢,已经听到里面传来两个女人的说话声,一个声音低低的听上去像是个十八九岁的女孩子的声音,而另一个声音一声声总是挑上房顶,游人听出来了,就是刚才的那位尼师的声音。
“姐,我爸那病一月得做十次透析,一个月就得五千块钱,咱做不起啊。后来和通州的几家有一样病的人联系了一下,大家决定共同买一台二手的透析机,这样就省多了,一次花个一百多就解决了。可这台机器得十多万。咱家该借的都借到了,我爸这些年治病本身就已经把家熬干了,村里人出主意说找四姐你,他们说现在的出家人都有钱。好多大款、大官们都围着你们转……”
“这是谁这么胡说八道,小颖你看我这衣服从出家到现在一直穿着,都快八年了。庙里的那点善款连每年僧众的吃住水电维修都不够。再说我们师父树的是正信的道场,从来不卖香火钱,不做道场超度,到现在还欠着村里的水电费几十万呢。话又说回来,庙里有些钱那是供养僧众的钱,俗家人又怎么敢用,那不是给你造孽吗?不瞒你,我一个月加起来连善众的供养加庙里的香资也就四五百块钱,每年都得跟家里要钱……”屋里陷入了沉默,接着又听尼师叹了口气:“哎,你听我这唠叨了半天干嘛呢。四叔的病也是怪让人心烦的,我这里还有两千块钱的积蓄,你拿着。另外去年冬天我弟弟刚给我买的笔记本电脑,你回头拿去把它卖了,先救救急!”
“姐,不听你说我还不知道你这么清苦,那我还是到别处想想办法吧!”
“行了,别说那些没用的话了。”尼师的嗓门一下子高起来,“你来这儿,我能让你白跑吗?再说你爸是谁,那是我四叔。我的脾气你又不是不知道,但凡我能帮的,什么时候袖手旁观了?”女孩不说话了,尼师的语气也缓和了些:“不过,回去你告诉那些没事天天胡造谣的人,别整天没事干,乱嚼舌头根子玩!记住了吗?”
“嗯。”
屋里人好像是听到屋外有人,话音一下子停止了。
游人只得上了台阶迈步进了屋。抬头看时,南墙下摆了一张实木的红漆木雕方桌,四张红漆木椅,一套棕红色的泥制茶具,茶香袅袅萦绕满屋。正中坐着的正是那位刚刚见过的尼师。她见游人进来轻轻地点了下头,这样刚刚的不快也就都冰释了。与许多佛堂不一样的是西墙上挂着一张白描淡彩的菩萨立轴法相。不见香案,亦不见果供灯烛,游人心底里暗暗称道:到底是禅宗的道场,无处不流淌着随顺自然的天性。
望着墙上的画像,游人问:“这画上的不知是哪位菩萨?”
“伽蓝菩萨!”尼师说过之后又笑着补了一句:“管斋堂的!”
“来这里坐吧!”尼师招呼着。斋堂里清静阴凉,除了院外的蝉吵声找不到半点尘世俗音的打扰。典雅精致的茶具、古色古香的茶案,桌对面坐着的是一个二十多岁的俗家女孩。细嫩的皮肤,白里透红的脸颊坐在那里一直低垂着头,一副羞怯的表情。新茶洗过两轮后,主人抡起杯,“来,喝——”尼师敞快的嗓音,以及抿住嘴角品茶的样子让人不由得想到了酒肆里的举杯豪饮者。加上举手投足之间的随意畅快,活脱就是《水浒》中的鲁达。于是这种感觉一起,连她倒出的茶水声似乎都变得铿锵有力了。就在尼师捋起的袍袖斟茶的一瞬,游人在她胳膊上猛然看到一个寸来大小,歪歪扭扭的忍字,这在乡下一些半大小子当中会常看到,游人一愣一下随后感到有种莫名的真实从心底里生起,仿佛一直由袈裟阻隔的神秘一下子变得亲切了。
尼师不大会讲经论道,讲了也像是听乡下人在夹夹生生地谈论宇宙人生。她喜欢谈些乡情俚语。从谈话间才知道,这位尼师出家也有七八年了,最早是从柏林寺落剃,然后追随了这里的当家师父过来的,之前干过酒肆饭庄,倒过鱼卖过海鲜……
不知不觉中墙上的挂钟已经当当地指向了午后两点了。游人只得为着下午的禅修课匆匆告辞了出来,在站起的一瞬,游人扬起手中的相机,笑着说:“不介意拍一张吗?”尼师迟疑了一下还是直爽地谢绝了:“不了,下次吧!我讨厌照相。”游人无奈地说:“好,有缘再见吧!”尼师一直将游人送到了山门,午后的寺里与山间仍旧一个人没有,除了鸟。游人走下石阶时,回头仰望一袭灰袍的尼师仍旧洒脱地挺立在那里招手,那刻游人忽然有些感动。感动什么呢?或许真性就是佛性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