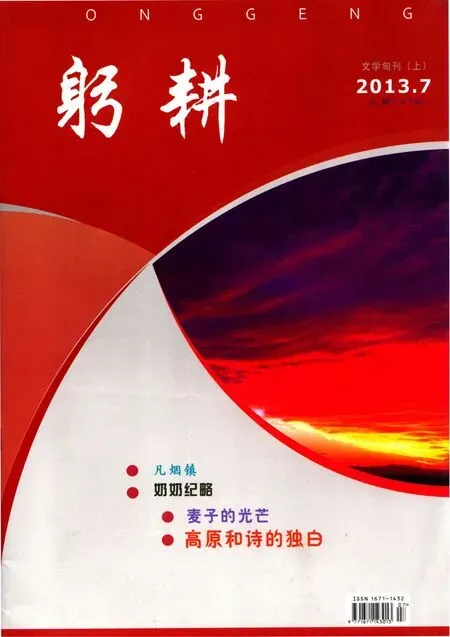麦子的光芒(外一篇)
◆ 任崇喜

时常有一双眼睛在面前清晰着。
说不出来的那种亲近,宛若时隐时现的河流,在我情感的脉管里缓缓流淌,沉淀着一种清明的色泽,鲜亮我心底最为隐秘的部分。这时间,即使有一阵风吹来,穿过风声,我依然能捕捉到它的神韵,那是我心底的方向。
就在此刻,眼睛就在我的面前显现。细长的眼眉沉沉的,似启微闭,熟捻得如同一个走不出我视野的女人,时常眯着眼睛,在朝我张望着什么;如水般的柔情淌过来,我便泊在其中。我需要的不过是这么简单的一种感觉。
是那次无意间的临近,在远离青青气息的地方,我坐在澄黄的阳光下,与它亲切地交谈。那些脱离母体的生命就在我的手掌上,未曾脱离稚嫩的色彩,长长的,细长的眸子,让我有些模糊了少年的记忆。用手轻轻地掐,竟有了些乳白色的浆,模糊了眼眉,模糊了这个季节我东南方向的家,模糊了我曾经设想过的那褐色的眼睛朝我张望的那些旧事。我有些陌生地把它们随意地弃于阳光下,这不是收获的季节,澄黄的阳光能还它一些本色吗?
这时,你该能明白我企及的是谁的眼睛,不错,是麦子,我久违的麦地里的麦子,那些真实裸露的麦粒。
无数个同样的日子,我背负着那双眼睛,行进在这远离稼穑的大街上。阳光真好,一方天蓝省略了许多纯净的语言;麦芒般的阳光,均匀地射在我的脊背上,一种莫名的感动。如今的我只能借助阳光的提醒来唤回关于眼睛最初的印象。在这几乎不知道季节变幻的地方,连鸟儿也很少飞来,听不到“麦儿快黄麦儿快黄”与“吃杯茶”的啼音,没有人能听得懂。对于这种声音,我已然有些陌生,只能想象那双眼睛在亮丽的阳光下,在乡下老家那一望无垠的澄黄麦田里,正闪着烁烁的光,那些亲切而细长的眼睛在等我走近,走回红蜻蜓绿蚂蚱曾经相伴的岁月。那些青翠的日子呵!怀想是一种激情。很早的时候,我喜欢一个人静静地坐着,不知不觉就会走进内心梦幻而美丽的花园去,撷取一些意想不到的花朵。而今,在生长不出田园情调的地方,我只能借助想象的力量回望那双眼睛,树叶般的阳光就在此刻灿烂着那方田园,明晰着那双眼睛。我记忆中小小的家在河的那一边,隔着平原,我在风中依然嗅得到那种熟悉的味道,风声过处,年过半百头发花白的母亲是那方土地的守望者。
一
我曾是母亲田园里的一棵青青的麦子。
北方所有的农事中,麦子的种植与收获的过程显得格外漫长而艰辛。这时常令我想起现在居住的城市里的浮躁的人群,急乎乎的行色匆匆,却又急不出什么所以然来。还在头年秋天,雁声的韵脚掠过村庄时,农人们就要耙地施肥,抢着那苍天降临的好墒情,迎风播下一粒粒坚韧的种子。我曾仔细看过,那种子坚硬得有些瘦削,放在口里是一种清脆,让人感叹麦子生命力的顽强,即便是寒冷萧索的季节,竟也能从干坼的土里探出头来。先是星星点点的绿,在秋后的原野能发现生命的原色真是奇迹;接着伸展开细嫩的叶,竟也萋萋地生长起来。那份旺盛,没有人怀疑这样生长下去,不久期待中的幸福就会临近。然而不,你听,凛然的风已挟着洁白的雪呼啸而来,那些北方冬季的宠儿,洋洋洒洒地改变着北国的容颜,成为麦们越冬的被褥。梦幻般的阳光里,那些憨厚的农人就站在麦田旁边,呵搓着手,站成了一帧风景,他们的心事一定如雪般洁白。
小时侯,几乎是整整一个冬天,我们都在雪的气息里呼吸着。是雪,让我们觉出日子的存在与漫长。我们小孩子是这季节的兔子,喜欢在雪地里疯着玩,到田野里去是免不了的。我曾经行进在雪后的平原,并有意识地刨开一团雪。于是,在依旧温暖的地平面上,在有些潮湿松软的泥土下,我看见了麦子青翠的叶片在冰凌下面透着一种光泽,与泥土相近的光彩;我看见了裸露的根部,那种质地如生命的底蕴,又如我曾经的乡村生活。而今,它们在我的心底写意成了一种忍耐与坚韧,写意成了一抹鲜亮的启迪。
雪融不久是春天,一切都变得明快与爽朗起来。经冬尤绿的麦苗仿佛在漫漫冬季蓄满了精力,又仿佛脱掉了臃肿冬衣的姑娘,青春的活力一下子迸发出来,生长得格外迅疾恣肆。置身麦地,踏着松软的泥土,你会体味出有种强大的力量上蹿着,冲撞得人心口有些紧。这时候,身边有和煦的杨柳风依依地拂着,有细密绵软的雨儿轻轻地润着,还有蛋黄半的嫩阳柔柔地暖着,麦苗细嫩的叶子,就在这宁静的情调中日渐一日地在苍翠茁壮起来,整个乡村的请调都仿佛因此濡染了文人雅士的风度,淡淡浅浅地透着清丽与明快。
天一日日地暖和起来。坐在麦地是一种享受,只为着那分青翠与宁静,在我乡村的家的庭院后面,不远处便是田地。在偶尔回乡的日子里,因着内心依然无法放下的诸般纷繁芜杂的事情,我常常把自己“放逐”到田野里。在这里,我是自然的,青翠的植物是自然的,鸟儿的啁啾是自然的,人自然回还原成真实的自我。在麦地静坐着,时常可以看见那些略有所待的农人们在田边走,那种恭敬温柔的神情让我时常想起自己行进在方格田园里的心情。这也是所有农人留给记忆中的印象。那份心境,脚下的黄土地知道,比肩而过的风知道,麦子青翠的叶子知道,那些隐藏在深处的眼睛也肯定知道。他们在风中半驼着身子,偶尔也停下来,看一看无垠的平原,看一看身后的家园,麦苗是静的,家园是静的,静谧得如影似幻。
下了雨,又施了肥,麦子们可着劲儿地疯长着。分蘖、拔节,拔节、分蘖,三五天就将麦地盖得严严实实的,麦杆也变得丰硕秀挺的,叶子肥厚丰腴,让人感到一种力的柔美与和谐。这时候漫步,一早一晚你会读出风景话题之外的许多东西。有烟岚在虚虚浮浮地缭绕着,有露珠在叶片上烁烁地闪着,仿佛专门在此刻为你等待着,放眼望去,郁郁葱葱的树丛飘渺着虚幻的光彩,浮动着,在乳白色的幕霭里,与麦地相映成趣;高与低的交叠,深与浅的错综,真与虚之间的演绎与过渡,让你由衷地惊叹大自然对生活的创造与超越;这不是匠人的慧心独具,也不是艺术家的神来之笔,它是自然的天籁,无须用语言来阐释,就那么简单而真实地存在。
我此刻就站在那些农人们曾经站过的地方,仿佛刚刚从长时间的蛰伏中苏醒过来,眼睛里满是惊异:才几日不见呢,麦地里那些初显的穗状的头竟也似羞还露地呈现出来了,那些期待中的眼睛就隐约在其中。在醺醺的小南风中,麦子们在悄悄地孕育着,孕育着期待,也孕育着骄傲,或动或静,或俯或扬,各具风韵。等麦地深成绿海的时候,正是乡下青黄不接的春三月,而正是那些初显的青青麦穗,摇曳着我们的心花,让我们憧憬迷醉。
二
当枣树米黄色的花粒开始吐露芬芳的时候,忙碌的气息已经开始在村子里弥漫。储备好镰刀、扫帚、桑杈之类的农什,翻晒麦囤,清理麦场,农人们为预期的丰收和幸福忙碌着。这时候,南风更急更暖,太阳也愈发地炙热,麦们便在疾风丽日中变得成熟。麦熟一晌,从麦芒开始,然后是麦穗、麦叶、麦杆、麦根,麦子以阳光的色彩写意着生命的历程。听,她们开始奏响自己的音乐了!辉煌灿烂的音乐开始在夏日里流行,整个田野在太阳的指挥下加入生命的合奏。阳光弥漫着黄灿灿的色泽,一棵棵麦子,就在那片晴朗之中完成了她们整个的生长过程。风匆匆地走着,先时还能翻开细细的波浪,从这边到那边,连鸟儿似乎也嗅出了其间沁人心脾的新麦清香,不停地在田野里翔过;但很快麦地再也看不到风的形状了,麦地静穆着,与阳光一起写意成等待的风景,如临近出阁的新嫁娘。
这时节,那些农人们更加亲近麦地。麦子在阳光下劈劈啪啪地展示着自己的成熟,农人们微眯着眼睛,掐下一穗来,用粗糙的大手揉一揉,吹掉麦壳,细心地数着麦粒,然后心满意足地放在口中嚼。我站在他们的身旁看着他们快乐的样子,阳光亮亮地落下来,落在我的肩上,落进我的眼睛,落在那些残存青色的麦子身上。我望着麦子,麦子望着我。只有一种温和,天瓦蓝瓦蓝的,偶尔有几朵白云飘过,阳光下的麦子无语,在天地之间,乡村静穆着,树丛静穆着。我是这个季子不知道成熟的一棵傻麦。
许多年后,回想起那场景,我只是在远远地听着季节那单调而富有力度的节奏,明亮的阳光和麦地的辉煌依然灼得我的眼睛发痛。我依然惊诧于少年的思想,我的情结依然被那麦地上的阳光濡染着、感动着。虽然我几乎没有与麦子相伴的农人生涯,不可能真实地掂出土地的分量,但在我的瞳孔里,依然喜欢那真实的麦粒,那梦幻般的眼眉,那如珍珠一般的麦粒,那凝望我血脉的眼睛。麦子那沉凝的颜色贯穿着我和麦地的快乐,那是我苦难家族永恒的维系。虽然我是城市的过客,我也是乡村的过客,我的根在脚下的黄土地,我青翠的枝叶却真实地吮吸着另一方天空的鲜润。
第一棵麦子被割倒了,锃亮的锋刃随着手臂优美的姿势,标志着农人们渴盼许久的麦收终于来临了。麦收没有序幕,一开始就进入了高潮,一种暴烈与匆忙的气息笼罩了整个乡村,先时还能听见自然的声响,转眼就变成了热火朝天的沸腾。农家五月少闲人,村子内外到处是忙碌的收割者,连空气也似乎因着人流而漾动着;白日炙热的阳光在头顶上烘烤着,麦杆也在焦急地甩着炸响,麦地仿佛马上就要因此而燃烧起来,农人们就像扑向烈焰的救火者。黄浊浊的汗滴开始顺着脸颊往下淌,淌进眼睛里,涩涩的,淌进口里,咸咸的,咸咸涩涩的汗滴,正唱着一曲古老的歌谣,唱和着生命的清香。麦子们纷纷倒地,麦地也因此开始变的空旷起来。一身尘土、满身疲惫,简单而拙扑的农人就坐在田垄上歇息,眼睛微红,默默地看着面前的麦地。有时候,我从文字的田地里走出来时,也时常这么静静地看一会儿誊写好的稿子,那些蝌蚪般的文字,就这样摇曳着灵性的尾巴,一直把我的情绪摇起来,让我重新走回那分圣洁。
麦子终于为那一片片露着麦茬的空地所代替,显得空阔而寂寥。除了零零星星的不变树丛和几个拾麦子者之外,麦地一无所有。就如我含辛茹苦的父母,几十年的辛勤奔波,除了我们几个子女和几间老屋之外,他们别无余物,而岁月在他们脸上刻下了无法抹却的印痕,让我时常不忍真诚面对。我记忆中的父母年富力强,依旧是在麦场。
麦场正中的是我的父亲、村人以及麦垛。
三
村南的麦场方正如同乡村的院落,南面一弯河水静静淌过,三面绿树密匝环绕,掩映出一方浓郁的田园风味。此时的乡村不喜欢飘渺的空白,只注重热情的厚实。那些散落的麦垛点缀成丰收院落中的树,远远望去,给人一种悠然恬然陶然的感觉,令人想起曾经青青日子里那么多葱茏的期待。叶子般的阳光散漫着,当真切地看见麦子惬意地躺在麦场上,不知会不会想到月光如水的夜晚,你静静地躺在烁烁的星光下,如一棵麦子平静而真实地呼吸。
乡村麦场的夏日黄昏,在热空里喧嚣的蝉声淡远了,湛蓝的天宇,有散淡的云儿轻轻拂过,最后挂在树梢上,掩隐在浓浓的绿荫后面,竟有了阳光般的色彩,是青青叶片与斑斓阳光的流睐。不远处,扬起的麦尘随风而落,夹杂的土粒与草屑随风飘远,只剩下麦粒如星而落——那是一种真实。我只是这个季节不成熟的一棵傻麦,只会怔怔地望着幸福。
这个季节的平原胸怀坦荡,孕育着令人激动和欣喜的幸福。在麦场临近的是一种惬意,离不开夏日热烈的氛围,鲜活如同冒沫的啤酒和鲜嫩的黄瓜。一个真正的农人,此时,站在家园壮阔的背景下,最能悟出幸福的分量抑或深度,颗粒饱满的麦子沉淀着昔日平静的生活和静守的期待。扬麦时的风,将杂尘和谎言一起摒弃,只剩下麦子的颗粒,什么也没有说,什么都说了,农人一生行进的是对土地的感恩。
父亲不是真正的农人,从大平原走出来的他依然能读懂麦子的眼睛;他感情的鲜亮部分还挂在故乡的柳梢上,丝丝缕缕地飘进他城市的梦中。我不是真正的农人,走在城市真实的阳光大道上,我熟捻的只是钢铁水泥构结的空间气息。乡村是我特别意义上的家,那里有我血缘上的根。虽然我也曾经在城市的梦中追忆过追云逐蝶的身影,而真实的我几乎连那些农具的名字也喊不出来。我们都真实地活着,一生中引导我们向前的是希望的影子,那些灿烂如星的期盼在前面引导着,使我们追逐的心永远不会累。收获的幸福充实而短暂,耗费我们更多宝贵光阴的,是无声的期待。
黄昏已经弥漫了整个平原,凉爽的风掠过我的身体。圆圆的月亮爬上来,有不知名字的鸟儿在清脆地叫着,我这棵傻麦在平静而真实地生长。
当我写完上面这段文章时,不知怎的,我又想起了我的父母。父亲已经永远地融合在那方土地,尽管他说过退休后要回到乡下的家,与母亲共守田地和几间老屋。我们依然在陌生的城市繁衍着他们的青枝绿叶。在远离麦地的城市,我时常因着内在外在的喧嚣而坐立不安,而一旦将笔植入那方田地,心竟莫名地开阔与平静,只是我依然不明白,麦粒的形状,为什么那般像母亲那双饱经风霜的眼睛?
时常有一双亲亲的眼睛在我的面前无言而清晰着。
南瓜,南瓜
——在去往乡村世界尽头的路途上,被光阴漫不经心记住的只是那熟悉的瓜蔓和味道。
想起她的时候,她还在从乡村的藤蔓走向城市的路上。
我看见她的时候,硕大丰韵的她就在一个方框后面散发着芬芳,清淡的白,雅致的红,灿烂的黄,容光焕发。阳光照亮的金黄,透过她的眼睛,在繁华包裹的苍凉中,让你看到宽阔天空中流云映照的淳朴,一种绚烂之后的宁静和单纯。我熟悉她的面容,表面平滑或者有瘤,这个季节,她长圆、扁圆、圆形或者瓢形的模样还隐匿在花朵之中;我熟悉她的肤色,赤褐、黄褐、墨绿或赭色,更有蛇皮纹、网纹或波状斑纹;我曾经熟稔她的方位和姿势,就在乡村瓦屋不太明亮的墙的一角,随意而散漫地舒展着身肢,不挤不闹,安静着岁月,绚丽亮堂着流水一般的布衣生活……
很早的时候,我不知道她竟然不是我们的土著。在瓜果中,让幼时的我奇怪的就是一些名字,比如西瓜、东(冬)瓜、南瓜。地理方位有东西南北,为什么没有北瓜?后来才知道,北瓜也是有的,就是我们耳熟能详的她——南瓜。
她是泊来的瓜。这一年生的草本葫芦科南瓜属植物,老家在北美洲南部,其野生祖先原产于墨西哥、危地马拉一带。有一说中国南瓜原产在亚洲南部(印度尼西亚、缅甸)。她的俗称有蛮南瓜、老倭瓜、窝瓜、缅瓜、老缅瓜、红南瓜、瓜斜瓜、砧瓜等。印象中,乡村有叫一种瓜叫面瓜,但个头远比她小。在乡下,我听到有人叫她北瓜或者胡瓜。难道荒蛮的胡地也出产这样的瓜吗?让我没有想到的是,我们熟悉的笋瓜、西葫芦竟然是她的兄弟,也有叫前者为南瓜的,只不过加个前缀。西葫芦和笋瓜传到中国时间比较短,大概100多年。
虽然她是泊来的瓜,但在元代贾铭的烹饪著作《饮食须知》就有南瓜的记录。元代的王祯所著的《农书》中说:“浙江种植一种南瓜,适宜在避光的环境下种植。秋天成熟,外皮色泽金黄。可以储藏到春天。”这说明元代中国已经种植了南瓜。李时珍云:“南瓜种出南蕃,转入闽、浙,今燕京诸处亦有之矣。”
在乡村的事物里,我从来还没有看见过像她这样如此博得一致名声的。她是蔬菜里贫贱的布衣,只要有适宜的水分和养料,就会无拘无束地快乐地生长。“过了三月三,南瓜葫芦地里钻。”印象中,这个季节,乡村墙头、地边、房前屋后,大多是葫芦或者南瓜,豆角、茄子和辣椒之类的菜蔬比邻而居。她的秧苗占地很少,成年后便向四处伸展,经常爬过自家的田埂到邻家串门,甚至连果实也安安稳稳地到别人家地里去了。南瓜苗刚破土而出时,娇憨的模样煞是逗人,两瓣嫩绿的叶片顶着陈旧的壳皮,就像一个小人戴着一顶很大的草帽。可是过不了几日,她就开始舒展自己绿色的梦想了。她的叶腋侧边生有一种卷须,具有攀援爬行的本领。不经意间,她爬过的地方到处是蓬蓬勃勃的藤蔓,充满了无限的生机,将个黄褐色的泥土遮蔽成一片阴凉。当她茎叶繁茂时,长长的藤蔓、宽宽的叶子爬满棚架,给人造就天然的凉棚,供人们乘凉避暑。
她逶迤伸展着长长的绿色藤蔓,让我寻找和发现在尘封的岁月里的乡村。
记忆中的有花的面容。
令我十分困惑的是,古代诗词咏花诗中,少见她的踪迹。大概诗人们不需要她的五彩,只需要菊兰们的情趣,尽管菊兰不能充饥。民以食为天,君子远庖厨,是两种境界。
她却从不关心这些,也不招摇。在她的生命里,似乎一直都蕴藏着对色彩的向往,这种单纯的梦想一直伴陪它开花。她仿佛是春天开得最迟的花朵,仿佛只为在眼光下绚丽,花期很长,一直会开到秋天,就如乡村里朴素的爱情。说不清它们是如何开的,仿佛是在一夜之间,一朵朵喇叭似的黄花就热热闹闹地开满菜园的每个角落,开满长长的篱笆,金色、透明的花瓣像阳光一样明媚。她的瓣厚而透明,就像浓郁的农事。就是这么一种花,鲜艳点缀在荷叶般的南瓜叶片中,便营造了浓浓的田园庭院韵味。盛夏的阳光穿过路旁茂密的杨树丛,将闪闪的金光半遮半掩撒落在绿油油的南瓜叶上。你可以看到,硕大的层层绿叶中,花们就像一群天真烂漫的孩子在微风中笑着、唱着,吐出丝丝清香。阳光明媚的地方,一些毛绒绒的小蜜蜂从一个花芯中跳到另一个花蕊中蠢蠢蠕动。空气中流动着安静,一望无际的安静,时间似乎静止了。
只是这般的花愈来愈少,好像隐匿在乡村岁月的深处,只那么一闪就不见了。
小时候,以为每一个花朵下面都会结瓜的,直到花朵干瘪凋落,还没见嫩绿的小瓜蕾长出来,就去问大人。后来才知道,花像有男人也有女人一样,有公花也有母花,公花就是“谎花”──不受粉的花。撒谎是人类的行为,难道花朵也有语言吗?
林黛玉曾经感叹:花开的时候,好叫人欢欣;花谢的时候,好令人伤悲。南瓜花却不同,花开花谢同样给人一种美的心境。花谢不久,它们就会像气球似的膨胀起来,结出一个浑圆敦厚的南瓜来。她对于自身仪表似乎无拘无束,只有长出来了,你才知道她的模样。你走向南瓜秧,用手拔开阔大肥厚的南瓜叶,便会看到了一个个墨绿色带有花纹的南瓜。小南瓜表面上分布着均匀清晰的墨绿色纹路,上面细小的绒毛是淡白色的,一不小心就会碰伤它,露出新鲜的表皮和晶莹的汁液。
果熟时节,大大小小、横七竖八的南瓜,有的像木桶、有的像磨盘、有的中间小两头大,形形色色。让人稀罕的是她的色彩,橙黄,墨绿,一抹抹浓深的条纹画上去,或者就那样红红绿绿,带着天然的艺术气质,朴实而内敛,素朴而华美。深秋风起,绿皮的南瓜就会变得金黄,阳光一样夺目的色彩。
“在严寒中,那些熟透的南瓜,像在村野里举起的一个个灯笼。”
“在冬天/想南瓜的时候/只能站在金边细白花碗上/粗粗地喊一声”。
这个热烈的季节,我想起了这位诗人怀想南瓜的诗句。
在西方,南瓜与一个节日有关。每年十月三十一日夜晚,在西方万圣节(西方鬼节),“南瓜、巫婆的扫帚、黑猫和各式妖怪鬼魔的服装已成为万圣节的标志。在西方三大节日之一的这个节日里到处可以看到化妆成妖怪鬼魔孩子,他们提着南瓜灯跑到邻居家门口。南瓜灯的样子十分憨态可掬,它是一个整个南瓜挖空,南瓜外面绘刻上笑眯眯的大眼睛和大嘴巴,然后在瓜中插上一支点燃的蜡烛,然后用线穿好,用竿子挑着。那可爱大脸四处游荡,换取孩子们美食。
让我没有想到的是,与南瓜在一起的还有浪漫。“我们的南瓜不知躲入那片草丛/使那个割草女的手指突然/热气腾腾 充满甜味。”在号称“中国情人节”的“乞巧节”,不少地方传说在七月七日晚上在葡萄架下能听到牛郎织女的对话。而在绍兴农村,这一夜会有许多少女一个人偷偷躲在生长得茂盛的南瓜棚下,在夜深人静之时如能听到牛郎织女相会时的悄悄话,这待嫁的少女日后便能得到这千年不渝的爱情。这个季节的南瓜花黄灿灿的,很好看,如同爱情,不知能不能结出爱情的果实?
让我没有想到的是,与南瓜在一起的还有女人的梦。在传统节日中秋节,古时有向月亮、月饼祈子的习俗,并逐渐衍生出了一系列祈子习俗和祈子物。中秋夜摸瓜、送瓜祈子习俗,便是以瓜来象征月亮祈子。用瓜来象征月亮作为祈子之物,不仅因为瓜与月亮同为圆形,还因为瓜在中国人的信仰中本身就是生殖崇拜物,所谓“瓜迭绵绵”,即是认为瓜具有繁衍子嗣的功能,这正好与月生殖崇拜相合。各地中秋摸瓜、送瓜习俗又有一些差异,有的地方是由祈子妇自己去摸回家,有的地方则由儿童摸瓜送给新婚之妇等等。至于所摸瓜之品种各地则不尽相同。有的地方为冬瓜,有的地方为南瓜。因“南”与“男”谐音,南瓜又被认为是生男之兆。
这或许有道理的。她一条细细的藤上,竟能躺满十几个硕大的瓜,还有什么果实比她丰满巨大?
这个生殖力旺盛的季节,回望那些硕硕的果的图景,我感到一种生命力的弥漫,听得见在土壤里南瓜籽萌芽的声音,看得到重复和继续的生命在温暖的境地中孕育。
“夜静下去,听没听见过,南瓜的呼吸和絮语,有香味又有色彩。”很符合我的心境。
想起一个词:暖老温贫。
这是从张爱玲的散文中看到的一个词语。这是一个让人感觉酸涩而温暖的词语,在现在似乎很难找到安放的地方,也找不到可形容的情景。她写的是小饭铺前的煮南瓜这样一种小吃,在那个年代,让她有一种“暖老温贫”的感觉。这样一个词语,让一种温暖的记忆在心中慢慢清晰,似有跳出的感觉。冬日里,万物萧瑟,一块温实的南瓜,总是叫你眼睛一亮。硕大丰韵的她让我们能看到什么?饥饿年代里的粮食代用品,灾荒年岁里的丰盈……那清淡的香,是日子的温润;那艳艳的红,是阳光的叠加。
她在农村很有人缘。有她的日子,是家常味道,粗糙简单却温暖可心。可以切成薄薄的片,配点大葱红椒来清炒;可以切成大块,放到锅里蒸;老熟的南瓜又面又甜,可以和米同煮成“填中悦口”的南瓜饭、南瓜粥;或者作馅来蒸包子,做菜卷、烙饼。我知道有不少蔬菜如同女人一样,怕老,怕岁月的飞刀刀刀催。她却不怕,越老味道越醇厚……
在豫西虎牢关黄土塬下,我曾经品尝过一道青菜:素炒南瓜头。南瓜头其实是南瓜藤上的幼芽。把嫩苗和叶柄采摘下来,佐上红辣椒青辣椒丝,急火清炒,脆嫩清甜,柔香余韵。吃在口中,一种生涩,青气十足,口感极好。
据说,南瓜花柄、花托、花冠也能吃。花柄去皮,花托去表,花朵去蕊,其余都能吃。当然只能吃“谎花”,结果的花谁也舍不得吃。吃南瓜花,也分两种。一种是精炒,将整朵的南瓜花洗了,热锅急炒,勾薄芡收汁;另一种仍是裹了米粉蒸熟,要带了花蒂,晒干,油炸。我没有吃过,不知道它的滋味,现在也不知道乡下的人是否这样吃。
古人讲:医食同源。《本草纲目》里说,南瓜“甘温,无毒,补中益气”。近年来,她从乡间走俏华美的宴席,还是那身乡里乡气的衣裙,让人对她青睐的是丰富的微量元素钴和锌,既补血又减肥。现代医学也认为,南瓜对糖尿病有治疗作用,可直接食用,每天煮南瓜一斤,早晚2次分服。另外有发现,南瓜含有一种防癌的酶。在我的印象中,有一种形如南瓜而较小的桃南瓜,皮色红黄似金,因可供观赏而又称为看瓜,民间常用来治哮喘。
“在盛放和枯萎之中,在伤害和逃避以后,所有的意图和结局,都变得像晨雾中的玻璃窗一样模糊不清”。南瓜,南瓜,念着这个乡村意味的名字,耳边仿佛又响起那首经典民谣:“红米饭,南瓜汤,秋茄子,味好香,餐餐吃得精打光。干稻草,软又黄,金丝被儿盖身上,不怕北风和大雪,暖暖和和入梦乡……” 对于我这个年龄的人而言,那个时代是英雄与艳羡的年代。现在的年轻人,对于那些都陌生了,仿佛在听一个遥远国度的童话。
“南瓜是和硬硬的红米饭/一起消失的”。没有感伤与留恋,一种简单的蔬菜,黄土地和阳光的色泽,让我回想某个时段生活里逗留的痕迹和无穷的诗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