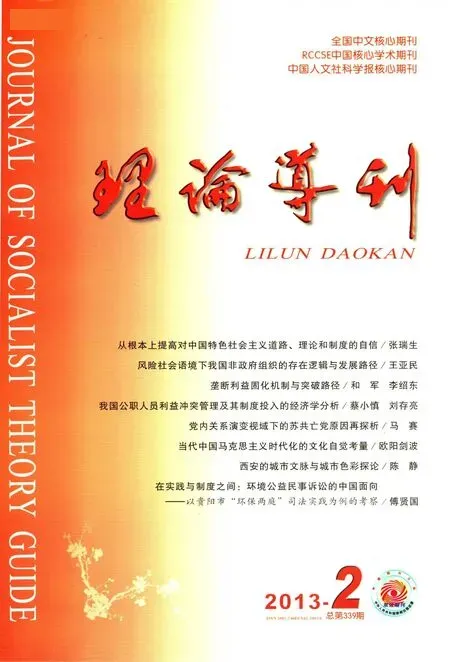党内关系演变视域下的苏共亡党原因再探析
马 赛
(嘉兴学院思政部,浙江嘉兴314001)
自苏共亡党20余年来,学界对于苏共亡党的原因从各个角度的探讨从未停止。在这个问题上,邓小平曾一针见血地指出:“关键是我们共产党内部要搞好,不出事,就可以放心睡大觉。”[1]381可以说,苏共党内关系的逐渐演变直至异化,是导致其最终衰亡的重要原因。
一、苏共党内关系的演变过程
1.列宁时期:“民主集中制”的党内关系。1902年的俄共二大,列宁和孟什维克在组织问题上出现分歧;1905年革命后俄国出现短暂民主,加之普列汉诺夫、卢森堡等人的批评,列宁采用民主集中制作为苏共党内关系的基本原则,包括“少数服从多数”、“党的最高机关应当是代表大会”、“党的中央机关的选举必须是直接选举,必须在代表大会上进行”、“对党内任何少数人的权利同样应在党章中作出明确的规定”,[2]154-155并在党的四大上写入党章,“党的一切组织是按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建立起来的”。[3]165这也标志着列宁党内关系思想基本成熟。国内战争时期,出现过短期的“战斗命令制”,但随着和平时期的到来,苏共党内关系向着民主进一步迈进,党的十大上提出了“工人民主制”,包括“排斥一切委任的制度”,“从下到上的一切机关都实行普遍选举制、报告制和监督制”。[4]54这代表晚年的列宁对党内关系的最后一次思考,尽管这一制度并没有被写入党章,但这些设想都是对民主集中制下党内关系的丰富和完善。
2.斯大林时期:“官僚集权制”的党内关系。斯大林逐步破坏列宁所奠定的苏共党内关系原则,过分强调集中制。一是破坏列宁创立的党代表大会制度,党代会和中央委员会召开的日期间隔不断延长,党的权力集中在政治局和书记处手里,党内权力关系发生完全的倒置。二是破坏党的选举制,用事实上存在的任命制取代党内民主选举,其结果是党内关系围绕权力和官位而展开,党内正常的干部流动渠道被封堵,仅给那些溜须拍马、投机钻营的投机分子提供了往上爬的梯子。三是改变列宁晚年精心设计的党内监督关系,党的监督机构由对同级权力机构的监督变成代表同级机构监督下级机构的工作,党内监督关系变成了党内监控关系。四是不能正确对待党内的斗争。党内关系是动态的,党内矛盾的存在推动党内关系的发展,用正确的党内斗争方式处理党内关系是列宁一贯坚持的原则,但斯大林在对待党内不同意见者时,起初还能用民主方式予以处理,到30年代以后,则更多的用肃反手段予以肉体消除,“党的十七大选出的139名正式和候补委员中,被杀的达70%。”[5]183这样一来,苏共党内关系就僵化为“官僚集权制”了。
3.后斯大林时代:“权贵中心制”的党内关系。斯大林时期由于不间断的党内清洗以及革命战争年代党内新陈代谢速度较快,苏共党内关系虽然僵化但并未固化。赫鲁晓夫上台后,已经意识到了这个问题,为此他推行干部更换制度,“由选举产生的各级机关的经常更新,今后应该成为不可违犯的党内生活准则”。[6]402赫鲁晓夫的改革,抓住了苏共党内关系的症结,却开错了药方,反而造成党内干部的不稳定。勃列日涅夫时期,苏联党内关系彻底蜕变,在干部问题上,强化委任制,任用的干部多是勃列日涅夫的亲信,被称为“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帮”。党的领导阶层高度自我封闭,往往是连选连任,终身制。这样的一种干部政策,与党内干部特权制度紧密结合,恶性膨胀,导致苏共党内形成了一个特殊的权贵阶层,凌驾于全党之上,党内关系不是建立在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基础上,而是建立在对特权的把持和利益的相互交换基础之上,为了维护既得利益,他们阻挠党内任何涉及自身特权的改革。当权力成为一种乐趣,当党内关系主体间变成一种围绕私人利益而展开的关系时,其党内关系也就蜕变成“权贵中心制”了。
4.戈尔巴乔夫时代:“放任自由式”的党内关系。戈尔巴乔夫意识到苏共存在的各种问题并开出了药方,即公开性和民主化,但它不但没能解决苏共数十年积累下来的党内关系的顽疾,反而加速了其紊乱。这一时期围绕改革不同的观点,苏共党内出现三大派别,即以利加乔夫为首的传统派、以叶利钦为首的极右派“民主纲领派”和以戈尔巴乔夫为首的主流派。由于戈尔巴乔夫抛弃民主集中制,妄图在党内建立“放任自由式”的党内关系,各个派别在党内大搞横向联系,使得党的团结变得脆弱不堪,极右派在党内关系问题上,公然鼓吹抛弃马克思主义的共同理想,要求放弃民主集中制,废除《关于党的统一的决议》。苏共二十八大上各派别“提出30个纲领,50个党章草案”,[5]210苏共的下属党组织、各加盟共和国党组织也开始分裂,一时间苏共党内派别林立,整个党已经成为一个政治俱乐部,丧失了领导能力和战斗力,面对非党化、解散、禁止活动的命令,完全无力回击,历经93年寿终正寝。
二、苏共党内关系演变的主要特点及其后果
1.上下级关系的演变使得党内关系由精诚团结异化为各怀异志。党内关系中,党的上下级关系具有首要地位,上下级关系顺畅,党的意志就能很好地贯彻;上下级关系不畅,党的意志可能就会发生执行中的扭曲。十月革命前,由于苏共还处在夺权状态,党内上下级关系强调绝对服从,“集中制要求中央和党的最遥远、最偏僻的部分之间没有任何壁障……我们的中央有直接掌握每一个党员的绝对权力。”[7]249应当指出的是,这种绝对服从和任命制的做法并不是列宁的初衷,一旦条件允许,列宁就着手对其调整。俄共十大规定:党委会不仅要向上级组织,而且要向下级组织报告工作。上级党的机关只有在下级组织公然违反党代表大会的决议以及根据代表大会决议进一步做出的指示或指令时,才能解散下级组织等等。[4]49-63遗憾的是,由于列宁的早逝,他关于党内关系的思想没能来得及贯彻。斯大林继承了列宁时期遗留下来的党内上下级关系的既有模式并加以强化,后果是在苏共党内制造了一种不唯实、只唯上的上下级关系,民主集中制的下级组织对上级组织的服从畸形为下级对上级个别领导人的绝对服从、人身依附,党内上下级关系演化为金字塔式的权力控制关系。赫鲁晓夫时期尽管在干部问题上曾经进行改革,但并未触动委任制。勃列日涅夫为了稳定干部,任命制之后又强化了终身制,党内上下级之间充满神秘色彩,下级对于上级的决策往往无从知道。戈尔巴乔夫推行改革之后,在上下级关系方面大动手术,推行各级党组织的“自治原则”。下级党组织的决议,“只要不违背党的纲领性目标”,“上级机构不得予以撤销”。同时还规定,“各加盟共和国共产党是独立的”。各加盟共和国共产党如果不同意苏共中央政治局的决议,“有权不执行这一决议”。[5]194这样一来,地方组织自行其是,与中央分庭抗礼,分裂不可避免。
2.干群关系的演变使得党内关系由风雨同舟异化为离心离德。健康的党内干群关系,要求党内的领导干部和各级组织必须密切联系党内的基层党员,倾听他们的呼声,保障他们的权益,只有这样,广大党员才能树立党内的主人翁意识。为此列宁提出要经常广泛地召开党员大会,创办报刊《争论专页》,开展党内批评等,来保障党员权利。他还注重生活方面的干群一致,反对党的干部待遇与普通党员差距太大。对有人私自提高列宁工资的行为,列宁斥责这是“公然违法行为”,对当事人给予“严重警告的处分”。[8]184列宁曾设立“疗养食堂”,让干部们吃饱肚子更好地工作,但斯大林把这种对干部的特供制度异化了,党内干部的职务越高,享受的特供待遇就越多,“你在职位的阶梯上爬得越高,归你享受的东西就越丰富。……如果你爬到了党的权力金字塔的顶尖,则可享有一切。”[9]129特权制度导致买官卖官、腐败成风,“在1969年,阿塞拜疆一个区委第一书记就‘价值’20万卢布,第二书记是10万卢布。”[10]戈尔巴乔夫时期,党内部分高层凭借改革之机,谋求暴利,甚至成为俄罗斯新的金融寡头。面对高层的腐败堕落,基层党员却被剥夺了批判的权利,党内只有歌功颂德,苏共一个地区党委会的记录记载,“1974年至1975年间召开了72次会议,共有600多人发言,只有12人对党的领导人提出了意见,其他人几乎都是空话、套话、赞美的话。”[10]而在党内说真话的人却反遭迫害,“一位铁路工程师认为勃列日涅夫在代表大会上的工作报告缺乏足够的批评精神,过分地赞美和颂扬他的功绩就是个人崇拜。此后,这个人就被开除了党籍。”[10]这样的党内干群关系,必然造成党内干群对立,党员对党的冷漠和不信任。
3.对待党内派别态度的演变使得党内关系由和衷共济异化为分庭抗礼。党内派别,一般指党内出现的有独立的纲领、固定的组织的小集团。无产阶级政党,并不否定党内会有不同的声音,发生争论也是正常的,但决不允许搞无原则的派别纷争。列宁向来是与党内派别做坚决斗争的,主张“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实行无条件的集中和极严格的纪律,是战胜资产阶级的基本条件之一”,[8]245十月革命后,面对党内又一次出现的各个派别,列宁又一次强调了党的团结的重要性,“任何派别活动都是有害的,都是不能允许的。”[8]295但是,对于党内派别,他并不是简单地予以清除,而是主要通过耐心的说服教育,组织手段只是作为最后的保障措施。但是列宁之后,斯大林在面对党内反对派的挑战时,其手段就较之列宁有根本改变,他认为,党内的派别活动必然“瓦解党的队伍,把党分裂为各个中心,削弱党,削弱无产阶级专政”,[11]103-104所以,对于党内派别组织,如托季联盟、布哈林集团,都动用组织手段粗暴解决,甚至驱逐出境,肉体消除,开了一个无产阶级政党处理党内派别关系的很坏的例子,使得党内斗争简单化、残酷化。戈尔巴乔夫一反苏共一贯做法,在对待党内派别组织方面,苏共二十八大通过的党章规定,党内“不允许建立具有自己内部纪律的派别,但并不限制共产党员在辩论过程中按纲领进行联合的权利”,党内可以“成立党组织书记委员会、党的俱乐部、理论研讨会、辩论中心、老党员委员会和按志趣和问题成立其他形式的党员联合组织”,[12]并且这些组织的活动不受限制。一时间苏共派别林立,并且党内有派,党外有党,内外勾结,共同搞垮了苏共。
4.监督关系的演变使得党内关系由民主监督异化为上下监控。党内监督关系,在于党内权力运行受到党内力量的约束,否则权力必然发生异化,恶性膨胀,最终危及党内关系。俄共第九次全国代表会议决议指出:“有必要成立一个同中央委员会平行的监察委员会。”[4]43-44俄共十大、十一大先后通过《关于监察委员会的决议》和《监察委员会条例》,确立了党内监督关系,其特点有三:一是监督者与被监督者地位平等,党的监察委员会由同级党的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二是监督者与被监督者职务分离,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不得兼任中央委员和行政职务,但有权参加同级党组织的各种会议,享有发言权。三是监督者与被监督者权力独立,监察委员会的决定,同级党的委员会必须执行而不得加以撤销,分歧可以通过双方联席会议解决,达不成一致,还可提交党的代表大会或上级监委会解决。这样,苏共党内形成了权力的执行者与监督者并行不悖的关系,有力地防止了党内的集权和官僚主义。斯大林掌权后改变了这种监督关系,矮化监督机构的地位,“监察委员会由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选举,并在联共(布)中央委员会领导下进行工作”;[13]54缩小中央监委的职权,监督党和联共(布)中央委员会的决议的执行、审理违反党纪的人、审理违反党的道德的人,[14]402对同级党委的监督权丧失;加强对监委会的控制,“委派一名联共(布)中央委员会书记为党监察委员会的领导者”。[14]393监督机构沦为党的权力机构的附属和监控机构,党内权力不再受到约束,党员权利也得不到保障。赫鲁晓夫和勃列日涅夫都进行过小修小补式的改革,但没有改变党内监督主体与客体地位不平等的关系。戈尔巴乔夫改革党内监督关系,包括中央监察委员会与中央委员会地位平等,可以监督中央的工作等,企图恢复到列宁时代的做法,但由于其改革的根本指导思想是错误的,苏共党内监督关系不可能恢复到理想状态,更挽救不了党的灭亡。
三、苏共党内关系演变与苏共衰亡的启示
1.处理党内关系必须坚持民主集中制。制度问题是带有根本性的问题,对于无产阶级党内关系而言最根本的制度就是民主集中制。列宁在党内关系问题上最大的理论贡献就是确立了民主集中制的党内关系原则,但是斯大林错误地理解民主集中制,使得苏共党内关系长期只有集中,没有民主,并且恶化为集中口号下的集权和个人专断,使得党内关系长期被压抑,丧失生机和活力。而这种高度集中制下党内关系恶化的后果,是把苏共党内关系一系列的问题归罪于民主集中制。戈尔巴乔夫宣传“党内有一股主张把这条原则从党章中删掉的强烈情绪,因为过去的全部实践已使这条原则声名狼藉”,[10]苏共二十八大上取消了民主集中制作为党的基本组织原则的条文。民主集中制是无产阶级政党根本的组织原则,也是构建党内关系的指导性原则。新形势下,我们应该根据列宁对民主集中制的经验总结和设想,探索进一步丰富和完善这一制度、促进党内关系更好发展的路子。必须坚决反对抽象的民主,反对照搬西方民主价值观念和模式,自觉划清无产阶级民主同西方资本主义民主的界限;反对打着民主旗号,削弱党的集中统一和领导作用,把党变成政治俱乐部和清谈馆的企图。同时要大胆谨慎地在党内探索一些民主改革的措施,包括党代表的提名选举方式、党代会常任制、党组织领导班子直选、党的各级委员会工作报告制等等。要进一步保障党员的民主权利,畅通他们对党的工作提出意见和批评的渠道。要完善党的集体领导制度,既做到一元化领导,又防止个人专断。维护党的权威和政令畅通,杜绝阳奉阴违、地方保护主义的行为,在党内真正营造“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构建和谐一致的党内关系,以党内和谐推动社会和谐。
2.处理党内关系必须维护党内团结。党内关系的正常离不开党内团结,维系党内团结的纽带是共同的政治信仰,如果信仰丧失,或者信仰多元,这个政党就必然四分五裂。戈尔巴乔夫推动新思维和公开性,放弃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最终使得苏共党员面对风起云涌的各种意识形态无所适从,党也在各种纲领的指导下分崩离析。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带领全体党员团结一致夺取革命、建设和改革胜利,离不开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的高度认同。新时期,党内团结要更为自觉和紧密,就必须让全党思想统一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最新理论成果上来,让科学发展观成为全党共同奋斗的精神动力。维系党内关系的团结,还必须正确开展党内斗争。党内斗争的根源是“社会阶级矛盾和新旧事物的矛盾在党内的反映。党内如果没有矛盾和解决矛盾的思想斗争,党的生命也就停止了”。[15]306对待党内矛盾、开展党内斗争有个方法问题,列宁对待党内不同意见,往往能用说理的办法解决,组织手段只是不得已而为之。斯大林却推行一条靠残酷的大清洗手段来解决党内斗争的错误路线。对于党内存在的矛盾,要分类看待,正确区分原则问题与具体工作上的矛盾;要民主对待,坚决反对一言堂,粗暴压制;要坚持原则,既反对无原则的一团和气,也反对散播小道消息,制造党内混乱。特别是市场经济条件下,党内矛盾更多的体现为利益关系,要正确开展党内斗争,就必须构建党内利益协调机制。党内利益关系如果不能正确协调一致,必然导致形成党内利益集团,成为改革的阻力。
3.处理党内关系必须坚持以人为本。在党内关系中,党员个人是重要主体之一。列宁一贯重视保障党员权利,“组成党的专门委员会,受理有关的控诉。任何控诉,即使是由少数党员署名的控诉,也都应当由上述委员会给以详尽的回答,或由省委员会予以批示。”[4]44斯大林上台后,经济上建立计划经济体制,计划经济是一种条块分割、自我封闭、缺少竞争的经济,因此必然要求在执政党内建立一种与之适应的严格的、固化的机制来确保行政手段的有效性、权威性,但这也就为党内关系演化为个人集权制和轻视个体权益埋下伏笔。马克思在谈到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时写道:“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16]294实际蕴含了个体发展对于整体发展的重要性,党内关系无疑也应该遵循这一价值准则。忽视党员个体利益,党内缺乏公平正义,会使得党员对政党的认同度降低,离心力增强。新时期发展党内关系,必须重视人的作用和价值,把注重人的个性与强调党的共性结合起来,既要继续保持全党高度统一,又要通过建立健全党内激励、关怀、帮扶机制,让每个党员、每个地方党组织能够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真正做到以人为本,只有这样,才能增强党员自身的主动性,增强党内的生机和活力,激发党员参与党内事务、关心党的事业的热情,避免目前在一些基层党组织和普通党员中间出现的政治冷漠。党内关系和谐一致,才能够迸发出无穷的活力,提升党驾驭市场经济、促进科学发展的能力。
[1]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2]列宁全集(第1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
[3]苏共决议汇编(第1分册)[G].北京:人民出版社,1964.
[4]苏共决议汇编(第2分册)[G].北京:人民出版社,1964.
[5]苏共的失败及教训[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4.
[6]苏联共产党第22次代表大会主要文件[G].北京:人民出版社,1961.
[7]列宁全集(第8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
[8]列宁专题文集·论无产阶级政党[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9][俄]鲍利斯·叶利钦.我的自述[M].北京:东方出版社,1993.
[10]李慎明.居安思危——苏共亡党的历史教训8集DVD教育参考片解说词(续)[J].俄罗斯中亚东欧研究,2007,(3).
[11]斯大林全集(第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
[12]牛安生.苏共党内的派别化及其教训[J].俄罗斯中亚东欧研究,1993,(6).
[13]苏共决议汇编(第5分册)[G].北京:人民出版社,1964.
[14]苏共决议汇编(第4分册)[G].北京:人民出版社,1964.
[15]毛泽东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1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