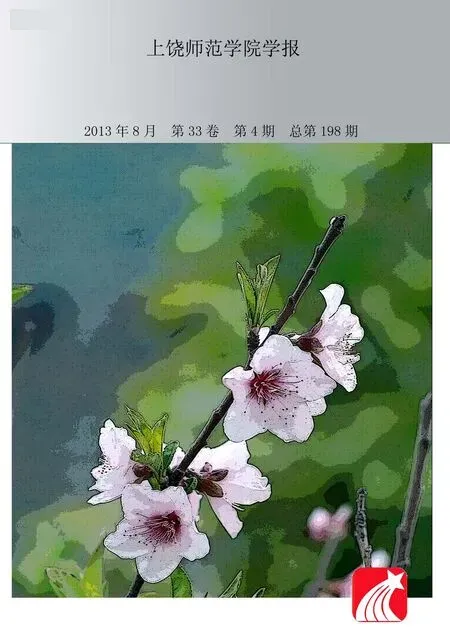论“意象”的“形而上质”
——从意象与易象的关系说起
(湖南师范大学 文学院,湖南长沙410006)
在中国古代文学理论中,意象是一个十分重要的范畴,它是“意”和“象”两者融合而成的艺术形象。意象作为一个术语,在西方文论中也十分常见,并在心理学、美学等诸多学科中有着不同的内涵,韦勒克和沃伦著的《文学理论》中就说到“意象是一个既属于心理学,又属于文学研究的题目。在心理学中,‘意象’一词表示有关过去的感受上、知觉上的经验在心中的重现或回忆,而这种重现或回忆未必一定是视觉上的”,并且谈及意象派诗人庞德对意象的界定:“‘意象’不是一种图像式的重现,而是‘一种在瞬间呈现的理智与感情的复杂经验’,是一种‘各种根本不同观念的联合’”[1] (P212)。关于意象概念的含义在中国当代学界有不同认识,叶朗认为“意象就是形象和情趣的契合,意象是一个标示艺术本体的美学范畴”[2](P265),童庆炳主编的《文学理论教程》则认为“审美意象是指以表达哲理为目的,以象征性或荒诞性为其基本特征的达到人类审美理想境界的表意之象”[3](P204)。虽然没有完全统一的看法,但是从这些观点中可以看出一些共同之处:意象是外界的“景”、“物”与作者的“情”、“意”融合而成的艺术形象。但是这种“意象”观念主要来自西方,用来诠释中国古代文论中的“意象”范畴并不恰当。正如许多学者所指出的,中国古代的“意象”范畴来自“易象”。譬如王运熙主编的《中国文学批评通史》认为“‘意象’、‘象物’等范畴,当来源于《易传》”[4](P93)。叶朗也认为这个范畴的形成“最早就是发源于《易传》的‘立象以尽意’这一命题”[2](P73)。吴廷玉则更进一步认为“易象具有象征性、示意性,原是悬挂起来以示于人的。伏羲画卦‘立象以尽意’,解卦者便可‘寻象以观意’。因此可以说易象也是一种意象”[5](P76)。熟悉《周易》的人们都知道,“易象”并不是指一般的物象或意象,中国古代文论的“意象”范畴也相应地具有一些非常独特的性质。因此,尽管“意象”范畴几乎已是老生常谈,却颇有进一步探讨的必要。
一、“易象”释义
“象”在《说文解字》中释为:“象,南越大兽,长鼻牙,三年一乳,象耳牙四足之形”,可见最早“象”的指称是作为动物的大象出现的,这是现实存在物的特指。后来“象”的涵义运用更为广泛,它超越了动物之象这种特指,进而可以指任何一种事物之象,这种“象”不是某一种具体之物的形貌,它具有一种形而上的特点,所以它与“形”有所区别,可以说是“有象而无形”。老子《道德经》中“道之为物,惟恍惟惚。惚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惚兮,其中有物”[6](P148)、“大音希声,大象无形”[6](P228),这里的 “物”、“形”是同一层面的,就是指具体的物象;“惚兮恍兮”是指道的表现形式,“象”是表现这种“道”的一种存在方式,所以它是与老子的“道”相联系的。老子这里的“大象无形”是一种哲学上的思辨,说明“道”是有象而无形的,或者说,“象”先于“形”,象无定形,所以它也才“无名”。这种“形”与“象”之区别还可以通过《易经·系辞》中“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7](P563)这句话来理解,“象”是形而上的、抽象的,是“道”的显现。
《易传·系辞》多次谈到了“象”这一范畴,它的开篇就说到“象”的形成过程与特点:
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陈,贵贱位矣。动静有常,刚柔断矣。方以类聚,物以群分,吉凶生矣。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变化见矣。[7] (P527)
“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变化见矣”,这里“象”与“形”也是两个不同的范畴,韩康伯注曰:“象,况日月星辰;形,况山川草木也。”[7](P529)“天象”和“地形”是相对的,天象是“天道”之“象”,是神秘莫测、变化不定的,“地形”是一些具体之物,是有定形的。韩康伯分别用“日月星辰”和“山川草木”来指实,实际上未必准确。“象”超越具体有形的物体,是有象而无形的,所以“象”是能变化者。“形”可以观,而对于“象”的把握,不仅要“观”,还应“想”和“悟”,就如庄子谈把握“道”的方式:“无听之以耳而听之以心,无听之以心而听之以气!耳止于听,心止于符。气也者,虚而待物者也。唯道集虚。虚者,心斋也”[8](P129),即“道”是用空虚的心境去体悟的。“在天成象”这种“象”与“道”相联系,正如陈良运所说:“‘道’是不可名状的,是超越人们感性经验的,但它又不是彻底的虚无,它是存在于冥冥中的一种自然规律性,人们可以凭自己的内视、内听去感觉它,感觉到无具体形状、无特地物象的‘恍惚’之‘象’”[9](P164)。这说明“道”本身是看不见、摸不着的,它没有具体的形象,但又不是“彻底的虚无”,人们通过“内视”、“内听”可以感觉到它的存在。“道”这种神秘性特征与易象的特征有着密切的关系,易象之“象”是体现“道”的一种方式, 所以易象也随之具有一种神秘性特征。“道”的这种神秘性源于它的“创生性”,老子认为“道”在天地产生之前就已存在,“道”能够产生万物,“道冲,而用之或不盈。渊兮,似万物之宗”[6](P75)、“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6](P232)及“道生之,德畜之,物形之,势成之”[6](P261)就都是讲“道”是万物之宗,它能创生万物。受“道”这种特征的影响,易象也具有很强的生发性,一方面它包罗万物,可以生发出万物,如《易传·系辞》曰“《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业”[7](P556);另一方面它又是变化多端的,而非某一固定之象,比如《说卦传》例举了乾卦的多种取象:“乾为天,为圆,为君,为父,为玉,为金,为寒,为冰,为大赤,为良马,为老马,为瘠马,为驳马,为木果”[7](P631)。
《易传·系辞》对“象”这个范畴还作了一个重要规定,提出了“立象以尽意”的命题:
子曰:“书不尽言,言不尽意。”然则圣人之意,其不可见乎?子曰:“圣人立象以尽意,设卦以尽情伪,系辞焉以尽其言,变而通之以尽利,鼓之舞之以尽神”。[7](P563)
“言不尽意”是指语言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不能完整地表达“圣人之意”。此不能用名言来完全表达的“圣人之意”实即圣人所领悟的“道”。《易传》认为“立象以尽意”,即“象”可以更直观地表达语言所不能及的“圣人之意”。孔颖达在《周易正义》说“凡易者象也,以物象而明人事者,若诗之比喻也”[10](P27),而“立象以尽意”正可体现这种比喻,高亨在《周易杂论》一书中谈《周易》的艺术特点时也提及了其取象的这种特点:
它的比喻和一般比喻有所不同,一般比喻有特定的被比喻的主体事物,而且多数是与取作比喻的客体事物同时出现在文中;而《周易》的比喻没有特定的被比喻的主体事物,当然不出现于文中,仅仅描述做比喻的客体事物,因此,可以应用在许多人事方面。这实有类似于象征。[11](P60)
高亨认为这种比喻类似于象征,也就是说易象具有一种象征性特征。《周易》两个最基本的符号“- -”和“—”就是一种象征,学术界对其象征说法较多,或认为天地的象征,或认为男女生殖器的象征,或认为奇偶的象征等等,总之,阴阳爻象象征着较为广泛的相互对立的种种事物、现象。在阴阳二爻的基础上以每三爻叠成一卦而形成的八卦也是如此,乾、坤、坎、离、震、艮、巽、兑这八卦分别象征 天、地、水、火、雷、山、风、泽八种具体事物。六十四卦的哲理也是通过象征表现出来的,六十四卦中每一卦都由六爻组成,从下到上分别为初、二、三、四、五、上,这六个等级分别象征事物发展过程中由低级向高级渐进的次序。六十四卦的卦形也各有其象征意义,比如《既济》卦火在下、水在上,就如煮熟食物,所以它象征万事的成功。可见易象就是象征的易象,可以说《周易》一书是以象征的方式言说的。
这种象征的易象与“道”相联系,也具有形上性的特征。刘若愚在《中国文学理论》中认为:“在‘形上’的标题下,可以包括以文学为宇宙原理之显现这种概念为基础的各种理论”,“在形上理论中,宇宙原理通常称为‘道'”[12](P20)。宇宙原理仅是“道”的涵义的一部分,《周易》一书多次提到了形而上的“道”,《易传·系辞》曰:
《易》与天地准,故能弥纶天地之道。仰以观于天文,俯以察于地理,是故知幽明之故;原始反终,故知死生之说;精气为物,游魂为变,是故知鬼神之情状。与天地相似,故不违;知周乎万物而道济天下,故不过。[7](P535)
此言《周易》所讲之道与天地齐等,能尽涵天地之道。仰观俯察是易象形成过程中的取象过程,易象是显现“道”的一种方式,通过易象来把握形而上的“道”之后才能知“幽明之故”、“死生之说”及“鬼神之情状”,易象既与“天地相似”,又能“知周乎万物”,故“不违”也“不过”,易象也随着“道”具有形上性的特征。八卦的取象过程也体现了这种形上性特征:
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7](P572)
易象的建立,不仅需要“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更要“精义入神”,“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也就是说,“易象”的建立需要极高的智慧,需要深入而准确地领会天地人三才之道。圣人能够深入而准确地领会形而上的道,所以从来都把易象的建立归功于圣人(包牺氏)。而圣人对于“道”的领会可以通过多种方式,其中就包括文学艺术的方式。
虽说易象与“道”相联系,是体现“道”的一种“象”,它具有神秘性、形上性等较为模糊抽象的一面,但它也有可观的一面,即直观性。易象的产生过程就表明了这种直观性,《易传·系辞》曰“圣人有以见天下之赜,而拟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谓之象”[7](P544),圣人有见于天下万物之幽隐繁杂,于是综合考虑其各种表现而建立最能体现事物变化趋势的易象,这里的易象就具有一种直观性。“观物取象”中“观”是取象的基本方式,它的思维起点是种种具体的物象,然后根据这些物象的内在精神建立一种既具普遍性又有直观性的易象,即所谓“立象以尽 意”。比如乾卦的形成,就是反复观察天象,领悟到其健行不息的特点后,便用纯阳卦象来表示,而所谓“龙”“君”“男”等,不过是用诸多具有某种共同特性的有形之物从多方面来表示此一无形之“象”。易象的直观性还体现在卦形上,八卦中坎卦的卦形为上下阴爻、中间阳爻,这个卦形非常像古文字的“水”字,从其卦形就可以直观的看出它象征水这种事物。泰卦的卦形坤在上、乾在下,表示阴气下降、阳气上升,两气相交所以通泰,也非常直观。
综上可知,《周易》的“象”即易象和某种简单的物象全然不同,一方面它是“道”的存在方式,具有神秘性、象征性、形上性等特征,另一方面又是人们把握“道”的方式,具有直观性特征。
二、意象与易象的关系
易象之“象”是象征性的形象,它既具有形上性、神秘性又具有直观性。意象涵义是“意”与“象”两者的结合,这里的“象”是一种象征性的形象,是直观的;“意”是作者之意,它蕴含着作者的某些感悟,是较为模糊、抽象、幽隐的。由这些特征看来,意象与易象是不是存在着某种特殊的联系?正如大部分学者所认为,易象是意象范畴之源。笔者将从意象范畴的形成过程及其特征这两方面来讨论它与易象之间的关系。
首先,从意象范畴的形成过程来看,《易传》中“观物取象”、“立象以尽意”的思想对意象的形成及展开产生了重要影响。“观物取象”讲的是易象的产生过程,“观”是对外界物象的直接观察、直接感受,这是一个认识的过程。“观”的方式既要仰观天象,又要俯察地法,既观之于远,又观之于近,这样才能把握天地之道,万物之情。“取”是在“观”的基础上的提炼、概括,这是一个创造的过程。可见“易象”的产生既是一个认识过程,又是一个创造过程,这与意象形成过程中的思维是一致的,作者先是因具体情境产生了对于世界和人生的某种感悟,此种感悟与其目触心感的种种实象与想像融为一体而不可分离,以致最初总是无法用语言来准确传达,几经深入琢磨与推敲之后,最后才选取自认为最为相宜的语言从多方面来描摹此种情境和由此生发的内心感悟,这也是一个创造的过程。它们在取象过程中都发挥了联想和想象的思维,并且两者所取的象都是为了表达某种“意”的象:易象这种“观物取象”的方式所取的“象”是“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包含着超越“形”之上的“神”、“德”、“情”等内涵,归根结底也就是与道的特征相关,这就是《易传》作者所要表达的“意”;意象之“意”则是作者在具体情境下的深刻感悟。
《易传》所提出的“立象以尽意”进一步用“意”字来统括《易传》作者所要表达的思想,并明确地把“意”与“象”联系起来,认为“象”对于表达“意” 有“言”所不能及的功能,进一步把形象和思想、情感联系起来,这对“意”、“象”两个范畴组合成“意象”这个范畴有很大的启发作用。这里的“象”是为了表达“意”, 不自觉地蕴含了“象”与“意”融合为一的思想,为意象范畴最终自觉地形成奠定了基础。
“意”与“象”连接成一个词,最早见于汉代王充的《论衡·乱龙》:
天子射熊,诸侯射麋,卿大夫射虎豹,士射鹿豕,示服猛也。名布为侯,示射无道诸侯也。夫画布为熊、糜之象,名布为或,礼贵意象,示义取名也。土龙亦夫熊糜、布侯之类。[13](P923)
这里将君臣上下礼仪之“意”,闸于兽象之中,这些“象”是画有熊、糜、虎、豹、鹿、豕之象的画像。意象在这里组合成一个范畴来使用,“麋鹿之象”就是一种表意的象征物象,这种“意象”的象征性特征与“易象”的象征性特征是一脉相承的。虽然这还不是审美中的“意象”范畴,但是这个“象”表达了人的某种意念和思想,是“意”与“象”的统一,也有一定程度上的审美意义,可见这个“意象”的涵义已经比较接近古代文艺理论中“意象”范畴的涵义。
南北朝时,刘勰在《文心雕龙·神思》中最早赋予“意象”以文学艺术及其审美内涵:
是以陶钧文思,贵在虚静,疏瀹五藏,澡雪精神,积学以储宝,酌理以富才,研阅以穷照,驯致以怿辞,然后使玄解之宰,寻声律而定墨;独照之匠,窥意象而运斤,此盖驭文之首术,谋篇之大端。[14](P493)
这里明确说“窥意象而运斤”的必是“独照之匠”,后者典出庄子所谓庖丁解牛、轮扁斫轮、匠石削垩诸故事,同时也来自“淮南子亻叔真篇:‘视于冥冥,听于无声,冥冥之中,独见晓焉,寂漠之中,独有照焉’”[15](P374),“独照之匠”和“玄解之宰”不是一般的作者,他们是“积学以储宝,酌理以富才,研阅以穷照,驯致以怿辞”,也就是在学、理、才、识等方面造诣极高的基础上,能像“观物取象”的圣人一样深入地领会文学艺术创作之“道”的奥秘。这种领会还需要特殊的心境,即“贵在虚静,疏瀹五藏,澡雪精神”,因为这不是一般的思考、感悟,而是一种“神思”,是对于形上之道的直觉与领悟,这种艺术思维被刘勰誉为“驭文之首术,谋篇之大端”。总之,“独照之匠”与“玄解之宰”一样,都是指“技进于道”者,即对于“道”有深刻体验与感悟者。这就既说明“意象”中包含了某种与“道”相关相近的内容,也说明恰像惟有圣人才能“观物取象”一样,也只有“独照之匠”和“玄解之宰”才能真正“窥意象”和“寻声律”并以恰当的语言、恰当的声律和恰当的结构与次序来表现。可见文学创作的“神思”实是一种见道之思、“精义入神”之思,文学艺术的情感与思维中也包含了对于形上之道的直觉与领悟。
其次,从意象范畴的特征来看,易象对其也产生了重要影响。我们可以通过意象与易象两者的特征的关联性来进一步探讨它们之间的关系。易象不同于物象,它与物象有层次之别。前者有形上性、直观性等特点,后者则是可以指实的、现存的具体对象。这就决定了用来表示“易象”的具体形象总是具有象征性。象征也是意象的一个重要特征,意象本身就是一些具有象征性特征的物象,在中国传统文学(尤其是诗词)中,文人通常通过一些意象来表达自己的情感,比如用“梅”这个意象象征高洁、孤傲的品格,用“竹”这个意象象征宁折不弯的精神,用“柳”象征离别时依依不舍的留别之情。“象征性意象的审美效应不发生在这些形象的本身,形象只起一种中介的作用,或干脆说被当成一种中介物,诗人情感的对应物,审美效应发生在形象之外”[9](P202),作者的情感是一种较为幽隐的东西,作者通过意象是为了传达这种模糊幽隐的情感,所以最终的目的是借助意象体悟到作者内心深处的情感,审美效应也就发生在形象之外。王弼在《周易略例·明象》所言“象者所以有意,得意而忘象”[16](P285),就是指借助“象”而去体会作者的“意”,意象与易象两者的象都是为了传达意,可见意象取象的象征就是对易象象征性特征的继承与发展。
陈良运在《中国诗学体系》一书谈到意象说的嬗变与发展,认为意象发展是由“象征性意象向情感性意象的转变”[9](P199),他把意象分为象征性意象和情感性意象,笔者认为意象是象征性与情感性的融合,但从他的这个分类可以说明情感性特征是意象的另一重要特征。不过一般讲情感常常等同于感情,即只侧重于“情”而不甚注意“感”,笔者则更愿意将作家的“情感”理解为有情之感,即对世界和人生的一种含着浓情的深刻感悟。据说马致远所作的《天净沙·秋思》中 “枯藤”、“老树”、“昏鸦”、“古道”、“瘦马”这些悲凉意象的形成,是作者长期漂泊在外而饱含着一种思念家乡的孤寂而悲凉之情,然后看到了“藤”、“树”、“鸦”、“道”、“马”这些物象,与其内心孤苦的情感相融合,通过这些形象直观的物象寄托了作者对人生、命运的深刻感悟。情感是作者对世界、人生含有浓情的感悟,这种感悟在文艺构思过程中也包含了对形上之道的直觉与领悟,从这一层面来说,作者的情感是较为模糊的、幽隐的、不确定的,甚至有时作者内心情感是错综交杂、百感交集,所以作者所取的象所指涉的意义显得迷离恍惚,呈现出多层次、多向性,例如李商隐的《锦瑟》一诗中“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经过许多评论家的揣摩,对作者所要传达的“此情”及“锦瑟”的象征意义至今仍是众说纷纭。对这些意象所象征的情感捉摸不透,正是与作者对人生、命运含着浓情的深刻感悟有关。上文所述文学艺术的情感与思维中包含了对于形上之道的直觉与领悟,这其实就是作者通过文学艺术这种方式来领会“道”。而读者只能通过直观的意象来体悟作者对世界、人生的感悟,这些意象所能传达出作者的感悟必然是有限的,所以读者对意象所指涉的意义的把握也相应地具有一种有限性与模糊性。
意象与易象的形成过程中的思维也是一致的,它们都是在取象过程中运用了想象与联想的思维来选取适宜的物象,并且都不是用概念和逻辑来表现作者的情感,而是通过具体的物象来表达。从它们的特征来看,两者都具有象征性、形上性等特征,这些象征性物象一方面是直观的,是为了表达作者心灵深处较为幽隐的“意”,也正因为与作者较为隐秘的“意”相关,读者对这些象的指涉意义的把握也因此具有模糊性的一面。综上可知,易象是意象范畴之源。
三、“意象”的涵义

正因为意象与道相联系,具有形而上的特性,所以历代学者对意象的把握也蕴含了神秘性。王昌龄《诗格》言及意象,认为它不是通过“久用精思”而能契合的,而是“神会于物,因心而得”。对“意象”的把握如同对“易象”的体认,有其神秘性。司空图在《诗品·缜密》中说:“是有真迹,如不可知,意象欲出,造化已奇。水流花开,清露未日希,要路愈远,幽行为迟。语不欲犯,思不欲痴,犹春于绿,明月雪时。”[17](P205)他又在《与极浦书》提出“象外之象,景外之景,岂容易可谈哉”[17](P201)。这表明,司空图也认为“意象”是神秘的,具有不可言说性。当我们明了“意象”与道之间的联系时,就比较容易理解这种神秘性的缘起了。何景明《与李空同论诗书》谈到“意象”,认为意与象应对应切合:“夫意象应曰合,意象乖曰离,是故乾坤之卦,体天地之撰,意象尽矣”[18](P37)。乾坤两卦是体现天地阴阳等自然现象变化规律的,这种规律也与道相关,把握了这种道才可以达到“意象尽矣”。王廷相在《与郭价夫学士论诗书》中说:“夫诗贵意象透莹,不喜事实粘著。古谓水中之月,镜中之影,可以目睹,难以实求是也。……故示以意象,使人思而咀之,感而契之,邈哉深矣。此诗之大致也”[19](P344-345)。 他认为意象“可以目睹,难以实求”,它是一种虚实相生、“不可言传,只可意会”的神秘之物。
这种与“道”相应的意象,在作者便是“形上之思”,是作者对于宇宙、人生、命运的思考,但这种思考并非是以逻辑思辨的形式而是以形象直观的形式展开的。陈良运认为“诗歌创作中自觉地运用象征性意象是从屈原始”[9](P200),其实在《诗经》中早就出现了不少象征性意象,而屈原之所以被认为是第一个运用象征性意象的诗人,就是因为楚辞中不仅饱含着作者对宇宙、人生、命运的思考,同时这些思考还是通过形象直观的方式完成的。在屈原那里,意象所具有的象征性,是和它的神话性与神秘性分不开的,也就是说,是和早期先民对世界的直观感受分不开的。
关于意象与“道”的关系,还可以从作品的存在方式角度来理解。韦勒克和沃伦在《文学理论》中提到英伽登的批评理论时说,“英伽登还提出了‘形而上质’的层面(崇高的、悲剧的、可怕的、神圣的),通过这一层面艺术可以引人深思。”[1](P169)这个“形而上质”的东西,实际指向的就是作品中所包孕的“哲学意义”。但这种“哲学意义”并不是直接地呈现的,而是潜含在意象之中,通过意象之间的关联和组接传达出来。就如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这首诗展示了较之此前诗歌“更迥绝的宇宙意识!一个更深沉,更寥廓,更宁静的境界!”[20](P20)但这种展示,恰是通过春、江、花、月、夜诸意象及其关联与组合来完成。
以此可见,“意象”范畴渊源于“易象”,“易象”与“道”相关,既有形上性和神秘性又有直观性,所以意象也并非如通常所理解的那样仅仅只与物象与情感相关,而同时也是与道相联系的。这种道,在作者是一种关于世界的形上之思,在作品就是文本所呈现的形而上质。作这样的理解,才可以进一步理解文学意象的丰富性和深邃性,以及意象作为意境构成的基本元素这一事实。
参考文献:
[1] 勒内·韦勒克、奥斯汀·沃伦.文学理论[M].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
[2] 叶朗.中国美学史纲要[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5.
[3] 童庆炳.文学理论教程[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
[4] 王运熙,顾易生.中国文学批评通史[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
[5] 吴廷玉.易象与意象—超象表达形式及美学意义[J].学术月刊,1992.
[6] 陈鼓应.老子注译及评价[M].北京:中华书局,1984.
[7] 黄寿祺,张善文.周易译注(修订本)[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
[8] 陈鼓应.庄子今注今译[M].北京:中华书局,1983.
[9] 陈良运.中国诗学体系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
[10] 李学勤.十三经注疏·周易正义[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11] 高亨.周易杂论[M].济南:齐鲁书社,1979.
[12] 刘若愚.中国文学理论[M].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
[13] 北京大学历史系.论衡注释[M].北京:中华书局,1979.
[14] 范文澜.文心雕龙注[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
[15] 黄叔琳注,李详补注,杨明照校注拾遗.增订文心雕龙校注[M].北京:中华书局,2000.
[16] 王弼.周易注校释[M].楼宇烈释.北京:中华书局,2012.
[17] 郭绍虞.中国历代文论选(第二册)[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
[18] 郭绍虞.中国历代文论选(第三册)[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19] 李壮鹰.中国古代文论[M].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
[20] 闻一多.唐诗杂论[M].北京:中华书局,2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