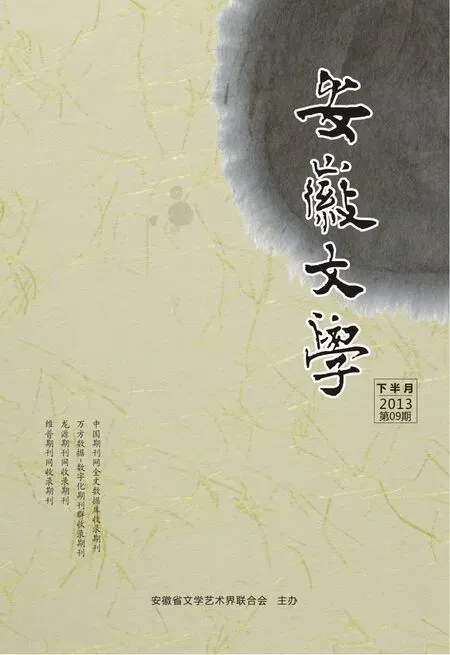《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之问题
缪伸涛
《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之问题
缪伸涛
巴赫金在《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中认为,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他的长篇小说中采用了一种复调思维,在处理作者与作品主人公的关系时采取了一种对话立场,从而打破了西方传统小说独白统一的窠臼,开创了新的艺术模式。本文认为,《诗学问题》自身存在一大问题,巴赫金在对作者“本人”的认识上存在很大偏差。
巴赫金 《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 作者主人公 复调的人
一、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长篇小说和巴赫金的复调对话理论
韦恩·C·布思在 《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的英译本导言中写道:“他在踏踏实实地研究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任何一部作品上是失败的,以及他固执于高层次的概括,这使我对他能够作的其他研究也都感到不耐烦。只要一个作者对被称为‘小说’(the novel)的大块文学、甚至对被称为‘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的小块文学冗长地赘述综合理论,而不是踏实细致地分析具体例证,我就愈感不安。 ”[1]
在《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的第一章,巴赫金使用了诸如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所有小说”、“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无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哪部小说”、“陀思妥耶夫斯基几乎全部小说”之类的论述,这无疑把复调小说的外延扩大化了。在第二章中,巴赫金总算第一次对外延做出了限定,即“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长篇小说”,这一限定在第四章和本书的结束语中又出现了两次。不难看出,只有这些论述对象集合的交集,即“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长篇小说”,才完全符合巴赫金对复调对话小说的定义。
巴赫金列举分析了当时评论界对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的几种代表性观点,通过对这些观点的正反两方面的评述,使复调对话理论的轮廓逐渐显现出来。巴赫金认为,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长篇小说中,主人公的意识被当做一种“他人意识”,是“自身的、直接具有意义的话语之主体”,主人公相对作者是独立的,同时各个主人公之间也是相对独立不相混合的。各种独立的不相混合的声音与意识之多样性、各种有充分价值的声音之正的复调,这就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的基本特征。[2]3
二、作者与主人公
巴赫金对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的“复调”定义,事实上是由两组“相互独立”构成的,即:主人公相对作者独立、各个主人公之间相互独立。在巴赫金之前,评论界已经有人指出了后一种独立,如:维亚切斯拉夫·伊万诺夫的“承认另一个‘我’不是客体,而是另一个主体”,格罗斯曼的“各个观点都能轮流统治”,奥托·考斯的“陀思妥耶夫斯基是这样一种家庭主人,他特别擅长跟最不同的客人周旋,能够控制最复杂的群体的注意力,善于使所有人都感到同样自在”,以及卢那察尔斯基的“各个‘声部’的深刻独立性”。巴赫金和评论界之间的分歧在对前一种独立的认识上。
格罗斯曼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道路》中把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的对话倾向揭示为作者本人世界观中没有被彻底克服的矛盾。[2]16巴赫金“不能同意这种揭示”,理由是“它实质上超出了作品的客观实际”。
奥托·考斯和卢那察尔斯基都考察了托斯托耶夫斯基复调小说产生的社会历史背景。卢那察尔斯基比奥托·考斯更进一步考察了受分裂的时代影响同样分裂的陀思妥耶夫斯基本人:
如果说陀思妥耶夫斯基作为作家是自己的主人,那么作为人他是自己的主人吗?
不,陀思妥耶夫斯基作为人不是自己的主人,他的个性分裂,他的崩溃,——即使他很想相信并不能使他真正信仰的东西,很想驳倒总是引起他怀疑的东西,——这使他在主观上对于自己时代的混乱很适合成为痛苦的、所需要的反映者。[2]38,39
巴赫金对奥托·考斯与卢那察尔斯基的起源分析是赞赏的,他对卢那察尔斯基的怀疑是在对复调小说的价值判断和发展前景上。
巴赫金一方面承认陀思妥耶夫斯基创作背景时代的分裂,也没有否定矛盾分裂在陀思妥耶夫斯基本人身上的客观存在;另一方面却一直矢口否认分裂的陀思妥耶夫斯基本人与他的长篇复调小说存在任何联系。所谓“超出了作品的客观实际”,似乎可以看做一个形式主义者理所当然地对作者问题的回避,这也是无可厚非的。但在第三章“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中的思想”中,巴赫金做了对他自己最不利的辩护:他试图证明,陀思妥耶夫斯基呈现了一个多声部的世界,但他只是在艺术思维上是复调的,在自身思想上则与任何一般作家一样,是统一的、肯定的、独白的。
首先他把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中的思想认定为一种“他在现实本身中发现、听到、有时猜到的思想”,[2]97陀思妥耶夫斯基被巴赫金赋予一种聆听时代声音的天才,而不是一种复调思考的天才。
紧接着巴赫金又为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里的思想形象/主人公形象寻找确定的原型。“例如,马克思·施蒂娜在他的论文《个人及其财产》中所叙述的思想和拿破仑第三在他的书《尤里斯·恺撒传》中所发挥的思想,就是拉斯科尔尼科夫思想的原型;《革命者手册》就是彼得·韦尔霍文斯基思想的原型之一;维尔西洛夫思想的原型是恰达耶夫和赫尔岑的思想。”[2]98,99似乎找出了这些思想原型就能证明,小说主人公并不是诞生于陀思妥耶夫斯基本人的思想,而是诞生于另外一些人的思想。
最后,巴赫金举例分析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政论文章和书信,提出了他自己对陀思妥耶夫斯基本人思想的认识:
陀思妥耶夫斯基不仅是一位写了许多中长篇小说的艺术家,还是一位在《时报》、《时代》、《公民》、《作家日记》等刊物上发表了许多相应文章的政论家、思想家。他在这些文章里表述了十分明确的哲学、宗教哲学、社会政治等方面的思想;这些思想在这儿(即文章里)是被他作为自己的肯定思想,以独白体系的形式或者演讲式独白(纯政论的)形式表述出来的。他在写给不同人的信里也时常表述这些思想。它们在这里——文章与书信——当然不是思想形象,而是直接的独白式肯定的思想。[2]100
巴赫金据此认为,陀思妥耶夫斯基本人的思想是统一的、肯定的、独白的。
三、陀思妥耶夫斯基——独白还是复调
巴赫金竟然试图让我们相信,假死刑和四年流放的经历不会在人的灵魂上留下丝毫印记,陀思妥耶夫斯基和任何一个普通作家一样,他本人的思想是“直接的独白式肯定的思想”。单看巴赫金在《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第三章中为“独白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做的辩护,就不难发现这些理据实际上漏洞百出。
陀思妥耶夫斯基确实写了不少政论文章,如巴赫金提到了《公民》杂志,对此格罗斯曼在《陀思妥耶夫斯基传》中这样评价道:
同这样一位政治投机家(指《公民》杂志的领导人梅谢尔斯基)接近,是陀思妥耶夫斯基一生中的可悲事件,也几乎是他最大的错误。[3]614
巴赫金认为陀思妥耶夫斯基在政论文章中表达了一种“直接的独白式肯定的思想”,然而他却没有考察这些“思想”的可信度。同样是在格罗斯曼的《陀思妥耶夫斯基传》中,我们发现:
刊物的新编辑同他的暗中领导人梅谢尔斯基的意见分歧很快暴露出来,针对《公民》创办人的种种浅薄而又卑劣的政治意图,例如返回到“尼古拉制度”等等,陀思妥耶夫斯基试图提出自己的纲领:“我的想法是,社会主义同基督教是一种对立物,我很想把这一想法写进一系列文章中,可是我却做不到”(1873年2月26日致米·彼·波戈金的信)。[3]616
叶尔米洛夫的《陀思妥耶夫斯基论》中也同样指出政论文章的不可信:
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作家日记》里宣传他的反动观点,但在艺术作品中,“除此以外”,他还创造了艺术形象。可是,正是在艺术形象里面,暴露出艺术家的具有现实矛盾的整个灵魂和他的真正的世界观,而在政论中,有时只可能表现世界观的“被修剪过的”、被熨平过的、跟矛盾人工地隔离开来的某一方面。[4]
我们同样可以用巴赫金自身的观点来反驳巴赫金。巴赫金写道:
当然,在政论文章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思想意识的这种生成形式的特点,不可能足够深刻地表现出来。那里只不过是表述的形式。思维的独白主义当然不可能在那里被克服。政论为它创造了最有利的条件。
既然政论天然不可能具有任何思维的复调性,即使出自陀思妥耶夫斯基之手也只不过徒具一种“表述的形式”,巴赫金却要用政论来证明陀思妥耶夫斯基思想的独白性,这显然自相矛盾。
米哈伊尔·巴赫金无疑是20世纪人文科学领域里最重要的苏联思想家,文学界最伟大的理论家,[5]171在对陀思妥耶夫斯基本人的认识上,为什么会出现这样大的偏差呢?托多罗夫解答了我们的疑问:一个真正的文学理论家必须思考超出文学以外的东西。[5]171巴赫金独特的哲学人类学决定了,“复调的陀思妥耶夫斯基”与他作为研究基础的哲学人类学是相悖的:
只有在他人那里我才能得到一个完善人的具有美学(和人种学)说服力经验和一种限定的先验客观性的经验。只有他人才能让我作为外部世界的一种同质物出现。因为人们只能拥抱他人,将他整个围起来,精心地去感觉他的全部。[5]307
巴赫金的哲学人类学是建立在“他人”的基础上的,“我”转化为“他人”眼中的“他人”,同时也就消解了。这也就不难解释为什么在《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中“他人”会成为被使用次数最多的一个术语(前后共出现38次)了。在巴赫金看来,如果陀思妥耶夫斯基是“复调的”,并且沉浸在自己内心的矛盾分裂里,这样一种“自我封闭”只能造成“失去自我”的结果,同时因为“内心活动”只能存在于“与他人的相遇”而不是在一个矛盾自我的内省中,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他的长篇小说中的心理描写也不可能有那样强的艺术感染力。
[1]韦恩·C·布思.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英译本导言[A]//巴赫金.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C].刘虎,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0:18.
[2]巴赫金.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M].刘虎,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0.
[3]格罗斯曼.陀思妥耶夫斯基传[M].王健夫,译.北京:外国文学出版社,1987:616.
[4]叶尔米洛夫.陀思妥耶夫斯基论[M].满涛,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9.
[5]托多罗夫.巴赫金、对话理论及其他[M].蒋子华,张萍,译.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1.
(作者单位:南京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