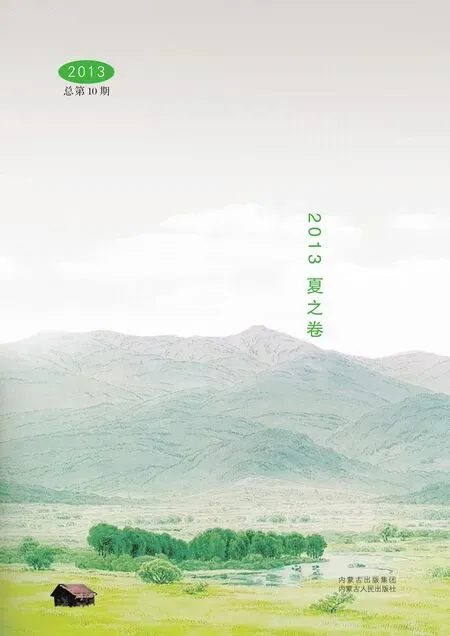彻悟与融通
——从纵向看王向峰近作风格
张无为
王向峰从1970年代开始写诗,至今坚持四十年已属难能,更可贵的是诗风也发展。
其初期风格正如黄桂元所说,代表作是1985年的长诗及其“某些史诗构架和思维气象”,在进入“活跃的入思状态”之后,手法上擅于通过构筑系列意象拓展诗的精神向度和意蕴空间,“以其寓言式的隐喻思考确立自身存在”,并“与哲学比肩而立,成为托起人类文明史的两大支柱”①参见《行者无疆的诗学跋涉——王向峰诗歌散论》(《黄河文学》2011年第7期)。
2003年应该是作者风格的重要转折。一方面,他创作的组诗《马背上的蝴蝶》颠覆、解构与戏谑立场非常鲜明,可谓另类的后现代文本。另一方面,作者经历过一场大病后,“望着那些来来往往的陌生脸孔,心里派生出一种想要走过去拥抱他们的温暖和冲动”,于是“开始重新审视自己,珍重无比……原来寻常的日子最有意义”。可以说,诗人“种下一粒鲜美生猛叫做冥想的果子”是从这时开始真正自觉勃发的,即通过个体生命感悟,探究生命奥秘,“诗境美好,但又这么疼痛”②参见《那些跌宕激越的日子,都成了诗》(2007年9月13日《每日新报》),如《读惠特曼诗作》、《这是我儿子》等。
本期这组诗均写于2012年下半年,作为近作,与作者以前的诗固然有风格关联,但明显的变化,一是进一步深入、冷静地彻悟人生;二是现实观照明显,风格实现融通。8首中,《雨夜梦入大泽乡》、《在北京南站乘地铁》、《吴先生的最后一天》以关注现实为主,其余5首均关涉到自我、生命及存在意义。
有人会问,《雨夜梦入大泽乡》不是选取了两千年的历史吗?是的,但该诗只是在夜雨与陈胜吴广起义之间获得契机,貌似追念历史,实则观照现实。诗中勾连出两千年来被压迫者的反抗,不屈不挠,连绵接续,目的恰恰是以“绕过我窗前”收拢至当下,个中既缘于现实的触发,又蕴藉了时代况味。夜雨年年有,此情常入梦,由此折射出现实症候及诗人复杂心绪。至于“草莽英雄的又一出大戏/抑或是误入了一场预谋?”则触及到更深层的斑驳。
而《在北京南站乘地铁》则直接揭示现代文明浮华背后的巨大失落感,其深刻之处在于,作者感受到人文精神丧失是心甘情愿的,由此暴露出人类性某种怪圈与无奈。只是,结尾若调整似更佳。《吴先生的最后一天》展现小人物的悲剧命运,即由于家庭、亲人、事业皆不幸,尤其是人性疏离,最终逼使他选择自杀。其实这与前面两首互为关联,互为因果。面对现实,人们如果拒绝屈从,就剩两条路:不能奋起反抗,只能愤然自绝。世界道貌岸然,人群普遍冷漠,则进而构成对现代文明的反讽。
其它5首,《我的风筝》、《我的九张面孔》均可谓作者的自我写照,包括自我的多面性、矛盾性展现以及对人与人的反思;《ha》则涉及到灵魂如何栖居问题;《搬走山的是一只手》以意象暗示出行动比思想的力量更强大;《致美国乡村歌手约翰·丹佛》借顶礼歌手表达对自由生命、人性本质的弘扬;《给诗人深耕》意味着作者与诗友同样“性本爱丘山”,共有人性之爱,归根结底是对生命休闲、田园牧歌的惬意,反观出畸形城市化及对其理性质疑。
这些诗不仅进一步体现出“直接攫取于日常生活的点滴感受”,“看似平实,实则机心老到,用意极深”的特点,而且其中的忧患主体意识、社会良知与生命况味、存在反思实现了交相辉映,也使得意象营造、自然口语与冷静舒缓相互融通、和谐共处。
如果说,以往“在‘第三代诗人’中,他的诗歌保持了朦胧诗的思想启蒙色彩与怀疑主义锋芒,却没有因循北岛、芒克们习惯于为特定的历史担承和意识形态代言”③参见《行者无疆的诗学跋涉——王向峰诗歌散论》(《黄河文学》2011年第7期),那么在这里,与朦胧诗或者第三代诗已经都没有什么关系了,在不断探索中,他又找到了新的个性呈现方式。可见,诗与年龄大可无关,执著探索就有新天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