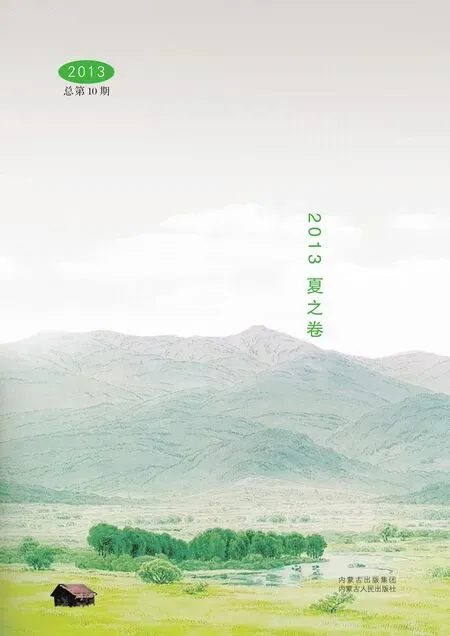一个把梦丢给真理的人
——王向峰诗歌作品简析
刘旭锋
给王向峰先生写诗评,莫过于鲁班门前耍大斧,不过,换而言之,连斧头都不敢抡的人,即使能设想出五花八门的家具样式,顶不过是些“海市蜃楼”。提起“海市蜃楼”这个词,就想起了中国文学,曾几何时,中国文学一度繁荣,尤其是中国诗歌,这种一晃而去的盛景丝毫不会因莫言荣获诺奖而彻底复现。前几日,一个写小说的朋友和我聊天时说,他认为倘若中国文学被诺奖青睐最值得获奖的应该是诗人。他这个振聋发聩的观点让我冒了一身冷汗,可是,待我片刻思索后,我好像接受了。
诗歌是中国文学的渊源,也是中华文明流传至今最古老的一种传承题材,无论是古诗词,还是现代诗,其精髓都具备中国人身上几千年沉淀下来的那种内涵气质,或是辩证思考问题的道家式的轮回审美观。中国诗歌之所以迟迟和世界文学接不上轨,我认为这不能单一地抱怨翻译的无知,更应该称颂中国诗歌的写意精神太高深,翻译领域有时候只能望洋兴叹。从这个角度看,似乎得不得诺奖,其实已经无关紧要了。
我读诗歌比较快,这是很多朋友批评我的地方,他们提醒我读作品要慢,要去品。其实,我的速度是快的,我对诗歌的感悟却是一个慢的过程,一组诗歌我会很快地明确作者的意图,却需要花很长时间去揣测作者有这种创作欲望的动机。是的,需要了解一个人创作动机,才能了解这个人是一个积极的人还是一个消极的人。当然,积极和消极都能出作家,且都能出大作家。这如同,痛苦能成大志,优越的生活条件也能帮助一个人成大志。在这里,我要说,王先生是一位积极的人,因为他在积极思考。
王向峰的诗歌使我快不起来,他的诗歌要求我仔细去读,重申一下,是他的诗歌要求我仔细去读,不是他这个人要求我去仔细去读。他的诗歌,把很多意象都切开了,就像切一块豆腐一样,一块一块的,块与块之间,是留白,是作者可以赋予的二次联想。他有一首诗歌《吴先生的最后一天》,里面有这么一小节“吴先生沿螺旋楼梯一步步向上/像哲学家思考人生似的/他找到了去天堂的近道”。三句话,把自己和哲学家还有天堂联系在了一起,当然,这里的天堂可以是心中的。这三个独立的意象,在此就是一块完整的豆腐,虽说是完整,但必须肯定它们之间是分割的,是必须用诗歌中的这种分行的形式拨开才有意义的一种表达方式,不然,就会成为一块水豆腐,少了正宗的北方豆腐应有的一股韧劲。
他的诗歌几乎全部是开放的,这里的“开放”这个词是广义上的开放,也就是说,读完作品后,你会向几个方向延伸思索,不一定和作者的初衷相同,但和作者的写意精神必定是相吻合的。
《我的九张面孔》里,最后一小节是这么写的“象一个被唤醒的失意者/心,在慢慢解冻,皓歌长空/独自等待大地回春”,强大的气场可以引领读者回旋在天地之间,他的这种力量既是向上的,也是向下的,既是封闭的,也是开放的。所以,我着重强调了一下广义两个字。某种程度上,所有的诗歌都应该是开放的,就像某种程度上,所有的白天应该都有太阳,所有的黑夜都应该有星辰。
王向峰的文字很老练,成熟的思维能轻松地驾驭着文字游弋,这和部分人有着明显的区别。有些人写诗歌也是在写,写小说也是在写,写散文还是在写。写来写去,有的人把自己写糊涂了,写的分不清诗歌和散文的区别,写的分不清诗歌讲故事和小说讲故事其实是大不同的。“一个声音在云中说:只有乌有之乡,才是/唯一值得居住的/我谢谢他:有您这句话/再多的苦/也该担着”。诗人在《智者的声音》一首中其实讲述了一个心中的故事,他告诉我们,有时候无为和有为并不绝对,乌有,有时候确是我们顶住痛苦的一种方式。这种讲故事的方式,新颖,有创造性,把文学世界的旧世界和诗人心中的新世界巧妙穿插起来。
读王向峰的文字,就是给自己的思想进行一次修整,对着未来和过去进行一次二重谈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