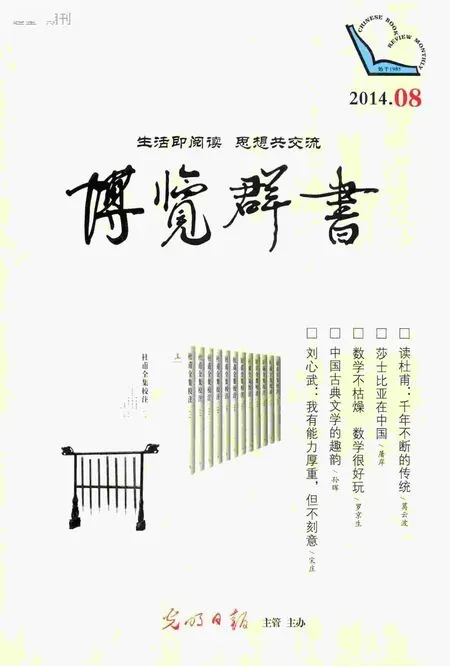《红舞鞋》的诱惑
○ 启 之

●江青最欣赏的镜头
暮蔼沉沉,华屋静寂。昏黄的灯光中,莱蒙托夫坐在沙发上,茶几上放着一封辞职信,一个堆满了烟蒂的烟灰缸。他两只手交叉在胸前,两个大拇指不停地转动。镜头推进,在他的脸上定格:紧锁的眉宇,紧绷的嘴唇,恨怒交织的眼神……他抓起那封信,站起,踱步;“啪啪”,他用力拍打着手中的信,自言自语:“蠢呀!”“蠢呀!”“真蠢呀!”——我们无从揣测,这个“蠢”指的是他自己,还是指剧团的台柱子——那个为了爱情而辞职的蓓蒂。
莱蒙托夫走到镜子面前,镜子里映照出一个英俊的中年男子的脸:棕色的眼睛,略带卷曲的浓密的黑发,标致的小胡子。他注视着镜子,嘴角掠过一丝嘲讽,突然,他龇牙咧嘴,一拳砸向了镜子。镜子裂了。拳头落下的地方,出现了一圈圈白色的裂纹,这些裂纹呈放射状扩散开去,使镜子里的人像残缺不全。
这是电影《红舞鞋》(又译为《红菱艳》,1948)里的一个镜头。
在江青欣赏的西片中,《红舞鞋》是她看的次数最多的一部。她的保健护士说她“《红菱艳》看不厌,菠菜泥吃不厌”。她不仅从头到尾地看,还要挑其中的某个段落看。放映员因此对这部影片了如指掌。只要江青吩咐要看哪一段,几分钟之内它就会呈现在银幕之上。莱蒙托夫砸镜子的那一场戏是江青的最爱。
●一个老掉牙的故事
这是一个老掉牙的故事:芭蕾舞剧团的老板莱蒙托夫偏执地认为,要成为伟大的艺术家,就必须放弃爱情。他让蓓蒂担任《红舞鞋》的主角,蓓蒂一跳成名。正当莱蒙托夫决定让她在所有的舞剧中担任主角,全球巡演,从而将她培养成一名伟大舞蹈家的时候,她却与作曲家格拉斯跌入爱河。莱开除了格拉斯,蓓蒂愤而辞职。莱虽然启用另一女演员担纲主角,但他仍想让蓓蒂回来。一次,蓓蒂来到剧团所在的城市,莱用成名成家说服蓓蒂,蓓蒂答应再跳一场《红舞鞋》。这时,格拉斯赶来,要求蓓蒂放弃演出。莱斥责格拉斯耽误蓓蒂的前程,并提醒蓓蒂要遵守演出合同——台下的观众正在翘首以待。蓓蒂进退两难,格拉斯斥责她背叛爱情,愤然离去。蓓蒂冲出剧院,追赶格拉斯,不幸在车站殒命。临终前,她让格拉斯脱下她脚上的红舞鞋。
两个男人争夺一个女人的故事,早在古希腊就有了。“特洛伊之战”就是因此而引起的。
●安徒生的“新教伦理”
说这个电影是根据安徒生的故事改编的,并不很准确。安徒生虽然也讲了一双跳个没完没了的红鞋,讲了诱惑与惩罚,但他的主旨是放弃物欲,摒弃虚华,勤劳节俭,忠于上帝,常思报恩。
在安徒生的故事中,小姑娘珈伦在做坚礼、吃圣餐时心不在焉,老想着她那双漂亮的红鞋,是对上帝不忠。她不去照顾生病的养母,而去参加舞会以炫耀那双鞋子,是失掉了报恩之心。那位留着奇怪的长胡子、拄着拐杖的老兵是撒旦派来的魔鬼。他出没在教堂门口,不断称赞珈伦的红鞋多么漂亮,是在诱惑珈伦。当珈伦迷上红鞋,他就向鞋施以魔法,让它自动跳舞,而且牢牢地长在了珈伦的脚上。
上帝对她的惩罚是残忍的——快被累死的珈伦,不得不请求刽子手砍掉她的双脚。而那双穿在血淋淋的双脚上的红鞋,还是在她的眼前大跳特跳,恐吓她不许去教堂。
上帝对救赎的吁求是冷酷的——即使在她虔诚地忏悔之后,那位庄严沉着,手持长剑、身穿白长袍、煽动着翅膀的安琪儿也不肯施以援手,坚持要把惩罚进行到底——她乞求牧师收留,拖着残疾之身为他家干这干那。只有到了晚上,在牧师念圣诗的时候,她才有机会聆听。为了表示忏悔之诚,每当牧师的家人谈论衣服之美、排场之华的时候,她就摇头。礼拜天,当牧师一家去教堂去听上帝的训诫的时候,她满眼泪水,凄惨地看着她的拐杖,不敢同往,只能躲在自己的小屋里手捧圣诗集,以至诚至敬之心诵读。教堂的琴声随风而至,她以泪洗面,吁求主的帮助。
只有在这时,上帝才显出一丝慈悲——安琪儿出现了,把这个失足的残疾姑娘带到教堂。珈伦得到了宽恕。琴声优雅,歌声美妙,朗日睛空,巨大的幸福充盈其胸,使她无法承受。她的心爆裂了,她的灵魂飞进了天国。
这篇故事源于安徒生对早年生活的回忆:14岁受坚信礼那天,他穿了一双新靴子,每走一步,靴子都咯吱作响。起初他为引起众人的关注而得意,但是,他很快就意识到,这是对上帝的大不敬。
这个故事表述了基督徒的人生观:勤劳、俭朴、克己。故事中的红鞋是虚荣和物欲的化身,砍掉双足代表要用肉体的痛苦来赎回物欲之罪,而不计报酬的劳作、摒弃物欲及享受才是人生的康庄大道。这正是马克斯·韦伯所说的新教“入世的禁欲主义”。
或许,可以说《红舞鞋》对安徒生的故事做了创造性的转换。在这里,艺术成了上帝,爱情成了诱惑人的物欲,莱蒙托夫成了上帝的使者——那个严厉的、不通人情的安琪儿;格拉斯则成了魔鬼——那个留着长胡子的老兵,他用男欢女爱来诱惑蓓蒂。

●莱蒙托夫:一个“迷人的魔鬼”
这是伯爵夫人对莱蒙托夫的评价。他为什么成了“魔鬼”呢?因为他清高简傲,刻薄无情——为了给侄女创造进入莱蒙托夫芭蕾舞剧团的机会,伯爵夫人举办大型晚宴,费尽心机把这位名满四海的剧团老总请来。可是,他对这位高贵的女主人,一点也不给面子。
伯爵夫人对莱蒙托夫说,她为他准备了一点意外的享受。
莱反唇相讥:“是享受还是难受?”
伯爵夫人不得不直言相告:“我想请你看看我的侄女跳芭蕾。这该是难受还是享受?”
莱更直裁了当:“这是难受。”
贵族的标志之一,就是有教养。伯爵夫人尽管很下不来台,但仍然用微笑掩饰着尴尬。要是换上中国的新贵,恐怕莱总的脸上会挨上一拳。
莱问伯爵夫人,什么是芭蕾?夫人说,芭蕾是一种动作的诗篇。莱告诉她:“远不止如此,芭蕾是一种信仰。任何人都不会允许自己的信仰在这种环境里表现出来。”
这个“魔鬼”的刻薄还远不止于此。
在巴黎,剧团在排练,女主角依莉娜激动地向大家宣布:我要结婚了。大家上前祝贺,只有莱蒙托夫在一边冷冷地注视着。依莉娜想请莱蒙托夫说一句祝福的话,莱转身走掉。“太没心肝了。”这是依莉娜对莱的评价。
剧团离开巴黎时,依莉娜到车站与朋友们告别。莱蒙托夫走来,依莉娜迎上去,莱冷冷地叫了她一声。依莉娜受宠若惊,含情脉脉地闭上眼睛,上身前倾,等着莱的吻别。莱再次转身离去。依睁开眼睛,伤心欲绝。
如果说,莱对伯爵夫人的冷漠,是为了维护芭蕾舞的高贵和纯洁,使之不受世俗的污染。那么,他对依莉娜的冷漠,则是出于一种牢不可破的偏见——婚姻是艺术坟墓。他对丑角留伯夫说得清楚:“沉湎于爱的空虚情趣的人,绝不能成为一个杰出的舞蹈家。永远不会!”
那么,这个魔鬼何以迷人呢?
首先,他是艺术大师。他精通芭蕾舞的所有艺术,从音乐、舞蹈、服装到舞台设计。他善于发现人才,培养人才。只凭一支短短的曲子,他就聘用了还在大学读书的格拉斯来剧团作曲,他把一个普通的芭蕾舞演员蓓蒂,培养成了大红大紫的明星。
其次,他是企业家,更是事业家。他不但知道如何经营,如何提高剧团的知名度,还把剧团当作培养艺术家的摇篮,把自己视为艺术的守护神。他的最高人生目标就是培养芭蕾舞大师。
再次,他精通人情世故。当格拉斯冲进他的办公室,控告《火之星》舞曲的作者帕沃教授剽窃了他的作品时,莱蒙托夫劝告这位激动的年轻人:“马上把信销毁,把这事全忘了,这些事往往是无意中发生的。值得记住的是,失窃者固然不幸,但是剽窃者更为可悲。”
迷人,对于异性来说,恐怕还包括他对美色与情欲的决绝态度——作为剧团老总,他年年月月天天处在美女、才女的包围之中,所有的女人都在向他献殷勤,都渴望得到他的爱抚。然而,人到中年,他仍不为美色所动。
蓓蒂说他是“有才华的残暴的恶魔”,这其中未必没有醋意。
●江青的“自我实现”
每个人都有欲望,都会被诱惑。最普遍、最要命的诱惑是掌声、鲜花、赞美和万人拥戴。这是一种永远无法满足的欲望——听惯了“万岁”“乌拉”的人们,总是希望有更多的掌声,更多的“万岁”“乌拉”。阿谀迎合之辈从来不曾缺少,于是,敬爱就会变成最敬爱、最最最敬爱、最最最最敬爱……马斯洛所说的“自我实现”的顶峰也不过如此吧?可惜,“自我实现”是受道德原则支配的,它至少可以分为利己利人、利己损人、利己但不损人三种。
江青说,她看西片是为了学习人家的技术。这部穿插了大量芭蕾舞的影片,是否对她指导中国的芭蕾舞片有帮助,我们不得而知。我们知道的只是,她曾经一遍又一遍地看这部电影。
从1963年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之时,中国的撒旦就让江青穿上了“红舞鞋”,在权力的诱惑下,她大跳特跳,从京剧改革到样板戏,从中央文革到“反击右倾翻案风”,这双红舞鞋让她跳了十几年。直到跳进了秦城,聪明的江青也没有悟出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