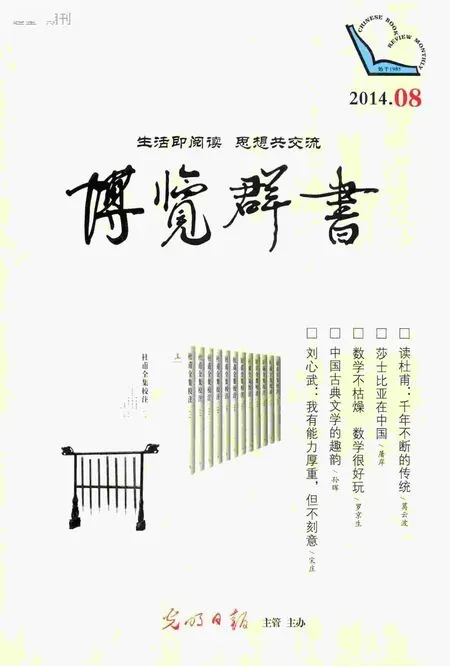《金瓶梅》《红楼梦》确实好玩
○ 马瑞芳
商务印书馆“双子书”《金瓶梅风情谭》《红楼梦风情谭》其实是由两个报纸专栏拓展而成。
我为什么写这两本书?归根结底是出于对传统小说的热爱。最入迷还是大学五年,《红楼梦》评点本一直放在枕边,被我翻烂了。我第一篇红学论文《妙玉的悲剧》,原打算做古代文学史开卷考试作业,因当时强调思想性,又改写《贾宝玉批判》。两篇1964年的手稿居然保留下来。此后我做了多年宝塔尖内小说研究,比如1985-1989做了几千张卡片,写了本《聊斋志异创作论》。1990年出版,印了三千册。1995年王扶林导演到山东执导我的长篇小说《蓝眼睛黑眼睛》为十七集电视连续剧时,《聊斋志异创作论》还没卖完。我想,如果我的研究成果有王导演87版《红楼梦》百分之一或千分之一读者就满意了。2004年我花一年时间写了三篇共七万字的《红楼梦》成书论文,蔡义江教授帮我看稿时写了十几页意见和建议,后来文章发在《红楼梦学刊》,与我的聊斋研究一样,即使文章被学者看重的《人大复印资料》、《新华文摘》收进去,读者仍不过是同行小圈子。其实我早就琢磨过,学术研究成果能不能走向大众?过去有过“大众哲学”,我们能不能搞“大众红学”、“大众金学”、“大众聊斋学”?20世纪80年代我开过报纸专栏《趣话聊斋》,大诗人臧克家撰写刊名。这是让学术走向大众的“牛刀小试”。
2004年百家讲坛约我录制二十四集“马瑞芳说聊斋”。2005-2007在央视播出,我学术研究的成果“受众”从圈内走向圈外。郭建磊秘书曾向我转述时任政治局常委吴官正的话“《说聊斋》既有群众性又有学术性”。歌星刘德华、诺贝尔奖得主丁肇中、莫言乐意看“说聊斋”,贺敬之、柯岩、铁凝、海迪……很多作家跟我聊看“说聊斋”感受。有次签名售书,中国八十岁读者和波兰五岁小读者同时到场,我家中读者年龄跨度更大,从八岁孙女阿牛到九十岁的老奶奶。我问阿牛:“奶奶讲得怎样?”“还行。”“比你老师?”“差不多。”我乐呵呵地说:我终于达到小学一年级教学效果了!有一次,我穿件十年前做的价值不过二十元的旧裙子在农贸市场买菜,有位中年人过来惊讶地问:“您是说聊斋的马教授吗?您也亲自买菜?”我笑道:“不错。我还亲自吃菜。”参加中国作家代表团出访更有趣,在波兰,八十岁的汉学家说“我是你的粉丝”;在布加勒斯特机场,大使馆秘书说:“我常在央视国际频道看马老师讲课,今天终于看到个活的!”真会“外交词令”啊,我大乐。
大学讲几十年聊斋,受众不过大学生、研究生、留学生,上一次电视,成了“你也说聊斋我也说聊斋”,我感慨万分,写了本散文集《百家讲坛这张魔鬼的床》,写阎崇年、易中天、于丹、王立群、隋丽娟等坛上朋友,还总结出条规律:百家讲坛是那张西方神话传说里“魔鬼的床”,上了这张床的学者,长的截短,短的拉长,按什么标准?十六个字:“传统文化,走向大众,深入浅出,雅俗共赏”。
“说聊斋”后,我再出书就不是高堂讲章《聊斋志异创作论》那种命运了。
话还得回到《风情谭》双子书上。红学、金学名家如林、佳作纷呈,怎么写出属于自己的东西?只能找属于自己的角度。我用当代小说家视角,把名著细节讲给读者听。我也是写小说的,我的“新儒林长篇系列”《蓝眼睛黑眼睛》、《天眼》、《感受四季》曾在德国亚洲文学讨论会讨论,还载入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华文学通史》当代卷第十一章第五节。过去我写小说论著,习惯“高屋见瓴”说思想论艺术,求“学问”求“深度”,现在放低身段,做两部名著“景点导游”。这个细节是什么含义?它有什么文化含量?这些极小极微的“风物”,对故事、对人物、对小说布局起什么作用……我自己写小说时体会到:故事好编,细节难寻。我就要研究《红楼梦》以及它所学习的《金瓶梅》如何用一个一个细节堆起两部世界名著?金瓶梅》学会会长黄霖教授对这两本“风情谭”的评价是:“小中见趣、小中见大、小中见学(问)。”我把这些绝妙细节用通俗简明的话告诉读者,你喜欢这些细节?去看小说吧。
我写小说时特别注意出来一个人给读者什么印象?先要知道他长什么模样,穿什么衣服,为什么穿这衣服,在什么情况下穿这衣服?我这是从哪学的?从欧美俄罗斯长篇小说,特别是《红楼梦》学的。黛玉进府,曹雪芹对她衣饰的描写一字没有,想想非常合理,为什么?林家封过列侯,林如海是巡盐御史,很有钱,林黛玉肯定穿着华贵。但如果描写她穿得多讲究,贾府收养她的悲凉气氛就不存在了。出来接待林黛玉的王熙凤衣饰则描写极细,金碧辉煌,宛如妃子,特别是头上戴着朝阳五凤挂珠钗这一性格化、命运化首饰。王熙凤是攫权攫钱的铁凤凰,又是冰山上的雌凤,贾府这座冰山一倒,落时凤凰不如鸡,就得刘姥姥救王熙凤的女儿。刘姥姥吃茄鲞、史太君两宴大观园,此情只可成追忆。大观园是《红楼梦》最好的风物。神需要特有庙宇,人需要特有环境,林黛玉需要住到“有凤来仪”的潇湘馆。林黛玉是《红楼梦》精神上和贾宝玉比翼齐飞的金凤凰。凤凰讲究清洁的精神,非梧桐不栖,非醴泉不饮,非竹实不餐。绿竹清溪的潇湘馆凤尾森森、龙吟细细,鹦鹉会吟诗。林黛玉在这里诗意栖居,写她的人格宣言《葬花吟》,爱情宣言《题帕诗》。宝黛爱情是精神恋爱,追求的是共同理想和志趣。薛宝钗的金锁是薛姨妈为追求与贾府联姻刻意打造,金锁不可能跟代表着“曹雪芹”的通灵宝玉是一对。大观园每个地方都和它住的主人联系在一起,这些风物决定这个人、这个故事怎么往前发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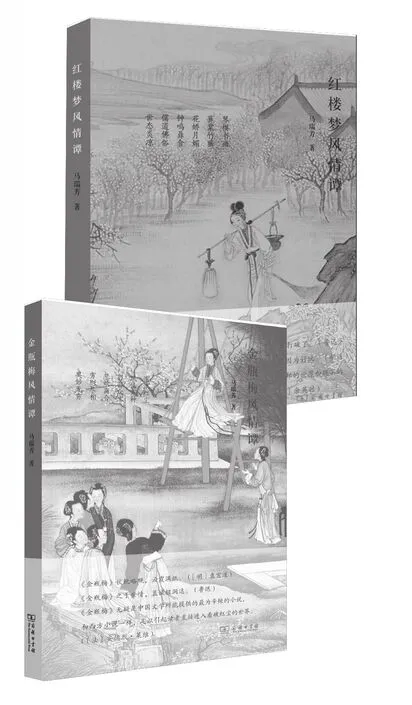
鲁迅先生说《金瓶梅》写人生,或“刻骨而尽相”,或“幽伏而含讥”。因为《金瓶梅》写人特别注意捕捉活灵活现的细节,人物举手投足风情万种、跃然纸上。《金瓶梅》可算明代社会别致的经济史,举凡市井社会物质生活的一切,都可以从《金瓶梅》找到印证。西门庆及其妻妾、内外宠的穿衣插戴,从西门庆骑的高头大马到官哥儿玩的拨郎鼓儿,从孟玉楼的金簪到李瓶儿的金簪,从潘金莲的毛青布大衫到春梅的命妇服,西门府内外的饮食茶酒,从武大郎炊饼到王婆梅汤,从应伯爵赞不绝口的糟鲥鱼,到春梅故意陷害孙雪娥的鸡尖汤,《金瓶梅》对市井社会的衣食住行、地方风情观察细微、描绘如画,饮食男女写社会,细枝末节看人情。用小物件、小饰品寄寓人生大悲欢、大道理,是《金瓶梅》教给《红楼梦》的。《金瓶梅》属于市井,而且是属于市井最聪明的人物。不要小看西门庆、潘金莲,这些人的智慧丝毫不亚于贾宝玉、林黛玉。西门庆玩女人讲人财俱得,玩官场知道投资性价比,从知县到宰相都被他的金钱指挥棒耍得团团转。潘金莲会用一只临清猫害死李瓶儿的儿子。我们为什么研究《金瓶梅》?因为它不仅是文学经典,《金瓶梅》的人物仍然活跃在好莱坞宝来坞,走在香榭里舍大道,全世界灯红酒绿场所的“西门庆”、“潘金莲”正在书写新的人生。
毛主席说《金瓶梅》是《红楼梦》的老祖宗。我琢磨:它是怎么样传承过来的?我注意到琴棋书画的例子。西门庆居然有琴棋书画!他的书童叫琴童、棋童、书童、画童,跟他发生不同的联系,有的是同性恋伙伴,有的是他请的秘书的同性恋伙伴,有的成了潘金莲的小情人,有的在他家上窜下跳制造矛盾,西门庆有如此奇异的琴棋书画。到了《红楼梦》,成了贾府“元、迎、探、惜”四小姐的贴身丫鬟。抱琴、司棋、侍书、入画,各人都有自己的故事,司棋把自己和小姐的人生司成一团乱棋,侍书将来只能给探春磨墨写想念家乡的信,入画看着惜春那幅大观园的画永远画不成,抱琴也该有跟贾元春一起瑟冷琴断故事。从西门庆的琴棋书画四童变成贾府琴棋书画四丫鬟,不仅青出于蓝,简直如凤凰涅槃。像应伯爵这种人《红楼梦》绝对没有,算得上古代小说“第一帮闲”。
两本书虽然叫“风情谭”,却也是我前一套四本“趣话经典”的延伸。我为什么要趣话经典?因为经典常读常新,经典总是有趣的。像《红楼梦》这样的经典,你从哪一页打开、什么时候看都有新体会。胡适有那么多研究《红楼梦》观点,我对他印象最深的观点是《红楼梦》好玩。当年唐德刚写胡适传,胡适对他说,《红楼梦》不是好小说,《红楼梦》没有主题。唐德刚问:没有主题你为什么还研究?胡适说:“《红楼梦》好玩啊”。唐德刚曝光这段话是1985国际红学会上,我一直记在心里。我发现《红楼梦》确实好玩,它的好玩是在中国非常繁富、博大精深的文化基础上发掘人心的奥秘,写得妙趣横生,叫你爱不释手,所以我也想发掘《红楼梦》以及《金瓶梅》它为什么有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