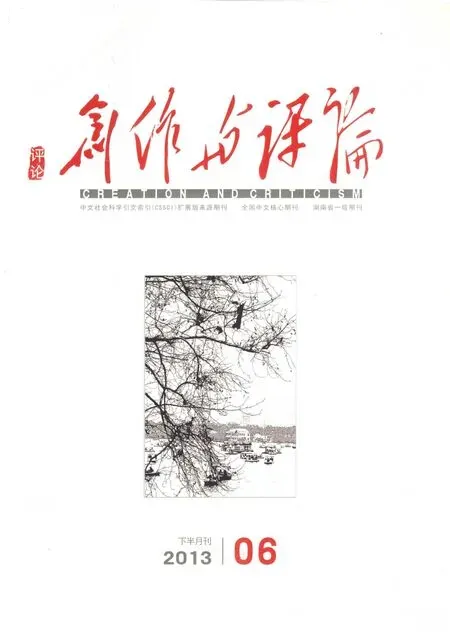《碧奴》: 『入魔』的写作奇迹
○ 袁红涛
“重述神话”是由英国坎农格特出版公司发起的全球首个跨国出版合作项目,各国作家以本国神话故事为原型,融合个性风格,重塑影响世界文明中沉淀了数千年的神话经典。苏童以重述“孟姜女哭长城”的传说成为入选这一项目的首位中国作家,该书的写作自启动之初便引来了广泛关注,出版之后更多获热评。如今热闹散去,“重述神话”的浩大声势似也没了多少下文,或可以静下心来看看苏童究竟书写了一个什么样的神话。
通过这次写作,作者谈到有一个最大的感受是,“神话确实是被很大一部分作家所忽略的文化资源。写神话让我回头向后看一眼。有时候往后看一眼,真的有灯火阑珊处的感觉。作家很多时候要靠想象去创作,借助民间神话,就是借一双翅膀飞翔。”①作者的这一感受当然值得中国作家借鉴,也因此笔者更加关注在《碧奴》中作者是如何认识和处理已在中国民间流传了数千年的关于孟姜女哭长城的传说,又是如何借助民间传说展开想象的翅膀、进行自己的重述的。
对于孟姜女传说的“本事”,作者这样复述:“这个民间传说的大致内容,是关于两千多年前的一个女人,自己的丈夫被拉差拉到很遥远的地方筑长城,所谓秋风一阵冷似一阵,在这种天气的压迫下,孟姜女觉得她有一关过不去,所以要给丈夫送棉衣。一个非常简单的故事导致了这个民间传说的起因。这个女人千辛万苦千里迢迢到了长城,但是丈夫已经死了,她当然要哭。‘哭’谁都能够了解和理解。”——因为“哭”谁都能了解和理解,所以它没有成为刺激作者重述的动力,也不构成小说的叙述重心。作者的关注点在于——“问题是,神话也好传说也好,到了这一步,突然产生了非常意想不到的力量,也是我之所以选择‘孟姜女哭长城’的故事作为新的长篇小说的题材和内容的大的动机,这就是:一个女人的眼泪竟然哭倒了八百里长城。这个传说之瑰丽,彻底征服了我。接受英国出版公司的‘重述神话’计划后,我脑海里无法摆脱的是一个女人的眼泪与城墙的故事。我要琢磨它、吃透它……”②作者在另外场合交代:“我曾在‘大禹治水’与‘孟姜女哭长城’两个经典神话中徘徊,但后来考虑孟姜女的故事更感人,你想,为丈夫千里送衣并用眼泪哭倒长城,可谓悲伤到顶、浪漫到顶。孟姜女让我入魔了。”③打动作者的,不是传说的故事情节或者内涵的情感,而主要是传说所展现的“想象”方式本身,这种形式的“瑰丽”和“浪漫到顶”征服了作者。由此,诚如作者所言,他在叙述中“入魔”了,他渴望创造一个自己写作的奇迹:“关于孟姜女的故事,如果要说一个支撑点的话,也是眼泪。其实这一部小说写下来,我觉得我是在尝试一种奇迹,是要用一滴泪支撑一个故事,支撑整部小说。”——在《碧奴》中,在四溢横流的泪水中,在离奇曲折的过程中,传说故事的历史与情感内涵被抽空,人物行为动力与信念被悬置,泪水的奇幻就是故事的主角,过程的铺陈即是叙述的指向。建构一系列的“隐喻”或者符号成为作者的兴趣所在,对于叙述本身的迷恋即是叙述的动力。作者着力于创作的是一部“泪水的传奇”,即建构一个情感的仪式或者符号;作者更欲由此情感仪式化、符号化的过程,以抽空动力的铺陈、无所依凭因而无拘无束的“自由想象”、“神性”缺席的重述建构一个神话,一个更近似于有关写作行为本身的“神话”。
在踏上重述之路的时候,作者对于传说故事主要做了两方面的处理:一是故事的主体由孟姜女转换为“碧奴”的“眼泪”;二是以对孟姜女寻夫过程满满当当的填充和铺陈,悬置了内在动力或者信念的呈现。认识这两点,是准确理解作者叙述意图、阐释小说“意义”世界的关键。
翻开小说,泪水的瑰丽奇幻让人叹为观止。在回答网友关于神话故事与小说最本质的区别时,作者也坦言:“在传统的孟姜女故事的版本中,孟姜女作为一个女人的形象大于一切,而在《碧奴》中,碧奴的眼泪大于一切”。“书中我把眼泪作为一个形象,眼泪当然不是一个人物,但是它变成一个非常重要的形象来塑造。所以在更多的时候,我在塑造碧奴,是通过碧奴身上泪的传奇来塑造的。”其实小说对眼泪的渲染不仅是或者不是塑造人物的方式问题,而是关乎小说叙述指向的转换:从对于人物形象的塑造转向对于情感符号的建构。通过将主人公由“孟姜女”改名为“碧奴”,进而将故事的主角由“碧奴”转换为“泪水”,屏蔽了原有传说中沉淀层积的历史意蕴和内涵,这一次重述不再负担有关反抗暴政的叙述义务同样,由于跳过了人物和人物哭泣的动作,直接指向对于泪水的描写,通过省略主语,从而回避对于人物情感主要是爱情的描写。面对有记者提出,在这样一个“千里为夫送寒衣”的故事中,为何并没有着重写夫妻深情,而将更多笔触停留在“碧奴流泪和她一路北上的艰辛”上这一问题时,作者承认这样的安排是刻意的,“爱情我留给读者遐想,如果这书大篇幅地写爱情,不仅让人觉得我强加太多的主观,也会让人觉得太没新意、太流于俗套了。”当然,作者的这一转换不仅仅是为了回避,更包含有主动的选择:述说一个“泪水的传奇”,让泪水成为情感的符号,把孟姜女塑造为一个“哭神”。作者自言:“我刻意去发掘眼泪的意义,似乎到最后,眼泪变成了我刻意塑造的形象。我在小说中最大的野心和企图的实现,是对眼泪的描写。”所以在小说中,流泪主要是一个掌握方法的问题,在许多的时候主人公在昏睡但泪水自行喷涌。尤其是随着故事进展,流泪的声势和规模越来越大,但是似乎和主人公内心世界关系不大。尽管这可以理解为碧奴内心的创痛在加剧,悲伤在加深,但是小说绝少人物内在世界的呈现,其实是在隔离这样一种解读的可能。那许许多多的泪水只是从碧奴的身上流出而已,流泪部位的匪夷所思,泪水的五味杂陈,由于泪水本身的神奇带给了主人公一系列离奇遭遇,凡此种种的渲染铺陈最终使得泪水成为小说的主角,泪水淹没了人物,泪水替代了感情,成就了一部“泪水的传奇”。然而,以“传奇”为神话,以这样一种建构符号的方式来接近神话,是不是包含着作者对“神话”理解的某些错位呢?
作者对于传说着力加工的另一方面是对孟姜女寻夫过程的填充。在故事一开始,碧奴就踏上北上寻夫之路,寻夫的过程几乎占去了全部的篇幅。有评论认为,“这似乎有违传说原来的基本架构,但这一点恰恰是被民间传说所忽略的地方,也因此成为苏童用力最勤,同时也是最显功力而又最具感染力的地方”④。作者自己介绍,小说的“构思很苦”,而最困难的地方就是“碧奴送寒衣之路艰难无比”的设计,“对环境设置我有野心和企图,送衣之路不可能那么简单,于是我刻意弄了很多困难。我要把这条路弄得更加坎坷,变得更有意义。”于是在小说中读者看到了为百春台门客送葬、寻找泪人入药、遭遇“鹿人”、“马人”等等离奇的情节。不过这些情节是如何“变得更有意义”、具有何种“意义”呢?
一些评论意见都曾追问作者,碧奴百折不挠地走在这条坎坷的送寒衣之路上,背后的动力是什么?⑤之所以有这样的疑问产生是因为,小说中的碧奴有坚持的行为,但是作者并不赋予她这样选择的内在意识。作者对此的设计是:“碧奴哭长城之前的旅程苦难到无以复加,她身上有种原始的动物性,有本能的生存欲望,所以她没有崩溃。”——所以,对于碧奴坚持的行为曾有的两种很有代表性的阐释,其实和作者的意图都是有距离的:一种是认为碧奴这种被动的愚钝的坚持不过是显示了叙述者内在的男权主义伦理⑥,一种则对之进行了存在主义式的解读⑦。然而在作者自己的认识中,碧奴的行为原来是基于一种“原始的动物性的本能”。作者对于女主角更进一步的解释是:“碧奴还真不好被归类。必须写得像一个半蛮荒半文明时期的女人,是单纯朴素的情感动物,自我认识或者性格培养都是被动的。如果要这样一个女子有今天所谓的女性意识,那是瞎掰。那个时期来自下层的女子几乎是‘低贱’的,她的世界就是她的丈夫,她的人生之路就浓缩在去长城千里寻夫这一路”。因而,虽然碧奴走在这条坎坷的路上,但是她作为一个被动的“情感动物”并不能使自己走过的道路、使自己的行为具有意义。原来这条坎坷之路的设计并不是为了显示碧奴对于丈夫的深情,碧奴性格中的坚韧。情节的离奇、过程的曲折根本上是为了叙述自身展开的需要,其意义就在于演绎和证明了叙述者的想象力,显示了叙述者掌控叙述的技巧和才华,确证叙述者这一次重述的行为。作者在回答网友提问时说:“这个小说在我的观念中是一次创作……为什么不是改编呢,因为这部小说我提供的是民间传说未提供的那一部分,或者说重述重要的是叙述,而恰好以前的传说的版本它给出了结果,但是并没有提供精细的叙述。所以这部作品应该说是创作。”对于“精细的叙述”的展示就是叙述的动力,从而以对过程满满当当的铺展悬置有关情感、信念、“神性”等等意义层面的呈现。
认识了这一点,就有可能理解围绕这部小说一些评论意见之间巨大的分歧和矛盾。虽然具体意见有异,但大多都力图从中阐释一些“意义”的东西。然而在文本中那是一个被悬置的区域,评论者寻找的“意义”或者“主义”多是自己携入的,也就难免人言言殊了。不仅在评论者之间,在小说的宣传广告和小说文本之间也有错位。关于小说的一个广为散布的宣传是:“在《碧奴》中,苏童带我们回到了遥远的古代,以丰富的想象力重现了一幕幕令人惊心动魄的场景——为生存练就九种哭法、送寒衣前为自己举行葬礼、装女巫吓走顽童、被当作刺客示众街头、众青蛙共赴长城……小说中,碧奴的坚韧与忠贞击退了世俗的阴谋、人性的丑恶,这个在权势压迫下的底层女子以自己的痴情、善良在沧桑乱世中创造了一个神话般的传奇。”在凸显小说的奇幻之外,依然以“坚韧、忠贞”与“痴情、善良”来归纳女主角的品质,概括这个传奇的意义。然而在小说文本中“坚贞”已经被“坚持”的行为所替换,“痴情”更近似于愚钝和蒙昧。即使作者自己关于小说的阐释也会有矛盾。关于创作动机作者有时候这样说明:“通过《碧奴》画一个情感的梦,源于我的一种真正感动。我是在借助创作《碧奴》来重温现代社会一种久违的情感。其实我是在借助碧奴探讨一个人对另外一个人感情深,究竟能深到什么程度,一个人为另外一个人牺牲,又能够牺牲到什么程度?”⑧一个个体对于另一个体的情感、或者为另一个个体“牺牲”,都包含着一种主动的姿态,有着主体选择层面的内涵。然而这属于小说中那个被动的“情感动物”吗?有评论者意识到“反差”的存在:“苏童在刻划《碧奴》的人物的时候,他写了很多很意外的东西。比如说碧奴这个人是不可理喻的,是执拗的,她是愚笨的,是不懂事故的。他极力的强调和夸张碧奴这种不可理喻的特征,使最后哭倒长城,这种强烈的反差。我注意到人物性格之间的反差。”⑨这种种矛盾,不是源于文本的丰富性因而提供了解读的多义性,而是暴露了文本内在结构的特征:它对于泪水的渲染、过程的铺陈就是这一次建构神话努力的指向。或者说在这里叙述就是叙述的支撑,除此之外,它没有支点,无所凭依。
作者曾言:“孟姜女故事给我的启发,就是从世俗出发,一个普通的民间女子怎么成了一位神?她身上如何散发神性的光芒?……所以,在写这个民间传说的过程中,我完成了这样一个填空——从民间传说到神话,孟姜女从凡人到神的进程。或者说,我写作这篇小说的兴趣本质上是在这里。”⑩作者创作神话、塑造“女神”的愿望或目的是明确的,同时这里也表露了对于自己叙述能力的自信,也是对于叙述本身的信心,相信通过自己的重述已经将民间传说提升到神话,将女主人公由凡人提升为中国的哭泣之神。叙述既是建构的方式,同时也是建构的支撑或依托。也许因为爱情太俗套,因为历史太沉重,因为人性太复杂和阴郁,在让现实飞翔起来的努力中,作者更愿意凭依或者相信的只有自己的叙述,更相信自己“想象”、渲染、铺陈的能力,相信自己对于叙述本身的掌握。一切的痴情与善良、坚韧与忠贞的品质,一切痛苦与悲伤的深情,更愿意把它归结为是一种原始的本能,一种蒙昧状态的反应。可能的“神性的光芒”只在曾经的传说、远方的神话中。在小说中并非没有历史,没有现实,没有感情,但是它们都不是重述或者演绎这个古老传说的支撑。作者这一次的“重述神话”从创作动力上、在展开过程中更主要着意于操练或者演绎的是一个关于叙述、关于写作本身的神话,而与“孟姜女哭长城”的传说或者神话关系其实不大。横溢铺张的设计与渲染除了显示出作者叙述的自负,大概并不能说这就是想象力的飞翔,相反却展现了在传说与历史、传说与现实之间自由想象空间的局促。小说确实以泪水支撑了一个故事,但可能并没有支撑起一个新的神话;相反却映照出身处当代的我们某种无所依凭的处境,即使是在我们这个时代放飞的神话中。
注释:
①苏童:《碧奴——孟姜女哭长城的传说》,重庆出版社2006年版。
②陈祥蕉,王蔓霞:《重述神话:全球作家的一道“命题作文”》,《南方日报》2006年7月30日。
③苏童:《神话是飞翔的现实》,《上海文学》2006年第11期。
④⑨《〈碧奴〉:重述中国神话的独特声音》,《中国青年报》2006年9月18日。
⑤郭春林:《眼泪和爱的神话》,《文景》2006年第11期。
⑥参见刘亚军、汪炜《沉默四载〈碧奴〉出世》对于复旦大学主办的《碧奴》研讨会(2006年9月15日)的报道,载《文汇读书周报》2006年9月22日。
⑦参见吴雁:《苏童在〈碧奴〉里犯错》,《新民周刊》2006年9月13日。
⑧参见阎晶明:《存在的呼告 神话的变奏》,《中华读书报》2006年9月13日。
⑩陈福民在“苏童新作《碧奴》学术研讨会”上的发言,2006年9月1日于北京大学英杰交流中心举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