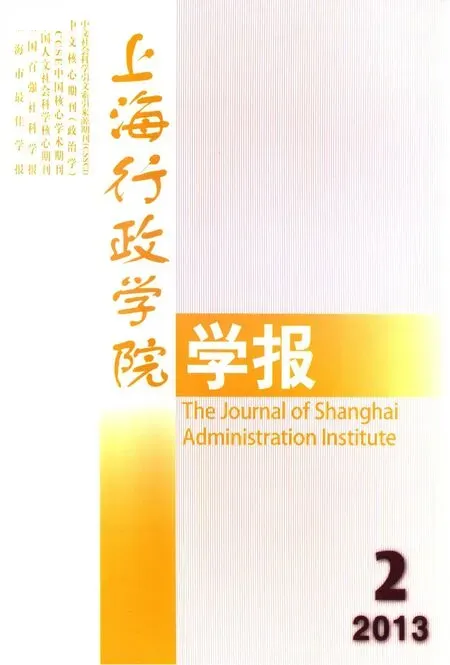我国粮食安全综合评价:1978-2010*
王国敏 卢婷婷 周庆元
(四川大学,成都 610064)
粮食安全历来是国家安全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基础性、公共性和战略性的特征。准确判断国家粮食安全的形势,客观分析粮食安全存在的风险,对于我国这样一个发展中的人口大国具有重要意义。构建科学合理的粮食安全评价体系并具体测评各阶段粮食安全的程度,是采取应对措施和制定政策的逻辑前提。本文试图提出一个涵盖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领域的粮食安全综合评价体系,并以此对中国1978-2010年的粮食安全状况进行测评,最后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一、文献回顾
联合国粮农组织(FAO)先后三次对粮食安全进行了定义,并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接受,其实质是使“所有人在任何时候都能享有充足的食物,满足健康生活的需要和喜好”。由此出发,国内外经济理论界和实际部门采用了多种方法,试图给出粮食安全的数量指标。
国际上具有代表性的方法有:(1)粮食安全系数,由1974年世界粮食大会提出,认为当年粮食储备超过17%即为粮食安全。(2)营养不良人口比重,由FAO提出,认为一国营养不良人口比重超过15%为不安全。(3)世界粮食安全委员会七指标法,综合考虑了消费、健康和营养等因素。(4)美国农业部问卷调查法,分为3大类18个问题,直接面向个人进行调查分析。(1)和(2)两种方法实际上属于单指标分析,易于操作和国际比较,但不能反映粮食安全问题的综合性和系统性。(3)和(4)更多关注的是“终端”,即个人消费环节,忽略了生产和分配环节,而且面向个人的调查,不可避免地带有主观因素的成分。
自1994年莱斯特·布朗发表《谁来养活中国》一文之后,国内掀起了粮食安全研究的热潮,并形成了一批关于粮食安全测评的研究成果。代表性的有:(1)四项指标简单平均法,采用粮食产量波动率、粮食储备率、粮食自给率和人均粮食占有量这四项指标,四项指标权重一致,总指标越大,表明粮食安全水平越高①。(2)食物保障可持续性评价指标体系,从农业生产及其资源生产效率、经济效益、资源利用率以及资源与环境质量构建食物安全指标体系②。(3)五项指标加权平均法,采用食物及膳食能量供求平衡指数、粮食生产波动指数、粮食储备—需求比率、粮食国际贸易依存度系数、粮食及食物市场价格稳定性各项指标得分值进行加权平均③。(4)四项指标加权平均安全系数法,采用人均占有粮食量、粮食总产量波动系数、粮食储备率和粮食进口率说明粮食安全,并使用加权平均法得出综合系数④。(5)生产、消费、流通和贸易综合指标体系,在给出各指标区间和取值基准的基础上,采用加权平均法得出了1978-2004年的粮食安全综合指数⑤。这些研究方法有可取之处,值得借鉴。但整体来看,国内学者的研究,更加偏重于供给,部分考虑到了消费和流通,但不约而同地忽略了分配环节。这显然没有很好地体现粮食安全综合性和系统性的特征,没有很好地回应粮食安全内涵演变的趋势,没有注重种粮主体的利益分配可能引发的粮食安全问题。此外,在指标权重的确定上,带有明显的主观色彩。
二、粮食安全综合评价指标体系的确定
粮食安全是一个复杂的系统,从整个国民经济系统来看,粮食安全涉及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等方方面面。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对社会生产的四个环节,即生产、分配、交换、消费之间的关系做了精辟的辩证分析,马克思指出,生产和消费具有直接的同一性;生产决定着消费的对象、水平和方式,为消费创造着动力;而消费则使生产行为和产品得以最终完成,同时也可以创造出新的劳动力和生产的内在动机与目的。产品的分配则处于生产和消费之间,受生产决定,对生产具有反作用。“分配的结构完全取决于生产的结构”⑥,随着分配的变动,相应地生产也会发生变动。交换则是作为以生产和分配为一方,以消费为另一方的中介要素,它受生产决定,并反作用于生产。“在社会再生产过程中,生产、分配、消费、交换是构成一个总循环的各个环节”,“一定的生产决定一定的消费、分配、交换和这些不同要素相互间的一定关系。当然,生产就其单方面形式来说也决定于其他要素”,“不同要素之间存在着相互作用”⑦。粮食产业也分为生产、分配、交换与消费四个环节,四个环节相互作用,是一个统一整体。从这个意义上讲,粮食安全就是粮食生产、分配、交换与消费四个环节的安全。
粮食风险存在于粮食系统的各个方面和环节,且各环节的风险程度有所差别,这就是说在一个国家的粮食安全体系内,个别环节安全程度较高,而个别环节安全程度较低,同时,随着时间的推移,各个环节的安全程度有可能发生变化。粮食系统不同环节上安全状况的不一致性,使我们很难对某一个国家粮食安全状况作出整体上的判断。为解决这个矛盾,我们引入了粮食安全系数这个综合指标,并将其分为三个层次。第一层是综合指标,代表粮食安全综合水平,以粮食安全综合指数表示。第二层是主体指标,代表粮食安全各个主要方面的水平,主体指标共四个,分别是生产环节安全指标、分配环节安全指标、交换环节安全指标和消费环节安全指标。第三层次是群体指标,反映各主体指标的基本内容,衡量粮食安全水平的各项具体指标共9项。根据以上三个层次设置的粮食安全评价指标体系框架如图所示。

粮食安全评价指标体系框架图
各项指标的经济含义和计算方法解释如下:
(一)生产环节安全指标
考虑粮食安全评价指标,首要的问题是粮食数量是否达到人们生存的基本需要。生产是分配、交换和消费的基础,是确保粮食安全最重要的环节,提高粮食综合生产能力是实现粮食安全的根本途径和治本之策。
1.人均粮食占有率X1
人均粮食占有率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一国的粮食安全水平,计算公式为:X1=Q/S。其中,X1为人均粮食占有率,S为粮食安全保障要求,Q为人均粮食占有量。不同历史阶段和条件下,粮食安全保障要求S的数量会有所差别。
FAO指出,如果一个国家人均粮食年占有量低于400公斤则可能会危及粮食安全。而胡守溢则进一步综合考虑了我国的人口比例、劳动人口的体力消耗程度、膳食营养标准、食物结构、营养热能关系以及实际消费习惯等因素,通过加权平均计算指出中国人均年占有粮食的最低安全保障为370公斤⑧。借鉴以上标准,我们采用人均占有粮食400公斤为安全线,人均占有粮食370公斤为基本安全线,人均占有粮食350公斤为温饱线。
2.粮食的自给率X2
粮食的自给率是在一定时期内一个国家或地区粮食总产量与粮食总消费量之比。计算公式为:

因各国国情差异较大,所以目前世界各国并没有就粮食自给率达成统一认识。国际上一般标准是:一国粮食自给率不小于90%为可以接受的粮食安全水平;若一国粮食自给率不小于95%,则基本上实现了自给。1996年颁布的《中国的粮食问题》白皮书,将我国的粮食自给率确定为95%及以上。
3.粮食生产波动系数X3
受自然环境、供求状况、经济政策等多重因素的影响,粮食生产往往在年度之间会出现波动。粮食生产波动常用粮食生产波动系数(或变异率)进行测算,其波动幅度的大小,反映着本期粮食产量的实际观察值对粮食长期趋势产量的偏离程度,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粮食生产的安全程度。
计算公式为:

具体可以采用回归法或五年平均法对趋势产量进行预测。一般来说,粮食生产波动系数越大,说明粮食总产偏离趋势产量越远,稳定性就越差,粮食安全水平也就越低;粮食生产波动系数越小,说明粮食总产偏离趋势产量的程度越小,稳定性就越高,粮食安全水平也就越高。
(二)分配环节安全指标
“保护粮食生产者的积极性,促进粮食生产”,全面调动粮食生产主体的积极性,是确保粮食安全的重要环节。这个环节通常是以往研究中忽略的方面,应当予以重视。
1.种粮成本收益率X4
成本利润率是反映盈利能力的重要指标。种粮成本收益率是粮食种植净利润与总成本之比,即种粮成本利润率=净利润/总成本。该指标越高,表明农户为取得利润而付出的代价越小,成本费用控制得越好,盈利能力越强。粮食安全问题直接表现为粮食过少,根源在于粮食过多时农民种粮收益没有得到很好保障。在1996年粮食丰收后,尽管国家启动保护价收购政策,但是农民的种粮收益仍从1996年开始逐年下滑,1996年亩均收益为146元,较1995年下降65元,下降31%,至2000年下跌为负值,种粮亏本。粮食总产因此连续五年下滑,至2003年跌至43070万吨,较1998年减少8160万吨,降幅达15.93%,粮食安全受到严重影响。因此,确保农民能获得种粮基本收益,是解决我国粮食生产问题的关键。根据专家预测并参照历史数据,种粮成本收益率保持在30%可以保障农民种粮的基本收益。
2.城乡收入差距X5
城乡收入差距=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农村居民纯收入。在经济发展的一定时期,客观上存在城乡收入差距问题。但若不能妥善处理,一方面会影响农民生产积极性,另一方面会造成粮食分配的不均匀。
(三)交换环节安全指标
交换是生产和消费的中介,交换效率及其稳定性直接影响粮食的可获得性,影响粮食安全的实现程度。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及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加快,国内外粮食市场对一个国家粮食安全影响将越来越大,特别是随着我国城镇化进程的加快,未来粮食市场建设与管理的重要性更加凸显。粮食管理体制健全、流通渠道通畅、供应量充足、物价稳定是确保粮食安全的重要方面。
1.粮价上涨率X6
粮食价格相对稳定是确保粮食供求平衡,从而实现粮食安全的一个基本条件。如果粮价过低,则会影响供给,抑制未来的粮食生产;如果粮价过高,则会影响需求,特别是降低贫困人口的购买能力。
由于粮食价格没有统一的数据,1978-2000年的数据采用粮食收购价格指数替代,2001-2010年的数据采用临时零售价格指数替代。
2.粮食储备率X7
粮食储备率是指粮食储备量占粮食消费量的比重,反映的是一国抵御粮食安全风险的能力。粮食储备率太低势必威胁粮食安全,而过高又会背负较高的储备成本,因此粮食储备率应保持恰当的比例。20世纪70年代联合国粮农组织曾提出,世界全部谷物储备至少要占世界谷物需求量的17-18%,其中5-6%为缓冲库存,12%为周转库存。联合国粮农组织以此作为确保全球粮食安全的最低储备标准号召世界各国采纳。
我国粮食储备率作为国家机密没有向外界公布准确的数字。据专家估计,我国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粮食储备率呈现逐年上升趋势,50年代年均14.6%,60年代年均13.3%,70年代年均14.7%,80年代年均20.2%,90年代年均34.8%,近年来粮食储备率在40%以上⑨。我国的储备率远高于FAO的标准。温家宝总理在2008年4月初曾公开表示,我国粮食库存充裕,约有1.5亿吨-2亿吨,按照5亿吨的消费总量,这样的库存比例高达30%~40%,是FAO建议比例17%-18%的2倍。
(四)消费环节安全指标
消费环节的安全更加注重粮食的“可获取性”,体现社会性,也是确保稳定的基本要求。要尽量消除地区间居民生活消费水平的差异,包括不同地区之间和城乡之间的差异,减少贫困人口的比例,最终实现全社会居民的粮食安全。
1.恩格尔系数X8
恩格尔系数反映了食品消费支出在总消费支出中的比例,可以用恩格尔系数来间接表示粮食消费在居民消费中的比例。
由于现有统计资料中只有城镇和农村居民分开的恩格尔系数,我们采取加权平均数来计算,计算公式为R=E1R1+E2R2,其中R1和R2分别指城乡居民的恩格尔系数,E1和E2分别指城乡居民的人口的比例。
2.贫困人口比重X9
粮食安全的内涵包括了确保所有人买得起所需的基本粮食,是否买得起粮食则主要受居民收入的影响。鉴于贫困与饥饿的伴生性,我们主要使用贫困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这一指标为依据来判断一国在多大程度上确保了居民买得起所需的基本粮食。
三、粮食安全状况的测评:1978-2010
(一)指标权重的确定
综合采用德尔菲法和层次分析法,确定主体指标和群体指标的权重。根据测评需要,运用德尔菲法原理,设计一套调查咨询表,邀请有关的实际工作者和专家,提供一些必要的定性分析资料,请专家就咨询表对各个指标的相对重要性打分。相对于粮食安全这一综合指标,对应下一层的四项主体指标,即生产环节安全指标、分配环节安全指标、交换环节安全指标和消费环节安全指标的相对重要程度。通过多轮函调,反复征询和修改,得到相对一致的四项主体指标的赋值。
为了便于定量化和采用同一个尺度,根据运筹学家T.L.Saaty提出的1-9及其倒数标度法,通过两两比较,得出咨询表中判断矩阵元素的值。然后,采用上述方法及层次分析法计算得到各个指标的权重。
相对于综合指标Z,根据专家意见构造出主体指标Y1-Y4各指标的比较判别矩阵。然后求出矩阵的最大特征根,进行一致性检验。逻辑一致性检验通过后,计算权重。计算结果如表所示:

Y1-Y4各指标的比较判别矩阵及权重
相对于各主体指标,由于群体指标数量较少,我们假设群体指标对相应的主体指标的影响效率是等同的。
由此,我们可以得出粮食安全综合评价指标的计算公式,即:
Z=0.4550Y1+0.1411Y2+0.1411Y3+0.2627Y4
其中:Y1=1/3X1+1/3X2+1/3X3
Y2=1/2X4+1/2X5
Y3=1/2X6+1/2X7
Y4=1/2X8+1/2X9
(二)指标取值区间和基准的确定
群体指标的数值,根据正负指标的不同性质,确定其取值区间和基准。这里有几种情况:一是群体指标的取值对于粮食安全的影响是单调的。人均粮食占有率、种粮成本收益率越大,越有利于粮食安全目标的实现。而城乡收入差距、综合恩格尔系数、贫困人口比重越小,粮食安全越有保障。二是群体指标的取值存在最优的区间,达不到或者超过相应的区间,都不利于粮食安全目标的实现。粮食自给率、粮食生产波动系数、粮价上涨率和粮食储备率属于此类指标。
根据上述理解与分析,我们可以确定各群体指标的取值和标准,如下表所示:

粮食安全群体指标取值区间和基准表
(三)粮食安全警区和警情的确定
从理论上说,粮食安全综合评价指数Z的指数越高,表明越安全,等于1时,为最优状态。如前所述,粮食安全涉及生产环节、分配环节、交换环节和消费环节等方方面面,它可能在某些环节上表现出很高的安全性,而在另外一些环节上表现出较低的安全性。粮食安全综合评价指数,可以帮助我们对一个国家粮食安全状况作出整体上的判断。为此,我们采用系统化的方法确定粮食安全的警区和警情(见下表),全面权衡考虑我国粮食安全的特征及变动规律。

粮食安全警区和警情表
(四)我国粮食安全状况的测评
首先,根据群体指标的分析,给出9个群体指标1978-2010年的实际数值,如下表所示:

1978-2010年粮食安全综合评价指标原始数据表
其次,对照“粮食安全群体指标取值区间和基准表”,得出各群体指标的标准值,然后,根据前述确定的权数计算得出粮食安全综合评价指数,并确定警情。如下表所示:

1978-2010年粮食安全综合评价指标标准值及粮食安全综合指数
根据上述计算分析,可以绘制1978-2010年粮食安全综合指数变化趋势图(见下图),进一步分析我国粮食安全演变的特征。

1978-2010年粮食安全综合指数变化趋势图
根据粮食安全综合评价指数的变化趋势,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第一,1978年以来,总体上我国粮食安全程度在不断提高,并逐渐趋于稳定。我国粮食安全整体上仍处于轻警状态,需要予以关注。一方面,目前我国不存在显性的粮食安全问题,另一方面,距离粮食完全安全状态仍有差距。1978-1979年平均为0.52,1980-1989年平均为0.63,1990-1999年平均为0.67,2000-2010年平均为0.71。粮食安全综合评价指数不断上升,粮食安全程度逐步提高。尤其是2005年以来,粮食安全综合评价指数趋于稳定,基本保持在0.75左右。
第二,粮食安全程度提高的过程中存在较为明显的波动,并非是单调递增,而是在波动中逐步提升。1978年以来,粮食安全程度的变动大致经过了4个周期:1978-1987年,粮食安全综合评价指数从1978年的0.56下降为1979年的0.48,然后再逐渐上升为1987年的0.71;1987-1998年,粮食安全综合评价指数从1987年的0.71下降为1989年的0.63,然后再上升为1998年的0.72;1998-2002年,粮食安全综合评价指数从1998年的0.72下降为2000年的0.62,然后再上升为2002年的0.77,同期达到历史最优状态;2002-2010年,粮食安全综合评价指数从2002年的0.77下降为2004年的0.68,之后上升为2005年的0.77,同时趋于稳定,基本保持在0.75左右。
第三,目前,对我国粮食安全影响程度最大的因素主要集中在分配和交换领域。具体来说,是种粮成本收益率、城乡收入差距和粮价上涨率这三个因素,这些因素可以在很大程度上说明粮食安全综合评价指数的变化。生产和消费领域的指标相对稳定,对粮食安全综合评价指数变化的影响较小。这提示我们,确保粮食安全需要统筹兼顾,考虑多方面因素,而当前需要调节的重点主要是分配和交换领域,尤其是分配领域。需要指出的是,虽然粮食生产连续四年稳定在5亿吨以上,但如果不能妥善解决分配和交换领域的问题,粮食增产是不可持续的。历史上的教训深刻说明了这个问题,1996年种粮成本收益率开始逐年下降,到2000年下跌为负值,与此同时,粮食总产连续五年下滑,粮食安全受到严重影响。
四、简要结论及政策建议
从粮食安全的综合性和系统性出发,构建了一个包括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的综合评价体系,并以此对我国1978-2010年的粮食安全状况进行了测评。结果表明,我国粮食安全水平在波动中不断提高,并逐渐趋于稳定,但仍处于轻度警情状态,需要加以关注。从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四个环节看,目前的症结主要集中在分配领域。我们建议要从初次分配和再分配的角度,处理好粮农与主产区、主销区和国家之间的关系,建立健全粮食增产与农民收增联动机制。
1.建立健全粮食市场定价机制和双向补贴机制,发挥市场对粮价的基础性调节作用
尽管粮食具有战略性意义,但粮食首先是商品,其价格应接受市场供求规律的调节,并通过价格再反作用于生产。然而就我国国内市场而言,粮价基本由中央政府确定,市场的自发调节作用甚微,使得价格这个市场信号难以反映我国粮食生产和需求的真实情况。因此,必须发挥市场对粮价的基础性调节作用,完善粮食市场定价机制。考虑到市场上粮价的波动会对粮农和消费者造成的影响,我们建议中央政府要以市场供求规律反映出的粮价为基准制定最低收购价,并采取双向补贴机制。当市场粮价较高时,为不影响居民的生活水平,政府应转向对购买粮食的居民,尤其是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居民进行适当补贴,而农民则按市场价格出售粮食;当市场粮价较低时,为保护粮农种粮积极性,政府应适当增加对农民的补贴力度。
2.完善国家种粮直接补贴政策,进一步调动种粮主体积极性
考虑到粮食的基础性、公共性和战略性,国家应建立种粮补贴逐年增长机制,加大用于补贴的财政支出;建立种粮面积与补贴额度梯度增加机制,加大对种粮大户的补贴力度,间接引导土地规模化经营;改善种粮直接补贴方式,在当前以承包土地面积为标准的基础上,增加“按农民出售商品粮数量进行补贴”的方式,把按承包土地面积补贴方式和按农民出售商品粮数量补贴方式相结合;改善“承包者得补贴、种粮者担风险”的现象,根据实际种地农民出售的粮量进行补贴,使种粮直接补贴资金真正补给种粮的农民,体现“谁种粮,谁受益”的基本原则。
3.创新粮食主销区对主产区的补偿机制,促进区域平衡发展
粮食安全具有公共性,这就要求集体成员都要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买单”,但目前粮食主销区在确保国家粮食安全上存在着明显的“搭便车”行为。为此,我们建议:第一,制定实施粮食主销区对粮食主产区的补偿机制,在经济发达的粮食主销区征收一定形式的粮食消费税,直接补贴给粮食主产区,以解决粮食主产区产粮越多包袱越重的悖论;也可利用粮食补贴税,建立奖励产粮大县的长效机制,使产粮大县真正享受到“以工补农”的政策实惠;第二,根据粮食主销区占用的耕地数量,从粮食主销区土地出让金之中收取10%-15%的补偿金,用于粮食主产区开发增补种粮耕地建设,以稳定国家的粮食种植总面积。
注释:
①朱泽:《中国粮食安全状况的实证研究》,《调研世界》1997年第3期。
②吕耀,谷树忠,楼惠新,陈屹松:《中国食物保障可持续性及其评价》,《中国农村经济》1999年第8期。
③马九杰,张象枢,顾海兵:《粮食安全衡量及预警指标体系研究》,《管理世界》2001年第1期。
④刘晓梅:《关于我国粮食安全评价指标体系的探讨》,《财贸经济》2004年第9期。
⑤高帆:《中国粮食安全的测度:一个指标体系》,《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2005年第12期。
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
⑦胡守溢:《国家粮食安全形势估计及成本分析》,《安徽农业科学》2003年第5期。
⑧程亨华,肖春阳:《中国粮食安全及其主要指标研究》,《财贸经济》2002年第1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