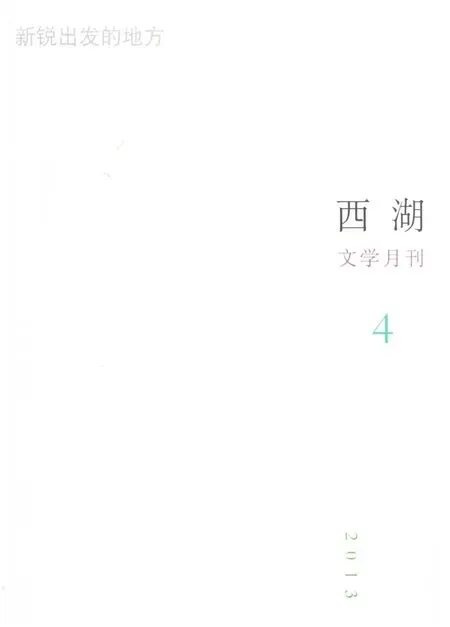纯真与世俗的辩证法——吕魁小说论
徐刚 徐勇
彰显青春气息,书写校园故事,这是一代代青年写作者必涉的主题。年轻的吕魁也未能免俗,尤其在他的创作之初。就像评论者所说的:“吕魁的小说多是关于青春的记录,呈现给读者的是一个洋溢着青春气息的世界,青春的气息如风如潮扑面而来,让人躲闪不及无法拒绝,只能欣然面对。”然而,吕魁的独特之处并不在此,与其说他是一个十足的青春写手,不如说他探讨得更多的是青春时代终结以后,如何面对庸俗的日常生活的问题。当然,其间也有那些“伟大的小人物”,连同他们顽强而卑微的小城故事。在这些故事的讲述之中,吕魁总会不失时机地拼接时下年轻人所熟知的现实元素,以此竭力将“80后”的生活经验落到实处。从QQ、“校内”、MSN等网络标志,到“三国杀”、“非诚勿扰”、超级女声等时尚因素,他以这样的方式拉近与读者之间的距离,将他们吸引到自己的故事中来。
一
还是从那篇 《小染》(《黄河》2005年第3期)开始吧!21岁的吕魁写出的这篇小说处女作,几乎奠定了他此后作品的基本母题:无处告别的飞扬青春和劈面相迎的庸俗现实,而这一切都是通过一位纯真、率性的女子,连同她为了生存牺牲一切的现实而展开,其间有暧昧有忧伤,而更多的则是成长如蜕的苦痛。我情愿将这个小说视为一位“纯真的守护者”对自己青春时代的缅怀和祭奠。小说热情追忆了一段洋溢着青春气息的校园故事,而在这个故事的最后,小说在一派“明媚的忧伤”之中,展现出青春的华美被耗尽之后所袒露的庸俗本质。小说从来自北京的姑娘小染在两个小城少年心中激起的涟漪开始讲起,那些被尘封的往事随着这青春期的萌动一点点被打开。此中,年少的纯情与率性的念想,飞扬的青春和刻骨的暗恋,也渐次呈现出来。然而一场突如其来的变故打破了这一切的平静,也就此宣告故事中人青春时代的终结。小说最后,就像所有不该重温的旧梦一样,他们的久别重逢也终究令人唏嘘喟叹。无论如何,面对一位无忧无虑的女孩日渐步入艰辛异常的生活,并且为了生存而牺牲一切,最后又被这个庸俗的社会所吞没的现实,任何关于青春的天真梦想都会在顷刻间土崩瓦解,这或许便是成长的代价。也是在这个意义上,就像论者所言的,“小染在小说中就是一个关于青春的象征,一个全新时代背景下关于青春的寓言。”
与《小染》相似,写于同一时期的《少年行》(《十月》2006年第5期)也将叙事的焦点聚集在中学时代。这个作品依稀让人想起姜文的电影《阳光灿烂的日子》,只不过王朔笔下那些文革时期打架、“拍婆子”的北京故事,被吕魁搬到了时间上更为晚近的小城里。如果说故事的主人公“我”,那个带着青春期的躁动与叛逆的小城男孩,像极了姜文电影中的男主角马小军,那么他那位兄长般的男人军伟,不就是耿乐扮演的刘忆苦吗?当然,还有米兰,她的角色则换成了同样漂亮神秘的林小丹。就此,主人公的叛逆,他对少年伙伴的追随,以及对女孩林小丹的爱慕,构成了整个故事的基本叙事单元。尽管小说最后,情感矛盾的激化势必将故事引向残酷的境地,但这种“平和的忧伤”却也体现出作者难得的真诚,而整个小说也演变为一曲喟叹青春逝去的哀歌。
吕魁的写作具有明显的成长小说的质地,他就像一位执着的孩子,不断地质询成人世界的逻辑,探讨世俗与纯真之间的刻骨矛盾。就像那篇《小染》,纯真的小染最终没能走进“我”的世界,她偏离了“我”所期待的人生轨迹,淹没在如蚁的人群之中,被世俗社会的滚滚红尘所吞噬。而另一篇小说《城市变奏曲》(《十月》2006年第5期),则在大学校园之外重述了这个纯真与世俗之间的矛盾故事。小说以诗人董三的故事开头,在虚晃一枪之后,迅速转向小说的主角,那个漂亮、热情、率真,甚至带着几分妖冶的女孩宁梓。她在音乐中忘我的摇摆,她的疯狂所散发的魅惑力,令我难以招架,她是“我”枯燥平庸的日常生活的一抹亮色。然而,这个酷爱漂泊、率性而为的女子,终究不会将自己固定在恒久的归宿中,她在这个世俗的社会里热情追逐着自己想要的一切。作者以言情的笔调,书写着让人怅然若失的爱恋。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请在四月叫醒我》(《黄河》2008年第1期)。这篇小说从网络聊天室的故事开始谈起,以证明这是不折不扣的“80后”生活经验。然而,故事本身却也显示出浓厚的“边缘人”的生活痕迹。小说主人公“我”在网上聊天,和一个妓女砍价,直到展开一次倾情投入的嫖娼之旅,只为展示“我”和小小,恩客与性工作者之间复杂暧昧的情感,事关纯真与世俗的辩证。小说之中,天真无邪的妓女小小,她为生活所迫而不得不遁入世俗的境遇,虽没有同类故事中“被侮辱被损害者”那般凄惨,却也具有十足的反思力度。对此,轻易用道德来评价,必然是轻率无理的。小说的惊人之处恰在于,在有情有义的妓女面前,知识者的卑劣令人感慨。作为文化人的“我”,学金融的大学生,以及小小那位当记者的前男友,在这位性工作者面前都显得如此渺小,而她对男人的轻信则更显其率真无邪。小说就是以这样的方式,让人重新思索纯真和世俗的真正本质。
二
吕魁笔下的女子大多具有超凡脱俗的魅力,她们热情似火、美艳动人,她们率性而为、敢爱敢恨,这些无与伦比的姑娘从天而降,突然闯进“我”的生活,给“我”平庸的生活带来亮色。然而在一番暧昧朦胧的爱恋之后,她们又无一例外地离“我”而去,去追逐更为“实在”的梦想。她们为了生存牺牲一切,最终却一败涂地,被这个物欲的社会所吞没。小染、宁梓莫不如此,而那位“莫塔”则更为典型。青春的故事就是这样令人唏嘘喟叹!
小说 《莫塔》(《人民文学》2009年第8期)可以算是不折不扣的80后的作品,年轻人追捧的校内网成了这个小说至关重要的媒介,而大段的网聊对话,也惊人地呈现了一代人的生活经验。尽管作者一次次地将莫塔比作那个叫做卡门的波西米亚女郎,但小说终究不是一篇让人领略异域风情的爱情传奇。就故事类型而言,毋宁说这是一个别样的“北漂”故事。学西班牙语的大一姑娘莫塔,是我在饭局上偶遇的兼职酒促女子。这位有着不幸童年的美丽女孩从千里之外的新疆来到北京,在这个艰难的城市独自谋生。她因物质的匮乏而努力追逐着金钱,甚至不惜出卖身体和灵魂。她甘当“富二代”情妇,最终也难逃被抛弃的命运。尽管生活曾一次次教育了她,让她明白这个世界根本没有童话,“与廉价的诺言相比,沉甸甸的物质更让我有安全感”,但她还是在这个物质的世界里一败涂地。“好女孩上天堂,坏女孩走四方”,这个冲着眼前的世界高喊“我爱你,北京”的执着女子,终究用自己的成长与伤痛,让人看清了世俗世界的真实面貌。
就像莫塔一样,那些渴望融入北京,但却悲哀地发现“我爱北京,北京却不爱我”这一人生真相的小人物,他们上下求索、漂泊无定的生存状态,在吕魁笔下被刻画得如此清晰。类似这种对物质追求、对城市迷恋的女子,在吕魁的小说中一再出现。《写篇小说登 〈大家〉》(《大家》2010年第1期)是一篇具有实验性质的小说,但也不自觉地流露出作者一贯的主题痕迹。就像小说开头所说的,“一切都从那个意外的电话开始”。因为和老汤的谈话,我开始写小说;因为和步小步的约定,我决心写篇小说登《大家》;为了给小说寻找素材,又接触到舞蹈妞;因为喜欢上舞蹈妞,又放弃了与步小步的感情。当然,知道自己要什么的舞蹈妞显然也看不上“我”这个不名一文的文学青年,于是小说最后又回到我和老汤的谈话,此时的他已经是美人在怀,纯文学的梦想早已抛到脑后。这个故事叙述结构严谨,设计精巧,一环接着一环,内容丰富,语言风趣,颇有可观之处。当然这样一来,也就不太能确定作者的意思是要探讨爱情的真谛,“爱只是爱,再伟大的爱情到头来也只是爱”;还是只想揭示世事的偶然,看看一个偶然导致另一个偶然,多米诺骨牌般的连锁反应是如何改变我原有生活轨迹的;抑或是想以反讽和调侃的语调书写一篇不同凡响的“元小说”。但是无论如何,这个作品还是包含了吕魁过往小说的一贯主题。令人心驰神往的舞蹈妞,依稀让人想起小染、莫塔这类为了个人奋斗而不断牺牲的“北漂”女子。
令人感到颇有意味的是,《写篇小说登〈大家〉》中的马山曾写了一篇题为《和美人告别》的小说,而与马山一样,现实中的吕魁真的有篇小说名为《和美人告别》(《山西文学》2010年第7期),尽管故事中并没有马山小说中那位念念不忘的舞蹈妞,但大体的思路却与之神似。小说吸收了校内网、超级女声、“艳照门”事件和金融危机等现实主义元素,故事却延续了吕魁一贯的模式,尤其是女性主人公的经历有些似曾相识。故事讲述的是校园男女的感情倾泻和闯荡社会之后的人生体悟。其主人公“唱歌妞”夏奈,是一位永远让人猜不透的奇女子,也是让“我”苦苦追求未果的物质主义女孩。她不在乎奋斗的方式和途径,她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留下来,活下去,甚至活得更好。她沉迷在世俗的追求中,其命运如何也可想而知。次贷危机之后,“完美男”毫无征兆地失踪,连同夏奈积攒多年的财富都被席卷一空。故事最后,夏奈有没有“像明知蝴蝶飞不过沧海那般继续热爱生活,相信明天”,我们并不知道;但小说结尾,她“打了一辆车,朝我的反方向开去”的画面定格带给人的淡淡忧伤却令人难以忘怀。
三
无论是小染、宁梓,还是莫塔、舞蹈妞,在吕魁笔下,她们并不是被否定的人物,相反,她们身上有一种与生活肉搏的力量和热情,有着令人迷醉的生命张力和青春活力。吕魁就是以这种“女性城市”的方式刻画这批“城市漂泊者”的形象的。正像作者所认同的作家汪曾祺先生所谈到的,“生活不是想象中那么好,也不是想象中那么坏”,因而这些女性漂泊者也无所谓善恶的道德评价。这种“性别构型”的思路,固然体现了作者在对个人奋斗的褒奖和道德主义的指责之间游移不定的状况,但在更大程度上却完美实践了“我所追求的不是深刻,而是和谐”的艺术追求。
正像吕魁一次次所说的,他的小说终是向“伟大的小人物”致敬,这些小人物不仅指的是莫塔等渴望留在城市的卑微女子,也包括那些游走在城市周边、不知何去何从的渺小的灵魂。《再见阿豪》(《百花洲》2010年第3期)是作者为数不多的没有写到女性形象的小说之一。故事里的阿豪是一个悲剧英雄,他像所有的“北漂”族一样,曾幻想着在北京这个繁华的首都打拼,但通过他那极尽艰辛却终感荒诞的故事,我们读出来的却是刻骨的悲凉。他从快递派送员开始,到贩卖盗版碟,再到饭店服务员、房产中介,最后终于难以为继,不得不在北京奥运会开幕这举世欢腾的时刻落寞地离开。在此,拥有鸿鹄之志的小人物,虽怀抱着“梦想照进现实”的决心,却终究无力展望那美好却终不可及的未来。小说的结尾不禁令人五味杂陈:阿豪和成千上万的人挤在北京西客站前的大屏幕看奥运开幕式,为那震撼、壮观、却终究不属于他的开幕式激动不已,在“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的虚幻想象中,为那个小女孩唱起的《歌唱祖国》而热泪盈眶。小人物承受着这个世界所强加的艰辛,却一厢情愿地妄图分享它的无上荣光,这是执着还是荒诞,是单纯抑或愚笨?小说最后,阿豪那暧昧不明的眼泪留给人们无尽的思考。
《浅生活》(《人民文学》2008 年第 12 期)也是一篇向“伟大的小人物”致敬的作品,这篇小说以旅行游记的方式饶有兴味地描写了主人公去婺源游玩的一路见闻,并以当地“摩的”司机老滕和小滕充当导游为线索,记述了这两个颇富意味的底层小人物。小说的可贵之处在于一改传统底层文学的俗套,将那些坚硬的现实深藏在小说朴素的叙述之中。写两位小人物谋生的艰难以及即将面临的生计风险,也并不回避他们的小狡黠。既不拔高他们的美德,也不回避他们的缺点,这便是带着生活底色的“伟大的小人物”。作品以毫不煽情的方式,呈现那些平淡无奇的生活,其情其景全无波澜,一如生活本身。
卑微的小人物和平淡的小城生活,一直是吕魁小说的主角。小说《信仰在空中飘扬》(《山西文学》2011年第1期)多少有些寓言的意味,它以财大气粗的高中同学老邢回乡投资,从而点燃整个县城的物质欲望为线索展开。然而随着金融危机的蔓延,老邢根本没有精力和实力继续投资,他最终的消失使“我”领略了人生如过山车似的大起大落,而在此之中,似乎只有平淡才是生活应有的底色。正如小说中的黑子所说的,“我和他这辈子注定没有发财命,只能在这熟悉到不能再熟悉的小县城里日复一日地过着单调、平淡但至少安全、踏实、还算快乐的日子。”由此亦可看出,在吕魁笔下,青春和理想的飞扬固然可贵,但现世的安稳和人生的平淡或许更加值得珍视。同样事关生活的价值选择,《火车要往哪里开》(《大家》2011年第1期)提出了一个严肃而认真的问题:火车要往哪里开?小说通过我在乡村女友牛红红与城市梦中情人徐菲菲之间价值选择的变化,来探讨城乡关系这一严峻的社会命题。小说不断地渲染乡下人牛红红的“土气”,这无疑也是“乡下人进城中”的惯常笔墨,而上海姑娘徐菲菲则体现出城市人的一贯嘴脸。当然,故事的结局早已注定,城市人的精明与算计,不过是想利用“我”对付第二天的考试而已,而小县城或乡下人的淳朴才是最为稳固的社会价值。小说曾饱含深情地回忆起少年时代“我”的乡村和县城生活:“那时候的我无忧无虑,并不知道上海在哪里,最大的乐趣是靠打零工积攒的钱去县城赶集,买几本武侠小说或是去录像厅看场枪战电影。”这样的城乡道德选择,以及所流露的“原初激情”式的乡村本位主义,无疑是极为传统的价值立场,但经由吕魁的朴素之笔写出却别有一番韵味。
四
吕魁近年来的小说呈现出较大的变化,《信仰在空中飘扬》、《火车要往哪里去》、《去乌兰巴托》等篇较之以前的作品,具有明显的区别。具体而言主要体现在,小说中女性的比重有所减少,而竭力在青春的故事之外,呈现出生活的丰富和复杂。比如他的那篇《所有的阳光扑向雪》(《文学界》2010年第10期),作为一篇“故事套故事”的小说,结构设计得比较精巧,这一点与那篇《写篇小说登〈大家〉》极其相似。通过网游通宵鏖战“三国杀”时认识的那位姑娘隋灵,依然像所有吕魁小说中的女主角一样,仿佛是突然之间从天而降,出现在人们的面前。小说写出了两个不同年代的人不同的生活方式,“一意孤行”的隋灵,依然在追求一些美好而疯狂的事情,这其中便包括“去一个陌生城市见一位陌生异性网友,和他共处一夜,并听他讲一个爱情故事”。而与隋灵不同,“我”,或者也包括武青青,都已充分领略了生活的庸俗。然而,无论是现实中的我,还是隋灵,抑或是老秦与武青青,“所有的阳光都扑向雪”,这也表明世间的爱情都具有殊途同归的结局:“再怎么缠绵悱恻,曲折动人,到头来无非就是你深深地爱着我,而我却渐渐地不再爱你。或者是你移情别恋爱上了他人,我仍在原地痴痴等你。……总而言之,理由有千百个,结局只有一种,在分手这件事情上,没人能免俗。”这其实也表明了吕魁小说一贯的主题,即人生飞扬与生活庸俗的辩证关系。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有评论者将它视为一篇“成长小说”,它见证的是“一个从青年到中年的故事”,“一个从激情走向平淡的故事”,“一个从诗意走向庸常的故事”,甚至是“一个从生到死的故事”。
这些成长的轨迹,从吕魁小说一个个创伤性的事件便可看出。吕魁笔下的青春往往终结于一起创伤性的事件,这也是人生的飞扬走向世俗与庸常的起点。比如《小染》中三个年轻人的离散源于一场濒死的殴斗;《少年行》的结尾,人物情感矛盾的激化将故事引向残酷境地。在《去乌兰巴托》(《文学界》2011年第11期)中,也是一场突如其来的杀戮,打破了三个年轻人去往乌兰巴托的计划。这篇小说的开头在墨县的季节上大做文章,夏季的游泳池和冬季的火锅,三个小城青年“子承父业,代代相传”,日复一日地重复着单调的生活,而聚会则成了可怖的日常生活必要的调剂。就像吕魁小说所惯常书写的那样,一位热情、漂亮的女子从天而降,成为了平庸生活的亮色。而去乌兰巴托,也是这群眺望梦想的小城青年追求别样生活的契机,然而一场突如其来的意外,使这卑微的梦想烟消云散。这些“创伤性事件”的意义,无疑在于使得浪漫的理想与坚硬的现实劈面相迎。然而,青春之后的故事该如何讲述?或许那飞扬的理想和激情终将化为泡影,而成长之路上的少男少女们也会像小染、莫塔,抑或吕魁小说中更多的主人公那样,在与现实短兵相接的过程中与生活达成妥协。自此,无忧无虑的青春时代宣告结束,生活本身也在青春终结之后显露出世俗的残酷面貌。吕魁的小说就是以这样的方式书写同龄人的当下境遇的,正如他所秉持“小说永远不会比生活精彩”的理念,他笔下那些纯真与世俗的辩证故事写得并不颓废悲观,而是心怀怜悯和同情。一切都极为自然,虽不深刻,但却和谐。当然,年轻的吕魁目前的作品还不多,所涉及的生活面也并不广阔,好在一切才刚开始,我们有理由对他的写作抱以期待。
注释:
①参见鲁顺民:《青春的书写与吟唱——读吕魁的中篇小说〈小染〉》,载于《黄河》2005年第3期。
②鲁顺民:《青春的书写与吟唱——读吕魁的中篇小说〈小染〉》,载于《黄河》2005年第3期。
③ 汪政、刘忠、李云雷:《爱情的存在方式与讲述爱情的方式——〈所有的阳光扑向雪〉三人谈》,载于《小说选刊》2010年第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