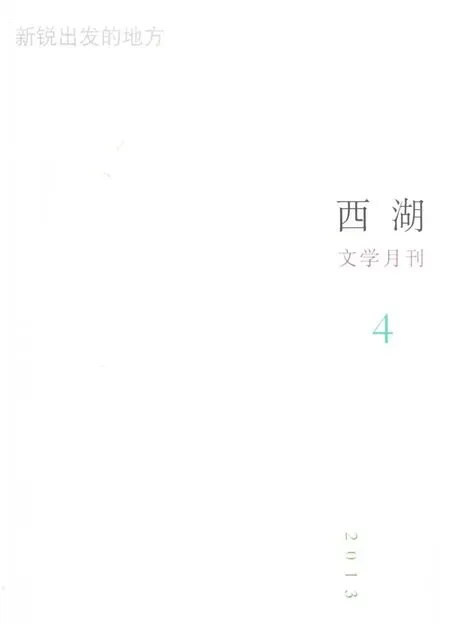诸林前
指尖
夜里下过雨,林子里湿扑扑的。在山上,湛蓝的天空仿佛伸手可及,而太阳的热量也发散得格外直接。某个停顿的瞬间,有烤着一盆炭火的感觉。到林子里,气温迅速下降。走一小段,鞋和裤腿上沾染上碎密的草木屑,加上露水,很快湿了。
枝柯稀疏处,阳光透过枝叶射照到草叶尖,晶莹剔透的露珠悬垂欲滴。鸟雀婉转的歌声传来,乱中有序,此起彼落,喧闹中有安静的余味,加上阳光斑斓,洒满林间草地,使林子明暗交加,宛如陷入迷境。
秋天,山上的松树、柏树、漆树、榆树、槐树、枫树、柳树、桦树、山杨浸淫了岁月漫长的痕迹,纷乱呈现,使山体变得厚,繁,杂,多,迷乱,醇厚,似七分醉意,稍不矜持,要疯癫的感觉。好在山是土石构成,人的臆想再好,亦不过虚妄。万物均遵循旧有的惯常。叶子们再狂野,也不过叶子的事。
山体色彩明艳,缤纷不绝,黄、红、褐、绿,种种随便涂饰,便是如画景色。上山入林,这感觉稍稍削减,黄是枯,红是碎,褐是烂,只有绿欣喜些。秋天的美,是掺杂了衰老和死亡的,是生命极处繁华的绝望。叶子带着虫洞,若一枚小破伞。一场战役,努力到败局,杀气和意气还在,生气却没了。有些落叶依旧完整青翠如初,梦中凋落,错失的顾盼,怀着绚烂的骄傲和霸道,落,亦有三分气势撑着。更多枯败的叶,被隔夜的雨浸湿,回忆加深颜面,暗褐着,枯竭着,消败着。
秋天的林子,虫蚁已无踪迹,狼籍不堪的枯色掩藏住一些真实的东西,比如,死亡。
一条小青蛇悠闲而来,拉着身下的枯叶,刺拉刺拉地响,后来,它遁到枯叶下,世界瞬间归位,安静如初。
自然界的存在都是有序的,连这遍地的死亡,都有生生不息的支撑和陪衬,没有一丝悲怆意味。
上午,树木的影子倒到西边,下午影子又把东边的树体遮盖。夏天,林子跟旋转的日光捉迷藏,无论阳光从哪个方向来,树林里都巧妙地保持着空间的阴暗、清凉,枝蔓横陈,使人贪恋热爱。
在林子里缓慢地走,跨过纷乱的草木和荆棘丛,蝴蝶随行左右,头上肩上,身前身后,白粉蝶树粉蝶灰蝶蓝灰蝶铜色蝶燕灰蝶长尾弄蝶鸾褐弄蝶蛱蝶王斑蝶们,成群结队,伸手可探,可得。拿两张白纸,随便一扑,纸间便有一双忽闪的翅膀,轻轻揭开,它鼓鼓的小肚子,绚烂的图案,触角伸长,像在找寻出口。终是不忍,放开,它便展开翅膀,飞走,指上徒留一捻白粉。
蝴蝶是不记仇的。
林子里,因这些纷飞的蝶,使人间充满幻想。传说树叶是蝴蝶的前世。在林中,有时分不清树叶和蝴蝶。山鸡清脆的鸣叫掠过树稍,惊得人猛抬头,却是亮晃晃的日光,眼前一片片黑斑,若无数羽毛落下。
山上的山菊花败酱草桔梗芒草胡枝子野姜花藿香蓟秋牡丹们开在任何可能的地方,石片下,石头间,道路中央,树体中,乱草和荆棘丛中,乃至一些肉眼无法探到的角落里,怎样的行走都能遇见一抹惊艳。人生便似走一回林中小道,谁都无法设想下一步上帝会给你怎样的遇见,喜的,痴的,心动的,难以推测。
到人走得气喘吁吁,汗流浃背,蚊子们便上场了。它们得到了怎样的讯息呢,或者不过本能,从停歇处蓦然飞来,叮在我们的皮肤上。身上马上出现一个粉团的疙瘩,这点缀让他有了几分滑稽的可爱。民间传说,甜皮苦命。连蚊子、跳蚤这些嗜血的昆虫们,都喜欢停留的肉体,怎么不是有情人?蚊子贪婪放肆咬嗜,留下众多印痕,乘兴而去。而发痒的滋味和痕迹,几天之后,会消失,你的身体看起来,完好如初。
在夏天的林子里走一遭,身上会留下浅浅一层白粉,几粒粉红的印痕,宛如经历过一场爱情,莫名的回忆在某个深夜突然出现,飞舞在黑暗中,发出轻微的响动。
林子里有成群的兔子,灰色,红眼,长须,后腿比前腿长,跑起来跟风差不多快。
冬天雪后,它从某处出来,穿梭在林子中间,或蹲在雪地里,找一些松果或更小动物的尸体充饥。深色的身体在白色的背景下,格外醒目。
前些年,有人在冬天频繁进山,野兔是最好最多的猎物。
到春天下种,野兔捱了一冬的饥寒,忍不住从山里跑出来,到田里刨种子吃。玉米、谷子、土豆,只要是种子,它都能灵敏地嗅到它们。很多人家在田里设了机关,它们稍不留神就会被机关暗杀,成为人家的锅中美味。
将肉连骨剁成块,放姜、葱、蒜、花椒、大料、辣角、食盐沙锅炖之入腹。皮毛做成护膝护腕,或用针线连在一处,制成褥子,铺在热炕上,渡好几十个冬天。
野兔肉是很好吃的。
山西某地特色食品为兔头。兔头上盘,少圆润态,头骨清晰,嘴略尖,眼睛多睁着,死灰死灰的。众人均啖之,但无人评说,滋味好坏,各人自知。眼眼相对,生死相望,今我盘中有你,谁能确保明天没有翻云覆雨手,令你盘中有我?世间物种,生生相安,其实才是大道。但物种之间互相残杀,互为食物,这种自然恒定的规律,无物能违。
护林人枪法好,专打其腿,擒之毛发完存。待其歇气,将内脏挖出,以丝棉或塑料回填,肚下拿针线缝之,眼里塞一玻璃珠,放在标本室里,野兔的魂散了,皮囊亦炯炯有神地注视着窗外。窗外流光涌青山,风云无限。
早年的打猎人喜好在野兔出入频繁期持枪捕之。近年,封山禁牧,护林防火,上山路关卡重重,人自觉,少有人入山猎物。
人与山,与诸树,与诸物,与诸神,均相安无事。
惊奇的是,野兔数量亦随之减少。是迁徙?是死灭?世界博大,瞬间万变,种种猜测,皆无果。
往年本地诗人有“风声洞口林涛歌”之句,好歹不究,只说这一腔热爱。诗中提及的修行洞在庙2公里处,传神仙于此修行过,并终成正果。
洞在北山,峭崖,周围树丛茂密,荆棘遍布,阳光直射,树叶隐隐散着水光。
沿直立的小道爬上去,洞内窄不容身。神修行的痕迹已了然无痕。
后当地人劈山轧斩石,塑神像,披红绸,燃香祭拜。并维修栈道,砌99级台阶。
通往神的路其实是无极限的。现在容易了些,复感觉凡人的抵达,太过简单些。
身边人跪下。祥云浮现,神气冲天。
扭身向着苍山,郁郁葱葱,层层叠叠,众色相杂,深浅不一。久了,倒感觉暖洋洋的倦意,若归乡土之地,说不出的妥贴可意。坐下。地上是青石,栏杆是雕花,壁石上刻着花鸟,一派现代气息。远不如这一山的树木好看,有意味。
极目,群山延绵不绝。山连着山,水连着水,所谓人间,怕也不过山河两字。
神仙在洞内,日日对着这山河大地,几百年,修着风调雨顺,平安泰然。
一直顺着昏暗或明亮的林子朝东走下去的第一个村子,有个好听的名字:麻叶水。风一摇,崭绿的、阔大的叶子上掉下一滴水,像珍宝。山的珍宝,神的珍宝。
这个自然村被树林包裹得严严实实,已从地图上永远消失,无人居住。
像其他被抛弃的村子一样,院子里篙草密布,长得一人多高,家家门户紧闭。树上牵着的晾衣绳已烂掉,两截各在各树上,风一来,无力地摇摆几下。
土砌的猪圈,狗窝,鸡窝都空了。生锈的鸟笼被挂在铁架子上。猪圈里,满是秸秆,腐烂的一头结着黑绣。
一件深色的衣服上面沾着厚厚的尘土,衣角被石头压着。
房子是石砌的窑洞,十几孔的样子,窗户上没玻璃,窗纸早被风吹得破破烂烂,“卐”字柳木窗棂,黑洞洞的小窟窿,一个个大大的句号。
门上,锁生着锈,门缝开得倒大,似谁故意推开。探头望去,土炕自中央塌陷下去,几个大瓮七零八落地摆放在地上,有的倒了,倒下的口沿边,积着厚厚的土。
一切都表明日子曾经多么红火过。
黄土路,人走上去,嘣嘣的响,像水滴从叶子上落下。
人间是一场流水宴,你来我往,再热闹,再留恋,都要散去。
麻叶水的人,在另外的地方,亦愿活得快乐,幸福。
林子里有种大鸟,通体黢黑,光下泛紫,外表贵雅,喙长而艳红,爪呈油绿色,鸣声沙哑,高。本地人称:红嘴鸟。
此鸟身大,嘶声不佳。传其一旦养成,随叫随到,能看家护院,忠心无比。所以颇受人喜爱。
夏天,是红嘴鸟的繁殖期。
红嘴鸟多居于高处阴暗湿润的洞穴。
刚孵出的小鸟,无进食能力,必得鸟妈妈觅来食物,以喙相予,方能活命。
在白天,鸟妈妈常将幼鸟置于巢内,独自觅食。
小鸟进食少,饥饿感频发,嘶哑的喊声不断。
入林,走大约两里多,方贴进山壁,山壁呈褐黄,岩层岫衍,抬眼,日照当空,眼前便漆黑一团。林中无风,鸟声喧闹,闷热无比。某人脱衣裸行,一副彪悍模样。众沉默前行,全神贯注聆听鸟音,良久,走得热汗淋漓,喘声吁吁,都未有一二鸟音。复提议穿荆棘林向上,直抵鸟可能藏身处。遂往。
爬行更是艰难。转忽,裸行之人遍体鳞伤,好不可怜。
上到半山,四周树木环绕,都是近造的新油松,绿郁郁的喜色,加带着人工的痕迹。便知,错过了鸟巢。
错过是人生常态。最好的时光,最好的年龄,最好的机会,亦要错过对的人,对的事。站在山腰,相顾无言,安静如树。
红嘴鸟,可能是相思鸟,白文鸟,鷭。其中鷭的可能性最大。鷭,形似鸡,背羽暗青灰色,腹面灰黑色,腹部中央灰白色,脚暗绿色。常栖河湖近旁。善游泳,以昆虫﹑鱼贝为食。头﹑颈具有角质裸出部分,称为骨顶,俗称白骨顶的为大鷭,红骨顶的为小鷭。
另:书上说的一种古鸟。
沿林路向北,一片古树群。山木多蓊郁,年年新植,但到底经不得枯、旱、火这些自然中难避的灾,生生死死间留存的一片古木群,使山在珍贵之上多了几分凝重。古木都是松,油松,高几十尺,粗两搂有余,都是一两百年的光景,仰望,树树直插云霄,若梯子般,上了半天。古物从来是通灵的。传某年,山间大火,烧了三天三夜,山上的林子都烧光了,连土都黑了,飞的、跑的、窜的、爬的,所有生物都被烧得面目全非,整座山,只余这一洼古木。
古木群围裹小庙,庙内有正殿三间,山门一间,石洞三眼,禅房九间,保存尚好。新新旧旧的痕迹涂抹在一起,合成一个大院子,院子砖石相砌,走上去,悄无声息。主殿里有旧壁画,画里车马人物线条清晰,文革时白灰刷过,后来工匠翻新,到底,亦未使古旧艺术泛出光芒,稍留意,便能看到哆嗦的痕迹。与神交接,人的恐惧总多于敬畏。神像堂而皇之新塑,多少也说得过去。
院里一株漆树,老得佝偻着身子,颤巍巍的,枝条都弯曲着,但主杆粗壮,纵裂,坚硬如铁。春夏绿荫遮地,枝条有乳白色漆液,开小花,呈淡黄绿色。结核果扁肾形,淡黄色,光滑。到10月,果熟,叶子开始泛黄至红。整个庙院,半天的霞红,分不清自天上还是庙里。
因之汁液有毒,可引起皮肤过敏,许多人都恐近其身,被人们称为神树。跟庙里的新神一样,披红挂绿,接受供奉。
庙北大石壁下,藏有一泉,泉口小窄,呈矩形,泉内水流不歇,有碑记载,此泉已存世几百载,名龙泉,泉水甜爽宜人,又名神泉。看林人说,建庙时的水都来自泉内,平时洗刷,浇灌,饮用,均来自此泉水。泉内有一线痕,水不溢不退,端端定在此痕上。想来真是神仙地界,古木,古庙,古泉,还有什么是肉眼无见的呢?
周遭无风,静若陷于密处。仰望,日西斜,古松渐墨,愈发肃穆。漆树泛了黄,叶子落了老砖的缝隙里,一些碎碎种子模样的东西,忽隐忽现。
往年冬天入庙小住。两个看林人匀一间禅房于我。屋子不大,暗,土胚房,土炕,炕上有窗,窗上一片模糊的小玻璃,能望见外面的景色:庙宇深红的后墙上,隐约暗色的污迹,想是风雨岁月无意的残留。冬天的古木群,愈发沉稳,黑绿而直耸的枝条,被玻璃框切段。想象中,一些神仙从此上下,出入人间天地。
下午,把柴薪从院里抱回来,自己烧火,先拿细枝用火点燃,放到火洞,然后慢慢地加柴,从细到粗,从疏到密,渐渐地,火大起来,半屋子的火光,烟雾散去,屋子里只剩下散发着松香的烟味。
晚上睡下,漆黑一团。耳朵里全是涛声,一波一波,滚滚来,滚滚去,人像在大海上漂移。偶尔有猫头鹰的叫声,仿佛就在头顶,地下便有响动。早上起来,晚间吃剩的瓜子撒了一地。
门帘是粗布做的,厚,沉,掀开出来,便看到细雪刚落,一粒一粒真真切切。山里天气,从来都是多变的。赵师傅说。小厨房里煮一锅粥,里面放了豆子、小米和南瓜,热气窜出门来,跟雪粒们合在一起,白茫茫一片。
雪沾在漆树的干枝上,一些粘住,一些落下堆到树根。一只鸟站在雪地里,东看看,西看看,又摇摆着走几步,不惧人。远处,灰蒙蒙的天,松林里雾气氤氲 ,似大口大口的呼吸,隐约有响动。
至午,山上披了一袭若隐若现的纱,天放晴了。整个林子被冬天的太阳拥抱着,却没有温度。直到起风,风声雷动,雪粒四扬,天地迷濛 。山上的树枝大幅度地摇摆,只有古木淡定如常,不摇不摆,却抖落了满身的雪意。
庙院里的雪厚了,晶莹剔透,若秘藏。
此间天气,深山,热炕,雪景,最宜猎一只野物,温一壶淡酒,相对畅饮,醉卧。岂不妙哉。
抬头,见廊下有蛛网,蛛已无迹,网依结实。一枚黑色的尸体被牢牢锁着。
正殿立有石碑6通,其中5通刻满功德人的名字,小,密密麻麻。剩一碑有记载:明洪武年间,王逃难至此地,见山上林荫密布,山鸟众多,人迹廖廖,遂居。
关于号希默的王,经过怎样的磨难,或造反,或冤屈,或躲避,或求全,如何逃于此山,隐度山中岁月,再无片纸可证。
古木的树叶在秋天大把大把地落,若一位逐老之人,眼睁睁观着自己茂密的华发,在日日相近的晨昏,随时间一根根砸到地上。大珠小珠落玉盘啊,这千古妙句,却原来非喻琴音,亦非雨滴,它竟是时间的珠,参差落下,溅起的回声充满空洞和哀伤的味道。时间粉碎了记忆。
断流的溪水,山谷的皱纹,横亘在山间,充满岁月的风沙和时间的尸首。鸟从头顶飞过。漫山红叶繁茂,密匝匝的,像一句话说出来,因无人倾听,而化着一堆落寞,涌着,漫着,眼看就要衰败凋落,却一直守口如瓶。长了新叶,褪了旧叶,淋了雨,挂了霜,依旧面色安然,活着,藏着。
如果泉水能证明王存在的事实。但又有些牵强,泉水已经不是几百年前的泉水了,它被冠以另一个与王无关的名字,也活了好久。想来,这是别人的王的泉。
壁画上贴满与王无关的故事,男的、女的、跑的、奔的、坐的、睡的、骑马的、牵驴的、喂鸡的、赶羊的。生命真是繁华啊,每个朝代,每天,每个人的一生之中,都要经历如此众多的事件,在这些事件中,人扮演着各种各样的角色,并用合理或者不合理的方式实现自己私己的愿望。怎样的一生才算圆满,从没有人能求证出这个简单的命题。门扇的缝隙中射进一缕缕暖黄的光线,照在记载王的石碑上,那上面,沉默的王冰冷,布满尘世的灰,在满山的红光中,暗淡如夜。
王死了。
世上的所有最终会停止呼吸,然后腐烂,成土,成泥,跟脚下的落叶一道,成为河沟里地被物层。王在几百年前,在最下面,跟许多虫豸的尸骨、尘土、叶泥们搅在一起,为污淤,结块,石化,坚硬如铁。我在浮世,烂着,腐着,死着。
风把更多的叶子带来,无数的蝶,盘旋飘舞在半空中,光线使它们纤细,薄透,经络分明,轻盈,欢喜,从容,寂静。
这是王的国。曾是,永是。
荆棘和野草,连带这满山的老树新木,在春天,顶着满身尘灰,却蓬蓬勃勃,像一伙流浪的小孩,面上有被怜的意味,深处却快活无人能及。越往山上走,林子越稀疏,越寡弱。山顶暸望台,两层小楼,外观颇好。暸望台旁一孤松,细瘦歪斜的树体,顶着满满的松盖。伸手去触,松针扑簌簌掉了一地。
站在树下,俯瞰四周,苍茫一片。春寒料峭,山顶感受最深。山与天,天与地,灰蒙蒙地连接在一起。北方春天,绿意来得缓慢,最好的,还是山。
世间的绿,从这山上一泼泼洒出去,洇出去,成点,成线,成川,成河。
风声穿耳过,若惊涛骇浪来。草浪沿着山体一波一波卷,波波向上,翻涌着,推进着,似要到眼前,却又齐刷刷退后了,一浪比一浪低,低到了极处。得得失失,枯枯荣荣,来来往往,欣喜之中掺搅遗憾。所谓圆满,其实也不过是无数缺憾的对接吧。
群山起伏,绵延伸展,山河大地,宽广无边。
山上,林中,蕴涵多少鲜为人知的秘密,它们是否正在时光中默默熄灭?默默生发呢?身边镜头,正窥着我。
人间景物,人间次序,人间情意,真让人不胜慨叹,却又无言以对。
赵师傅五十多岁,头发花白,脸色黝黑,个头中等,是国营林场的正式职工,在山上,工作了十余年。
他跟高师傅两个人,一个住在庙里,一个住在嘹望台。庙里低,稍静些。台上高,常年四季风声不歇,千军万马,千刀万戈,时间之中,人眼所看不见的争斗连绵不绝。赵师傅熟悉山里的一切,从某地,某坡,某崖,某村,到某树,某物,乃至哪个岩下藏有鸟窝蜂巢都一清二楚。说起来,三天三夜也说不完。人渐老着,心渐静着,一切痕迹便也缠缠绵绵,时光难以磨灭。
防火期,两人都搬到台上,日夜监控着境内8万亩国有林的安全。熬过冬春,熬到入夏,方长长地歇口气。推开门,站在山顶,山上隐隐的绿气映着两个人熬红了的眼睛,风一吹,头发乱舞,泪落下。
在他们,更好的时光是雨雪天。
两人或独自一人温一壶酒,坐在石桌前,就着山里的食物。小鸡炖蘑菇的香味在鼻息中飘荡。鸡是山鸡,蘑菇是松下野味,味道都重,炖在一起,便有了异于常态下的浓郁。
窗外松林静谧,偶尔有山鸡的喊叫,回声淡下去的时候,月亮升起。
林子里的夜晚,一草一木都有灵气,古木巍然不动,枝条上,似经工匠雕刻过,一丝一缕,舒展硬朗。
山峰被月色划出一条温柔敦厚的线条,柔软如水。
有神的世界,总是如此吧,安然的,美好的,穆清且可爱。教人向往,留恋。
月亮尚未落下,日头已早早跳出来,天空中,便出现两个圆球,互相对视,然后,一个越来越白,越来越淡,而另一个则恰恰相反。
一些又回到现实的世界中,昨夜变得恍惚若幻,似真非真。
山里人,枕着月光入睡,又在月光淡去的时候醒来。阴阳协调,所以身体好,活得久,年岁大。
在山里,吃一顿野味,喝一壶淡茶,做一回短梦,真是神仙日子。
早春,粉艳艳的山桃花在山上浮浮地飘了一层,好像邻家女孩吹出的泡泡。要是风来,真担心把它们刮跑呢。
山体在春天是最难看的,干硬,黑,嶙嶙峋峋,带了几分狰狞气,又裹了尘灰,不洁之感。枝条们也一样,人要靠上去,心里总怕沾了灰土。
于是有了桃花。
大自然是世上最好的画师,它把色彩搭配得艳而不俗,香而不腻。
赏花人冒着寒风成群结队地来,站在山顶喊叫,坐在山坡上沉默,拿着相机,左一张右一张拍个没够,或者在心里,上上下下搜寻有关桃花的诗句。风把人的嘴唇都吹裂了,心里那点说不出的感动都变得干巴巴的。
但没有人到树林里走一遭。
树林显得很冷漠,寂寥,空旷。树下的暗影里,依旧残留着暗冰,阳光偶尔闪过,射出一道亮光。宛如神留下的痕迹。
小道上堆满上年的落叶,干透了,摸上去,纸一样脆,一用力,它就碎了。
山上很少有梨花,白的,像雪一样的颜色。
早几年来山里,走了半座山也未找着一树梨花,趴在大石头上照了一张像,仿佛一个失意人更深的失意。
梨树是家养的树。村里家家有梨树。到了夏天,小孩偷偷摘了青果吃。山桃介于花与树之间,是独属山的,有灼目的花,果很少拿来食。倒填了山的某种空缺。
或者它就是用来点缀北方的春天的吧,让人间的第一缕春风顺着它溢漫开去,从此拉开四季的序幕。
桃开三月,到四月就开始谢了。五月,万树皆生机勃勃,灵动无比。全绿以后,粉色,这种有点小气的颜色便彻底被淹没了。
山桃结了青果,鸟雀来了,虫子来了,风一摇,落一地。也没人管。山上其他花开了,蜜蜂啊,蝴蝶的也多起来。天蓝得教人陶醉。落到地下的青果子,烂了还是残了,抑或被某物食了?或许更多的成了山里的种子?
还真是。
但那也是几年、十几年以后的事了。
后记:诸山,境内山峦起伏,形态各异,平均海拔均在1000米以上,主峰海拔为1467米。山体的母岩以白云质灰岩、灰岩为主,地质结构较为坚固。土壤以褐土为主,另有沙土黏土。境内有天然油松林,天然杨桦、阔叶混交林,人工油松纯林,人工油松、落叶松混交林等;主要树种有油松、侧柏、桦树、山杨、栎类等;灌木种类有绣线菊、黄刺梅、沙棘、毛榛、忍冬、六道木、黄栌、蚂蚱腿子等,草本植物有白草、苔草、铁杆蒿、白头翁、尖草等。野生动物有五十多种,有土豹、狍子、狐狸、野兔、石鸡、野鸡、田鼠、鹰、雉、百灵、云雀等。有昆虫一百六十多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