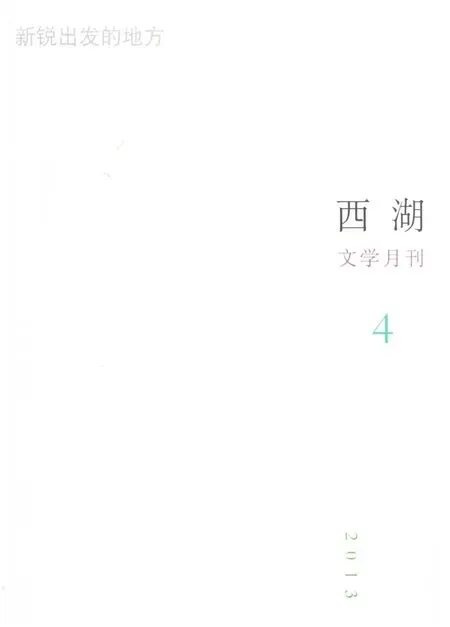自传与公传:一九七二(三)
董学仁
野人离不开人间
有些事情,淹没在互联网的深处,没有耐心查不到。
我想查证一件事情发生的年代,昨天就没查到。
据说是在欧洲某地建楼,挖地基时发现了二战时德国人的一个军需仓库,里面竟然有个活着的纳粹士兵。仓库的大门被炮弹炸毁后,他一个人封在里面,不知道战争结束了几十年,但他有足够的水、食物和衣物,每天洗脸,经常洗澡,按时擦拭枪支,穿着军装站岗。他让我想到,对一个人来说,既然规定了士兵的身份,不知道战争结束,就得以士兵的姿态站岗,完成自己的职责;对作家来说也是一样,既然规定了作家的身份,当世界还没有变好,就得以作家的姿态写作,坚守自己的良知。
那件事情发生在互联网出现之前,大概是1970年代。几十年前我读到关于它的描述,具体时间被我忘了。
在互联网上容易查到的,是1972年,关岛的两个猎人,捕获了一个形似野人的日本士兵。
他的部队被消灭了,只剩他一个人,躲在岛上的丛林深处。他甚至不知道战争已经结束,日本战败投降,海陆空部队都被解散。在那个岛上,他练就了捕捉老鼠、蛇和青蛙的本领,穿树皮,住洞穴,独自在野外生存了二十八年。如果不是已经到了五十六七岁,体力不如先前,那两个猎人可能捉不到他。回到日本,他被当成了英雄,作为一个特例,补发了二十八年间拖欠的军饷,一点不少,可能还加上利息。
他生于1915年,死于1997年,活了八十二岁。
让我感兴趣的,大概有两点。一是人的心理容易调整。远离人间社会二十八年之久,仅仅做了八十二天的心理调整,他就能够适应现代人的社会生活。二是人的态度可以改变。他回到日本对媒体的第一句话是“我回来了。很惭愧,我活着回来了”。那时的他,还担心日本政府按照对待战场逃兵的方式处死自己。到了1992年,知道日本自卫队要开向海湾的消息时,他已经有了对战争的一些觉悟,对媒体表示自己的看法:“战争,总是使身份最低下的人,付出巨大的牺牲。”
他不是最后一个“皇军士兵”。
1974年底,印度尼西亚莫罗泰岛。村民发现了一个赤身裸体、满头长发的“野人”在原始森林中身轻如猿,攀岩上树如履平地。地方当局闻讯后立即派人搜索,经数日围捕,终于在密林深处的树巢中将他抓获。经耐心盘查、询问,并给他食物、衣服,这个“野人”终于开口说话——令人惊讶的是他说汉语,原来是个中国人。
他 1919年生于台湾,1943年被日军强征入伍,同年被派往印尼参加太平洋战争,1945年3月被列入战地失踪者名单。此后三十年间,世上的一切变化他都一无所知,一个人藏匿于热带丛林,靠采集野果、草药和捕捉林中小动物生存,过着原始人一般的生活。
我比较羡慕的是他的意志力。生存本能,加上对妻儿的思念,使他顽强地活了下来,在与世隔绝的密林深处,孤寂地度过了三十年,终于活到了妻儿重逢的时刻。
那时他眼睛大睁,口唇颤抖,久久说不出话来——他一遍遍回忆的,是离家时为他送行的年轻妻子和怀抱中的婴儿,那种形象深入心中,忽然就变了,变成了眼前这老妇人和她身边的青年。
匆匆浏览一下,在互联网上没有看到他去世的信息。他可能还活着,快要一百岁了。我希望他的妻子也活着,他们要多活三十年,把丛林里失散的三十年补回来。
历史有过记载,最早进入深山的中国人,出现于公元之前,是一位很有影响的人士。他躲到山里的时候,战乱已经结束了,新政府请他下山,还派人放火烧那座山,以为他被烟熏得受不了,就会走到山下。但他宁可一死,也不做新朝的官员。
这件事感动了中国,于是把他抱在树上烧死的日子,叫做寒食节。两千多年里,每当寒食节到来,全国百姓都不升火烧饭,仅仅吃前一天准备的食物。
我读小学时还有寒食节呢,就在清明前一天。北方的冰雪没有融化,天空中吹过寒冷的风。但我们宁可咬嚼着又冷又硬的食物,也不去升火,怕的是烟火缭绕,会让那个人在天英灵回想起山火烧起时的痛楚。
文化大革命一来,传统文化和现代文明都成了敌人,延续了几千年的寒食节,终于不见了。现在的孩子们,已经不知道什么是寒食节,更不会知道那时发生了怎样的事情,致使那个人宁死不同新政府合作。
文化大革命虽然不是战争,但空前地残酷与恐怖、毁坏与损失,不亚于一场战争。
躲到山里的人渐渐多起来了。
有个画家,1930年代从欧洲回国,带回了五百多座石膏像,都很精美,在苏州开办了美术学校。日本侵略者来了,战火烧到家乡,画家来不及把所有的石膏像运走。没搬走的那些石膏像,就成了日本兵练习瞄准射击的靶子。二十多年后的文化大革命,全国都成了红卫兵的天下,连藏匿石膏像的地方都没有了。那些二战后幸存的石膏像,被年轻的革命者砸个粉碎,一个也没有剩下。
红卫兵还把许多画家关押起来,狠狠殴打他们。有个画家受不了非人折磨,逃进了深山,从陕西一直走到四川,在深山里走了五十多天,后来昏倒了被人发现,又送回去关押起来。那时候的深山已经不是以前的深山了,草木植被遭到破坏,野果和小动物不见踪影,野外生存的条件已经很差了。这样想来,一个五十岁左右的画家,能生存五十多天也算得上奇迹。
我还欣赏他一点,记忆力很好。大约三十年前,他从四川到陕西走过的山路,竟然还能记得,还能再走回去。当年他去陕西参加革命者团体,革命了三十年,算是资格很老了,但仍然被新一代革命者当作敌人,可见那种残酷性非同一般。当他逃进深山,循着原路逃回曾经出发的地方,是否有过一个期望:能不能将那几十年里的事情,以及它们的后果,像擦去一幅画的初稿,全都抹去呢?
相比起来,南方的高原地区山高林密,人迹罕至,植被尚好,隐藏和生存容易一些。文化大革命那些年,有的山上竟出现了几个人、十几个人一群的小部落。
他们是迫不得已才逃进密林的。
他们中年纪稍大的人,曾经在1949年以前担任过公职,或者生活比较富裕,就自然成了新朝代的敌人,并殃及到他们的儿孙后代。文化大革命来了,比以前的革命更加猛烈,只能逃进深山,回到原始氏族的方式,艰难地生活。他们不敢回到社会之中,只是实在找不到吃的时候,才下山抢一些粮食。
既然抢粮食,也就成了土匪,这关系到国家的安全。于是清剿这批土匪的任务,就由正规军来完成。没有一两年,那些人就不见了踪迹。
我看到网络上的文章回忆,也有不是土匪的普通村民,因为误会,出现了意外的伤亡。某一天天还没亮,山这边的村民合伙翻山越岭,去山那边参加婚礼,他们既没有向剿匪的人报告,又碰响了山上警戒用的空罐头盒,结果,机关枪声响了起来,十多个人倒了下去。
也有命大的人,一直躲在没有人迹的深山里生活。近年来,就有探险者发现野人踪迹,紧着追赶过去,那野人实在逃不掉,就停下来和他们说话。让探险者吃惊的是野人说的第一句话:“毛主席他老人家身体可好?”
野人离开人间,已经四十多年,他的思维还离不开人间。
两只豪猪有了距离
读大学的最后一年,我和同学想去海边,在有轨电车站等车时,旁边两个人正在聊天。一个同学说那两个人是渔民,看脸色就看得出来,像红蟹壳一样,肯定是海上太阳晒的;另一个同学也说他们是渔民,能闻到身上的海腥味儿,那种味道浸透到他们的骨头里去了;我说他们也是渔民,但不是根据推理,而是听到那两个人谈话,说的是钻入海底抓鲍鱼的事情。
他们正说到为美国总统抓鲍鱼。
总统是以前的总统尼克松。在尼克松访华之前,他们几个渔民领到一个政治任务:捕捞一千公斤鲍鱼,运到北京搞国宴,招待美国总统。
“那个逼养子 (大连人把前面那三个字读一个音,做形容词,糟糕的意思)天气,元旦刚过去不两天儿,海里的水血(大连人的形容词,非常的意思)冷,能把人冻死。”他们下水找了十多天,才在礁石丛找到鲍鱼藏身的地方,又下水十多天,抓了一千五百公斤,挑出个大肉肥的一千公斤,由军舰载到岸边,装上直升飞机,奔北京去了。
“大连人说话夸张,”我心里说。“把豪猪说成大象。那尼克松能有多大肚量,一顿饭吃掉一千公斤鲍鱼?真那样的话,来中国时不到一百公斤,回去时能胖到三百公斤,路都走不动了。”
过了二三十年,我阅读杂志时愣住了,一篇文章说到中国当年招待尼克松总统,用了一千公斤鲜活的鲍鱼,正是找大连会潜水的渔民,冒着被鲨鱼咬死和严寒中冻死的危险捕捉来的。并且他吃了鲜美可口的鲍鱼,真的是非常喜欢。
杂志上还说,尼克松访华前,美国方面提出带一千个新闻记者来,中国考虑到人数太多,不容易接待,只同意美国记者来五百人。
虽然杂志上没有说记者之外的各方面随行人员有多少,想必加起来也不会比记者少。这样看来,那些鲍鱼,确实不是美国总统一个人吃掉的。当年,我也是判断推理力很强的人,却在大连人说话夸张这个认识上出现了错误,因为思考的素材不足,不知道尼克松带来那么多人。
尼克松来中国的日期,向后拖延了十多年。
还是1959年,尼克松在副总统的任上,倡导跨越意识形态,与社会主义国家阵营和平共处。他是一个合格的政治家,能考虑到整个人类的利益。比如,他觉得,应当少谈共产主义的威胁,多谈给人们以自由,而民主国家的首要目标,不是击败共产主义,是让富足战胜匮乏,让健康战胜疾病,让自由战胜暴政。
那时候,苏联是共产主义阵营的首领国。夏天里,他访问了莫斯科的赫鲁晓夫,确定了美国和苏联之间的交流和开放,确定了民主国家与共产主义在激烈冲突中相安无事,不会引发新的世界战争,洗劫人类的幸福。他还希望赫鲁晓夫,向中国人转达美国与中国开放交流的想法。可是,赫鲁晓夫在中国革命者眼里,已经没有共产主义阵营前领袖斯大林的威望了,在雄心勃勃改变世界的北京,碰到的是尴尬与羞辱。
到了1972年,尼克松访问中国的时机成熟。那些年里,中国的大跃进引发了大饥荒,四清运动又引发了文化大革命,该想的都想到了,该做的都做到了,一次次实验的失败,都带来了灾难性后果。革命者不必担心革命的后果,但是会在困惑迷茫中,收缩自己激进的政策。八十岁的毛泽东,做了他生命晚年唯一最清醒又最正确的事,回应了美国总统尼克松的访华请求。
前一周的火车上,有个青年人读毛姆的《月亮与六便士》;这一周的地铁上,另一个青年人读奥威尔的《动物庄园》。这两部小说我都看过,印象都很深。
在后一部寓言体小说里,动物庄园开始时壁垒森严,用武力与外界敌人对抗,后来与外界做起生意,卖出自己的产品,买进需要的东西。
它们不会打开阔大的前门,那样太招摇了,谁都会看见。但是仅仅打开侧面的小门,也等于打开动物庄园的大门,结束了封闭状态,结束了对抗时期。这样做必然带来庄园的变化,身为领袖的动物,最早站起来用两条腿走路,穿上了人的衣裳。
《动物庄园》的写法挺好玩的。整部小说有整体方面的寓意,各个情节也有细节方面的寓意。庄园领袖站起来走路的情节虽然一带而过,作者的寓意还是显露出来:只要与外界来往,自身就会变化。
中国人的习惯之一,是在公众场合不与陌生人谈话。前一周的火车上,这一周的地铁上,我都没有与他们谈关于小说的体会,只是低下头来,阅读我手上的一本书,凯尔泰斯的小说《无命运的人生》。我买这本书时,看中的是瑞典文学院的评价:他的作品对脆弱的个人在对抗强大的野蛮强权时的痛苦经历进行了深入的刻画,而其自传体文学风格也有其独特性。
关于回忆尼克松访华的文章,我读过一些,感兴趣的是其中一些细节。比如那时中国到处都有毛泽东的巨幅画像,都有宣传毛泽东思想的大幅标语。尼克松所到之处,那些标语收起来了,那些画像全部移走。移走毛泽东画像,当时的叫法是“请走”,“请走”是在个人崇拜和个人迷信年代唯一的叫法,就与中国人不能说买观音菩萨像,只能说“请”观音菩萨像,是同样的道理。
这个细节让我感到意外。
原来我们那时就知道,让外国人看了那些个人崇拜、个人迷信、世俗领袖宗教化的东西,会笑话我们没有进入现代文明。我们把那些东西“请走”或搬开,目的只有一个:让美国人看到的中国,像是一个比较正常的国家。
1972年的时候,多麻烦啊。在清楚地知道个人崇拜、个人迷信、世俗领袖宗教化不符合现代文明的时候,我们还要做两方面的事情:一方面是需要他的画像和标语遍布中国,继续对民众的宣传;一方面是外国来宾到来时赶紧搬走,完成对外国人的欺骗。
这两方面的欺骗宣传,不做不行吗?
大概是不行。
如果行的话,在当时就停止了,或者在1972年以后,也可以停止了。
我还注意到一个细节。
尼克松和毛泽东见面后,提出了他来中国需要解决的一些重大问题。他的话被毛泽东打断。后者指了指身边的周恩来,这些事情你同他谈,我们只是谈谈哲学。
哲学好啊,在中国人看来,它统领全局,有指导意义。
当然,任何事物,包括尼克松访华这件事,都可以上升到哲学的高度。
在我的印象里,比起毛泽东和尼克松,叔本华更像哲学家。并且,他有一段生动的论述,比奥威尔的动物庄园更像一个寓言。
他说,一群豪猪在寒冷的天气感到寒冷,挤在一起取暖,每一只豪猪都被对方的刺扎痛了。但是相互远离了呢,还是感到寒冷。它们在无数次扎痛之后,找到了合适的距离,身上的刺扎不到对方,体温却能够相互影响。
人也是豪猪,他接着说,又要不被刺痛,又要感到温暖。这就需要适当的礼貌。
再引申出去,国家也是豪猪,不同的国家和阵营也是,它们需要适当的规则。
这样看来,在叔本华的观念里,他去世以后的尼克松与毛泽东见面,调整了两只豪猪——两大阵营的距离,意义很大。
正义没有得到伸张
中国官方的《人民日报》,在1972年的一篇社论中说道:“日本人民过着非常贫穷的生活,我们不应该再增加日本人民的负担。”
在那之前的官方宣传里,所有资本主义国家的人民,都过着贫穷的生活,只有中国人过着幸福的生活。至于日本人的生活更差、非常贫穷的说法,我还是第一次听到。
许多年之后,我看到真实情况是这样的:
二战以前,日本是亚洲最富的国家;二战之中,日本掠夺了很多国家的财富;二战过去没几年,日本经济恢复到战前水平。此后日本的发展速度,一直遥遥领先于其他发达资本主义国家,1965年至1979年,经济增长十倍以上。
就在1972年,日本的国民生产总值超过了德国,跃居资本主义世界第二位。根据另一种说法,在1960年代末,日本就已紧随美国和苏联之后,成为世界第三经济大国,其都市劳动者的收入,是中国都市劳动者收入的十倍以上。
为什么官方报纸故意说谎?它们在掩饰什么?
回想一下1972年都发生了哪些事情,我才想到,那篇不说真话的社论,掩饰的是那一年中国与日本签署的共同声明,而那份文件里,中国放弃了对日本国的战争赔偿要求。
不幸的是,我们人类有了工具之后也有了武器,有了国家之后也有了战争。
我们知道,国家之间战争状态宣告结束,往往不是在战场上胜负已定,而是战败国的赔偿数额和方式确定之后,这好像是人类社会的惯例。二战后,饱受战火蹂躏的世界,重新制定了一个关于战时保护平民的日内瓦公约,禁止战争加害国逃避自己的责任,也禁止战争受害国放弃自己的权利,为的是加大发动战争的成本,使好战者不敢轻易发动战争,从而最大限度地减少人类的损失。
按照这个公约,作为战争受害国,必须对自己的百姓负责,即使愿意放弃对战争加害国的赔偿权力,也是不合法理的。
如果中国不放弃战争赔偿,日本要赔偿多少呢?
那场特别惨烈的战争,是从1931年开始的。日本军人发动的侵华战争持续了十四年,造成几千万中国平民死亡,掠夺和破坏了大量资源财富。二战结束的1945年,中国政府的赔偿委员会估计,十四年战争里,中国的损失不低于620亿美元。我看到的另一个统计数字更大一些,900亿美元,大约是民间赔偿需要的数量。当然这两个数字是按当时币值计算的,远远高于后来的购买力。按照一种叫做可比价格的计算方式,1945年的 620亿,折合为1972年的1200亿。
1972年,我家住的那条街,新搬来一个邻居,满脸横肉,身材高大,性如烈火,看谁不顺眼就动手殴打。许多年后,他的儿子长大了,也很霸道。但是,随便打人的革命年代过去了,打人致伤需要赔偿损失。有一次,他儿子赔了受害者一万元,其中医药费四千多,剩下的算是精神赔偿。按我的理解,这就与德国的战争赔偿相似:二战结束后,有几百万人无辜受难的犹太民族,获得了德国600亿美元的赔偿,其中一部分赔偿的是他们的财富损失,一部分是赔偿他们精神上的巨大痛苦。
日本还要增加多少赔偿,才能对几千万中国平民死亡负责?才能对中国人的巨大痛苦有所安慰?
1972年,美国总统访问了中国,这件事深深触动了日本。新任日本首相也要建立与中国的外交关系。据许多文章介绍,他已经准备答应对中国的战争赔偿。
这种说法,我觉得可信。一是1972年的日本国力非昔日可比。从这一点来说,中国很幸运,等到能够向日本索要赔偿时,日本已经成为世界第三经济强国,完全具备了赔偿能力。二是中国的国门一旦打开,那个难以想象的巨大市场,会给日本企业带来难以想象的巨额利润,远远超过那份战争赔偿。三是战争赔偿这道障碍,横在日本与中国正常邦交前面,必须跨越过去才能向前走,并且那是欠着中国的,赖也赖不掉,早晚要给。
但是上面第一个观点根本就不成立。
索要战争赔偿,是文明世界伸张正义的一种手段,并不看你有没有赔偿能力,有了要赔偿,没有也要赔偿。我知道这方面的例子:一战后的战争赔偿,相当于9.6万吨黄金,德国历时九十二年才完全还清。最后一笔还清时,已经是2010年的深秋。
这里有一个不能被忽略的细节。
民众。民众在非正义战争中的作用。
一战后的巨额战争赔款,在德国民间形成严重的对立情绪,是德国能够发动二战的原因之一。发动新的战争,德国就拒绝了继续赔款,民众成了战争的实际受益者。他们以积极合作或消极合作的心态参与了战争,就像他们是国家的一部分一样,他们的罪恶也成了国家罪恶的一部分。
我看过充满人性反思的《朗读者》,还记得电影中那个不会阅读、后来在监狱中学会了读书的女主角汉娜。战争结束了,汉娜与那一代德国人一样,生活在普遍弥漫的麻木之中,从没想到追究自己的责任。直到1960年代,二战胜利20周年之际,西德开始打破对纳粹罪行的缄默,社会舆论开始广泛讨论大屠杀。年轻人开始追问他们的父辈:什么是大屠杀?什么是集中营?你在战争中做了什么?你是不是纳粹党党员?
汉娜后来在监狱中阅读的书,就有一本是另一个汉娜写的:《耶路撒冷的艾希曼——关于平庸的恶的报告》。后一个汉娜认为,使得纳粹的罪行得以实现的绝大部分人都具有这种“平庸”特征,他们轻易地放弃了个人判断的权利。在罪恶的极权统治下,人的不思想所造成的灾难可以远胜于人作恶本能的危害的总和。
民众从战争中受益的事情,也发生在日本。
你可能读过川端康成的作品,他是出生在1899年的日本作家。
在他出生前后的一些年里,日本通过战争掠夺中国资源,向战败的中国索要赔款,不能不影响到日本民众的生活。说是民众参与分赃、利益共享,可能说得重了,但如果说他们会从中受益,并不过分——比如,当时的日本商人能够在中国获得比中国商人更好的政治、经济待遇。
1931年日本侵占中国东北,随后向那里移民的日本人数量大增,以致于日本政府把向中国东北移民列为“国策”,制订了十年间一百万户、五百万人的庞大移民计划。那位川端康成也去了中国东北,但从军方那里听到了要向整个中国开战的消息,很快搬回了日本。
国家为善,民众为善;国家作恶,民众帮凶。与德国不同的是,二战后的日本,从知识界到普通民众,一直到1972年,仍然缺少对发动侵略战争的反省。川端康成的小说里,你读不到反省的文字,无论是对国家罪恶的反省,还是对民众罪恶的反省。
我看到几幅日本首相1972年访问中国时的照片,他的手与中国领袖的手,不止一次地握在一起。手的上面是两张面孔,都很胖,带着笑容。
据报道,听到中国领袖放弃要求日本战争赔偿的决定,日本首相喜出望外,全世界感到非常吃惊。至于应该得到赔偿的中国民众,他们有什么反应,却没有报道提及。
有文章说,日本已经公开了那段时期的文件,文件上说:在研究中日建交条件的时候,日本曾打算参照与韩国和东南亚建交的先例,向中国支付战争赔款。然而,中国政府却一口回绝。
我还读到中国官方媒体刊登的文章,对1952年的台湾、1972年的北京,全都放弃了日本战争赔偿的事情,做出了一种特别神奇的解释。
对于前者的解释是:台湾当局为求得一个所谓“中国合法政府”代表的形象,处处委曲求全,步步退让,为一党一派之私利出卖民族大义,令每个正直的华夏子孙羞愧。
对于后者的解释是:中国政府从大局出发,放弃战争赔偿,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的博大襟怀,也代表了一个泱泱大国的宽容大度和长远眼光。
这种解释的神奇之处,在于它是斗争中的两个党派相互通用的文体。如果台湾那边,将其中表示身份的名称对调一下,其余的不做改动,也可以刊登在他们的媒体上。
我把这段神奇的解释收录在这篇文字里,是希望一二百年以后的中国人能读到它。
我甚至想到他们读了之后微微一笑。
他们会说,与日本建交的1972年,正是美国把中国钓鱼岛的行政管辖权交给日本那一年,为什么不提出钓鱼岛的主权?那年月的人真有意思,竟然会把唯一合法政府的名分,看得比索要钓鱼岛和战争赔偿更重要!在中国几千年历史上,两个相邻朝代政府并存的情况很多,比如清朝的政府迁都北京,明朝的政府一路南逃,逃到台湾岛又生存了几十年,哪个政府不是合法政府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