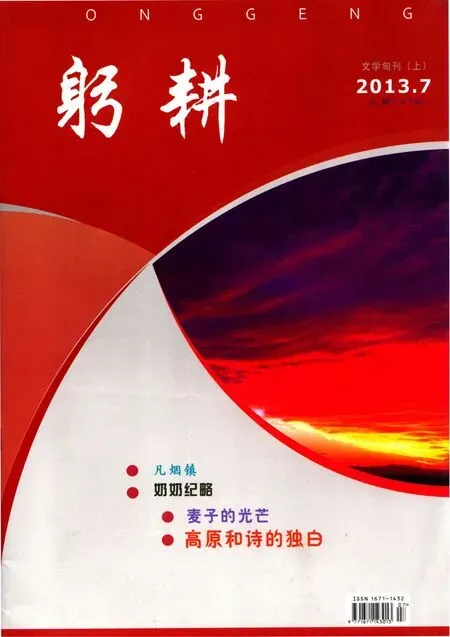我的博士生活
◆ 周岩壁
2009年9月至2012年6月,这段时间,我在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攻读博士学位。这离我本科毕业,走上工作岗位,已有近14年时间了。14年时间!那是唐僧师徒四人从长安出发经历了十万八千里的艰难险阻,取得真经,终成正果,成佛作祖的时间。鲁迅《在酒楼上》的吕纬甫说:“我在少年时,看见蜂子或蝇子停在一个地方,给什么来一吓,即刻飞去了,但是飞了一个小圈子,便又回来停在原地点,便以为这实在很可笑,也可怜。可不料现在我自己也飞回来了,不过绕了一点小圈子。”真是,又不料我也回来了!就怎样两手空空地进了华东师大的校园,我希望能采撷点儿知识,装装空荡荡地过得穿堂风的头脑。就是说,我刚进校园时,还很乐观,有点不可救药的老天真哩。刚开始,一是由社会切换生活场景到恬静的校园,挺新鲜的,也有点重拾青春的喜悦与感慨;二是,还没有开始学位论文的写作,听听导师的课,看看闲书,时间尚余裕。三是乱涂乱画的老毛病,总是不可救药,像陈年的疟疾患者,趁机不时折腾那么一下,随手写些随感随想,经历的人情世故。这三篇都是读博时炮制的,放在那里,总有想出土见光的痒痒。
前一段时间,回南阳,和著名作家华歌主席、《躬耕》主持人水兵一起吃饭,都鼓励我写点东西。我也知道他们的良苦用心。厚着脸也就答应了。私下里想,虽然我的文章差,和登在《躬耕》上的大家们的文章相比,令我汗颜。但给他们陪衬陪衬,做个反证,对他们而言不是很好嘛。
——是谓序。
春天校园里的猫
据杨绛回忆,他们和林徽因家做邻居的时候,春天的晚上,钱家的猫和梁家的猫争风吃醋,在外面房顶上翻翻滚滚地斗殴,钱锺书总是穿上布衫,拿上长竹竿,夺门而出,前去支援他家的猫;这大概是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再早二十多年,鲁迅住在北京八道弯的院子里,春天的晚上,听见声嘶力竭的猫叫春声,总是拿上长竹竿,夺门而出,但并非前往支援谁家的猫,而是要给这些被爱情弄得头昏脑胀的家伙以当头棒喝:配合就配合吧,何必如此大吵大闹!你看,生气也罢,喜欢也罢,猫总是牵动读书人的心绪,二者似乎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华东师大校园里的猫对这一说法也给予相当有力的声援。具体说,是生活在我们闵行区研究生公寓院子里的猫。在女生宿舍的门口,照例有个牌子——“男士止步!”,就在牌子边上,有个纸箱子,里面铺着小被褥,那就是猫睡觉的地方;准确些,应该说,猫似乎在这里睡觉。因为首先我没有半夜三更地跑到女生宿舍门口去实际踏看猫是不是在它的房间里睡觉,就无法肯定——否则,就有悖科学之实证精神也。再者,这些猫不分性别,全都对“男士止步”的招牌视若无睹,迈着猫步在女生宿舍进进出出,经过的女生还不时招呼它们,亲热得很;女生对我们这些男生反倒粉面朝天,不屑一顾;所以,有哪位女生款待它,赏脸留宿也是可能的。这样看来,门口那个纸箱子房间恐怕是形同虚设了。
虽然猫大得女生爱恋,我们倒也并不妒恨它。反而爱屋及乌,“非女之为美,美人之遗”嘛,我们也有点喜欢华东师大校园里的猫了。有一回,从食堂吃过饭回宿舍,经过女生宿舍,有个纤细腰身极像希腊古花瓶的女生,掌上摊着猫食;猫食看上去像干了的枣子一样,两只猫摇着尾巴,把猫食嚼得格嘣格嘣响。见此情景,我不由地和身边的兄弟讨论起陶渊明的《闲情赋》:他对美人爱得发昏,为一近芳泽,愿意做他情人的衣领、脚上穿的鞋子、手里拿的扇子,为什么就没有想着做一只偏得美女怜的猫呢?这位兄弟说,你又苛求古人了!1600年前的老隐士实在是无法知道咱们华东师大校园里的猫过着多么幸福的生活呀。
春天来了,正是猫叫春的时候,但校园里的猫并不是那么热烈;偶尔也听得一两声,然后就是一片安静。晚上也绝不会因猫热烈的叫声而蹂躏坏大家的睡眠,以至于你起了鲁、钱二位大师那样持竿、夺门而出,要去交涉一番的冲动。原因何在?诗人说过 The mouth kissing is not singing,接吻的嘴巴不唱歌嘛。校园里的猫足够多,都有自己中意的伴侣,忙着在花花草草中寻幽探胜呢;没时间叫春了。
那天正午,我从复印店回宿舍,求近,走一条草地上的石子路,一只瘦健的黄猫在路半中间冒了出来。路窄,它不但不让开,反而冲着我很有底气地喵了一声,这时我看到它的两只眼睛,在春天温暖的阳光下,一只是黄琥珀色的,一只是混沌的蓝色。我很情愿地给它让开路。给它让路,固然是因为女生宠它,我们不能不随和;另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猫对整个校园的环境卫生是有功劳的。因为它们,在这个绿地众多、花木蓊郁的大校园里,我没有遇见过一只老鼠!
所以,华东师大校园里的猫,有理由得到女生青睐、男生尊重,自由地在校园里大摇大摆,像贝洛童话里穿靴子的猫巡行在他主人的领地上一样。那么,我们呢,我们这些拿着国家津贴,解决了个人吃饭问题,这些坐在图书馆里搞研究的人——我们也要有点责任意识、担当精神吧,立志对国家有所贡献。岂能人而不如猫乎,尤其是我们校园里的猫!
自愿退化
老巩有点与众不同:首先因为他已经是副教授了,又不辞辛苦地出来读文学博士学位;再者,他儿子意气风发,也已经在湖南一家大学读本科学位了;第三,他老婆不甘寂寞,也在他们家所在的江北某市攻读在职硕士研究生学位。这样看来,好像老巩在家里很有号召力,人人都被发动起来,使大家为着更高的学历而自强不息!然而,我们后来发现,事实上并非如此:老巩在家里恐怕没有那么高的威信哩。
事情还得从头说起,那是上学期。老巩的岳父因为年纪高大,天气寒冷,哮喘病发作,到上海来住院治疗。老巩的老婆也来上海陪护。其实老巩的内弟们就在上海工作,老爷子这种慢性病,犯不着那么兴师动众的,由儿子看护一下得了。老巩竟然也请了一星期的假,在医院陪护老岳父。他再露面的时候,我们看他眼睛红红的,好像也瘦了许多。大家都给他的模范表现深深打动了。看来他老婆对丈夫的表现也颇为满意。为了表彰老巩不分昼夜的坚守,特地安排了一场小小的聚会,就在这场聚会上,我们才一睹这位老嫂子的风采。我们也才有点明白老巩在日常言谈中对他老婆赞不绝口的原因所在。
老嫂子这种说法是不太准确的。因为她看去只有二十八九岁,薄施脂粉,身腰纤细,睫毛长长的,给下眼睑打上浅淡的阴影,显得非常有魅力;而且应酬交际又非常老练。大家都开玩笑说这恐怕是老巩临时雇来的美人吧。老巩听着,也不辩驳,看着面前盛酒的杯子,笑容压抑不住地泛上脸来。有这样如花似玉的佳人,对岳父再尽心一点也是应该的。
然而,老巩的老婆,绝对不是花瓶。老巩有一回给我们说,我们这个年纪,经常让老婆伺候着,都退化了;出来上学,生活都不能自理了。老巩的宿舍乱糟糟的,进去就闻见浓厚的香烟的臭味。他喝茶的杯子,一层褐色茶垢,弄得什么茶叶从杯子外面看都是那种钝钝的陈旧。除了上课,老巩甚至吃饭都尽量省了,每天煮方便面吃。过了不到一个月,受不了了,老巩把他老婆又从家里叫来,来给他做卫生大扫除:给他收拾屋子,整理东西,把堆积的脏衣服给一件件洗了。据江西的一个兄弟说,老巩老婆为给抽水马桶擦洗干净,把他只用了一次的一瓶清洁液几乎用光!这就是说,结婚以后,老巩因为老婆太能干,已经退化成一个附件了,丧失功能,到了常人难以想象的程度。虽然是这样,大家说起来老巩,还是羡慕他的福气,愿意能有这么又美貌又能干的老婆,可以使自己也做附件呢。
然而,太听老婆的,有时也会出岔子。这学期开学早,过了正月十五我们就上课了。老巩由他老婆把他送上车,当时正是寒流由北向南推进。他老婆说,上海已经是春天了,棉袄带去也是累赘。于是,老巩就穿着西装,一副迎接春天的样子,欢快地出来在我们面前。然而,春天并非有那么轻易地到来,倒是一些冬天残余的雪花零零星星地洒下来。
于是,老巩就不免冻地瑟瑟缩缩的。尤其是晚上,他铺的、盖的被褥都不足以抵挡寒冷,光有他老婆的话语是温暖不了他的身体的。老巩冻得晚上睡不着觉。正好我有两床被子闲着没用;于是给老巩说,让他拿过去晚上用。老巩本来说行;但他又打了个电话问他老婆,他老婆不同意,说用人家的被褥,干嘛呀!于是,老巩就不来借被子,硬是用他坚强的意志度过了那一段寒冷!这才使我发现老巩对自己的老婆真是言听计从,忠心耿耿。
前两天,老巩的老婆又来了。他请我们在花香吃了顿饭,然后服服帖帖,由老婆领着坐公交车,说要去一家超市给老巩买个电热壶,好烧开水。我们看着他俩上车,都说,老巩你好幸福呀。这恐怕是老巩在学术上取得显著成就的重要原因呢。
书癖
博士津贴刚刚发下来的那天晚上,老蒙来找我,一脸秋霜,要借两千块钱。说是欠我们研究生公寓楼下的那家书店书钱,开店的老头子要回乡下去,所以要老蒙还钱。我有点将信将疑,这学期才来一个多月,如何就欠那么多钱!我说,太多了吧,你再找别人借一点;并且我手头没钱,晚上食堂边上的自动取款机里的钱都取走了,现在要取都没处取;你给老头子说说,明天再还他吧。老蒙说好吧。老蒙走后,我换了衣服,跑到那家书店,书店里也没什么人,老头子和他儿子都在。我直接问老头子,我们老蒙欠你多少钱?老头子面无表情地说,两千多,你们帮他凑一凑,快点还了。我说,我们哪有那么多钱,你不会让他慢慢还嘛。
老蒙买书成癖,我们都是知道的。他宿舍里两个书架上都堆满了书,有些直接就摞在床头,把他睡觉的地方都侵占了。甚至一些赠送的报纸,他看了也并不丢弃,带回宿舍,堆在阳台上,过一段时间,拿到留学生楼下那个修自行车的小屋里当废品卖给人家。
我们中文系的几个博士住在一块,时间长了相互比较了解。老蒙说他是早产儿,生下来只有七个月,身体虚弱,一向多灾多病。他读的博士是委培,所以,学校不给他发津贴;但他给自己的导师作助教,因而学校给他发有助教费,每月五百多元。他在东北的原工作单位,每月给他发基本工资,有一千多元;这个钱,他老婆掌管着,他老婆和他一个单位,工资也不高,还要照护他们的女儿,也挺辛苦。老蒙在这边有时候找点家教作作,也能赚点钱。但家教也不容易找到,这学期老蒙就还没有找到家教的差事。所以,老蒙的日子过得很紧巴。有一回找我借钱,说吃饭都有困难;我借给他了。但老蒙并未将钱全贮到饭卡上,而是拿出一部分去付网上订购的书账。
老蒙不光找我借钱,他还找另几个发了博士津贴的兄弟借。但他们都没借给他。一个广东的兄弟,不太了解老蒙,说,以前在单位的时候借给朋友一千多元,至今未还。现在老蒙来借钱,又不说什么时候还;不敢借给他。一个浙江的兄弟说,老蒙上学期走的时候,找他借了三百元钱,说是回去给他女儿买点礼物;后来才知道老蒙在借钱之前已经给他女儿买好礼物了!这学期来,老蒙从来不提那三百块钱的事。
老蒙曾对别的兄弟说过,他在家乡的时候,借亲戚朋友的钱,两千三千,甚至几百块钱,也不还人家,最后弄得都不理他了,亲戚也不来往了。所以,我们认为他有种四处欠钱的坏毛病;如今看到我们发津贴了,又来借。
第二天,老蒙正好被导师召去有事,几个兄弟一商量,这回都不借给他钱。因为,这样纵容他的坏毛病,只能使他越陷越深。而且,这又不是什么天灾人祸,是他自由意志的结果,他必须自己来解决这个麻烦。但我们也不能坐视不管,我们尽力协助他处理这件事。所以,老蒙晚上回来,我们先把他臭骂一顿,说,你已经是三十多的人了,有老婆有孩子,得有点责任意识;还只是由着性子乱买书,图书馆那么多书,怎么不去看!你得量入为出,别尽赊账。
我们建议老蒙把赊的书还搬回去,还给那老头子。老蒙说,那些书上都写上他的名字了,退不掉!但有一套《蔡尚思全集》还没来得及写上老蒙的名字。我们就帮着老蒙搬着蔡尚思去老头子的书店交涉。结果,书店的老头子同意把这套值五百多元的书退回去,剩下的1500元 ,要老蒙两个月内还清。老头子生气地训斥老蒙,你没钱还让我向出版社又订了两套书!老蒙低着头,一句话也不说。事情就算这样解决了。
过了两天,一个晚上,我和老蒙到一家超市买生活用品。老蒙的手机响,我听他问对方叫大叔。他说是书店的老头子找他,让他去。我问他干什么?他说,老头子要回乡下去,让他儿子接班,叫我们认识一下。又说,欠老头子的书钱,都已还清。我问老蒙,从哪儿来的钱。老蒙不告诉我,只说,只问家里要了五百元钱。于是,我们就结了账从超市出来。我看老蒙买了一套笔墨纸砚,说要练字。我自己买了两袋买一送一的蛋黄派,劝老蒙也买,老蒙不干,说,便宜没好货。老蒙买了一袋法式小面包。我想,嘿,这家伙又有钱了啊。
这两天,老蒙给抽去改公务员考试的卷子,忙得很,不过又要给他发一笔钱了。近段没见他买书,过几天他拿到改卷子的钱,是不是又要买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