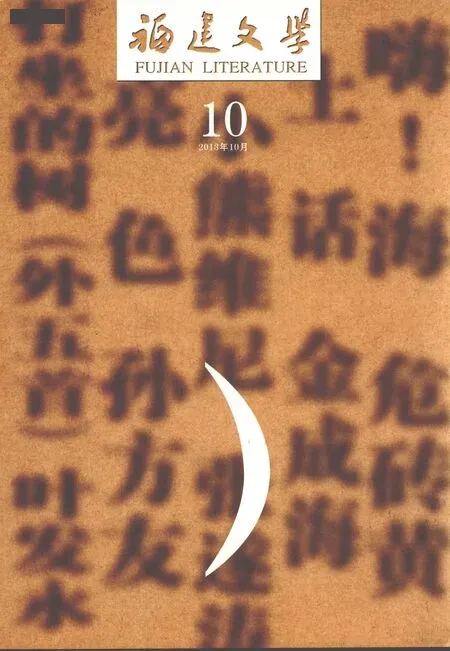萧红的园子
□李晓光
在呼兰,萧红留下两样东西。
一个是呼兰河。一个是她的园子。
据说,一次一个台湾作家采风团来大陆,他们只看了两个作家的家。一个是沈从文的湘西。一个是萧红的呼兰河。如果没有萧红这个园子,我想我这辈子也不见得会到那里去的。
当我第一次迈进她的园子时,除了园子周围那段古朴的围墙,还有几间像棋子似的房子,静如处子般。另外,印象最深的是几个吊在架子上的葫芦,醒目地在秋风里一荡一荡的。
第二次迈进这个园子,一切都是经霜后的景象。
生命在这个季节里剥离。写在人们脸上的除了无奈就是心底的惊叹。
园子里有几株地瓜花儿,经了霜后,越发地红了。红得有些乍眼,红得有些坚韧。
我没有赶上好时候来到这个园子。我错过了它的最佳年龄。
比如春天萌醒的时刻。
比如夏天叫天子叫的时刻。
比如冬天雪拥蓝关的时刻。
来此正逢深秋,最是潇潇落红之后。
在园子里拍了很多幅照片。唯有一帧不能忘怀,又是历历在目的,却是那一抹深秋的红。
萧红在《呼兰河传》里着重写了她的园子。她说:“呼兰这小城里边住着我的祖父……”“我家有一个大花园,这花园里蜂子、蝴蝶、蜻蜓、蚂蚱,样样都有。”
源于祖父,源于园子。在她看来,一切都是好的。
“偏偏这后园每年要封闭一次的,秋雨之后这花园就开始凋零了,黄的黄,败的败,好像很快似的一切花朵都灭了,好像有人把它们摧残了似的……”
原来,在幼小的孩子心里,除了倾听了生命拔节的声音,也要第一次领略凋零的含义。
摧残的岂止是这些花朵呢?
在园子的西南角,粉坊的旁边,是赶车的胡家。至今还留有马厩。两匹嘶嘶的烈马。一匹低头吃草。一匹仰天长啸。还有古老的石磨和古井等一切旧事物,独独不见了小团圆媳妇一家人,仿佛被跳大神的用风卷走了。
但一切都凋零了。胡家的小团圆媳妇还活化在呼兰河传里。
冯歪嘴子的草棚,草棚里王大姑娘和他的大公子。
有二伯顶着洗澡盆子在正午的阳光里偷偷地溜出家门。
粉坊里吱呀作响的房梁和一地的歌声,在月光里铺陈开来。
萧红不止一次地说,我家是荒凉的。
我家的院子是很荒凉的。
我家的院子是很荒凉的。
我家是荒凉的。
我家的院子是很荒凉的。
……
在她的笔下,我不知道重复这五次荒凉到底出自何初衷?她打下了一个深深的伏笔。我彻夜思想不得要领。
第一次提到“我家是荒凉的”——尽管房子连着房子,外表上似乎是很威武的。但在她的眼里“但我看它内容空虚”。除了磨坊一家和养猪的那家被她信手拈来,摆在棋盘之中以外,再就是粉坊的歌声,沉重的梆子声,磨坊里打梆子的声音在夜里常常是越打越响,越打的激烈人们越说那声音凄凉。荒凉的院子里像一张棋盘,上面走着一些像棋子一样的人。木木的,在院子里,在那个荒凉的院子里等待着命运的宰割,不敢轻易反叛。那个园子是夜的颜色,是深秋的季节。无声的反叛只会像那个12岁的小团圆媳妇,被无情地剥夺,直至生命的早夭。
有反叛意识的应该是那个执笔的人,她有着一双透视的眼睛。她观察。她记录。她写光明。也不越过黑暗。
沉重的梆子声像在为谁送葬?又像是在为谁招魂?
园子是荒凉的。确实有些荒凉。
一切都在暗暗地反叛着。
比如有二伯偷窃的报复心理。
比如冯歪嘴子与王大姑娘向封建礼教的挑战。
园子是荒凉的。仿佛有一片乌云笼罩着。似乎有某种不可冒犯的王权在这里主宰着。
除了爷爷在她笔下活着。她的亲人很少被她提及。至于她的父亲,她大概只提到了两次。一次是将顶着酱缸帽子的小女孩一脚踢翻了,差点没被踢到灶口的火堆上去。另一次是将有二伯打翻在地,她这样记述的:“父亲三十多岁,有二伯快六十岁了。他站起来就被父亲打倒下去,他再站起来,又被父亲打倒下去,最后他起不来了,他躺在院子里边了,而他的鼻子也许是嘴还流了一些血。”
磨坊里住着王大姑娘和她的儿子,孩子在母亲的怀里吃奶,小脸冻得红彤彤的,身上盖着布口袋。磨坊跟室外的温度一样,盆子里的水都冻上了。小萧红第一次知道了冯歪嘴子和王大姑娘这个秘密。在强烈的反差下,母亲的屋子里很温暖的,温暖的屋子里有母亲和周三奶奶在咬耳根子,嚼舌头。他们想用口水将王大姑娘淹没。就连下等人做饭的厨子也不忘了在背地里说坏话。园子里的人都说王大姑娘的坏话,整个园子风生水起的。
王大姑娘没被淹死,而且顽强地生下了另一个孩子后,死在了难产上。
小团圆媳妇死了。
王大姑娘带着无情的恶言中伤早早地离开了。
……
只有这圈院墙,及园子里几个寂寂的房子和一些旧事物,还泛着昨天的光辉。
幸好,萧红留下了这个园子。尽管它曾经一度是荒凉的。
但是那笔是疼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