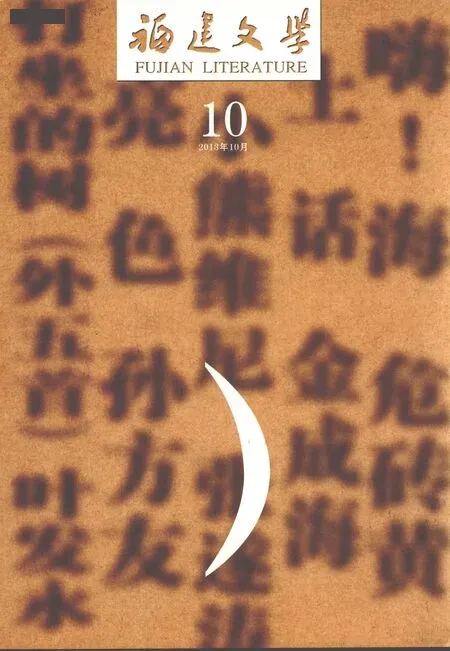小熊维尼
A
似乎每个城市都有条步行街,每个城市也都有条中山路。在葛城,中山路和步行街恰好合二为一,中山路就是步行街。一年那么多节日,别的城市大都是春节热闹,葛城也怪,最热闹的是中秋。这主要得益于这个城市的一种游戏,博饼。博饼据说是郑成功传下来的,说是为了缓解将士们的思乡之苦,所以就发明了这样一种玩意。之所以叫博饼,是因为那时博的确实是饼,想来那时月饼还很稀罕。在今天可就不一样了,一方面月饼越做越豪华,越卖越昂贵,另一方面却没多少人肯再吃它。张远山每年就仅吃月牙似一小块,再吃就说腻了——这还是佐了红茶、蜜柚。但是小的时候并不是这样,那时他还在农村,吃到一块带冰糖的月饼能让他幸福半个月。所以今天在葛城,博饼博的都是生活用品、购物卡,每次博完饼,可以一年不用买沐浴露、洗发液。当然这是一般的情况,单位福利好的,可以博手机、手提电脑,甚至汽车。博的东西越来越丰富,也逐步升级,渐渐地这个城市就疯了。一进入农历八月,大街小巷到处都能听到清脆的骰子声,到处都是“状元”“四进”的吆喝声,满城的人都在博饼,有的是提前在博,有的则是在练习预演。
张远山一开始对博饼还颇有兴趣,觉得不失为一种节日助兴的方式,然而到后来看到博的东西越来越贵重,甚至开始博汽车、房子时,就开始反感了,觉得这已经失去了游戏的原意,变味了,所以对博饼的兴致越来越淡,虽然单位的博饼仍然参加,但已不在乎博到了什么。
唯一没变的爱好是赏月。以前赏月都是上山,家附近就有座小山,半山腰有个亭子,在那里赏月最是合适。所以每年就带了果肴月饼,去那里看半天月亮,然后缓缓下山。山上人很少,下山路上更少,在满月的清辉下,颇有一种萧瑟之感。
但是今年刘思影建议去海边看月亮,嘟嘟一听也吵着要去,张远山一想,也好,“海上升明月”,这样的意境也好多年没有看到过了。早早吃过晚饭,三个人就出发了。到了海边,月亮还未升起。
在海边看了半天月亮,看腻了,三个人就沿着海边往回走,走到轮渡,过街就是中山路。看到中山路上熙熙攘攘的人群,刘思影突然动了心,说我们去逛逛街吧。张远山犹豫了一下,他不喜欢逛街,更不喜欢在拥挤的人群里逛,他宁可回家看会儿书。但是想到今天是中秋节,难得陪刘思影逛一次街,也就答应了。
张远山逛起街来,基本上是目不斜视,直直地往前走,刘思影拉他逛过几次,受不了他走得太快,他也受不了刘思影每个服装店都要驻足停留,两个人也就很少再一起逛街。偶尔一次,张远山也是躲进书店,等刘思影逛完了,再一起回去。那时也算各得其所,但是后来书店倒闭了,张远山无处可躲,带了几次书,坐在商场门口边等边看,但总觉怪异,像是表演,也就更不愿意去了。但是今天,仿佛全葛城的人都拥到了这条步行街上,张远山也就无法再像平时那样迈大步子,只好安慰自己“既来之则安之”,遂踱起小方步故作悠闲地陪刘思影一家店一家店往下逛。
因为是节日,各店家都打出了打折促销的旗号,张远山对这些不感兴趣,总觉得是骗人,半价说不定是先提高了原价再打的半价,折后的价格并不比平时的价格低,但总有一帮糊涂虫被打折冲昏了头脑,趁这个时机买下一大堆自己不会穿的衣服。刘思影毫无疑问,也属于这种糊涂虫之一,他给她提醒过几次,但她根本不听,他也莫之奈何。
刘思影看了几家店,试穿了几套衣服,走出来转着身子给他看,问漂亮不漂亮,他说漂亮。是真漂亮,刘思影天生的好身材,生了嘟嘟之后也没有变形,该凸的地方仍凸,该翘的地方仍翘,小蛮腰仍盈盈可握。配了好的服装,人更见精神。刘思影读得懂张远山眼中的话,笑一笑,自顾自对着镜子再左右看看,进去脱了却不买。拉着张远山的胳膊往外走,张远山奇怪:“为什么不买,不是挺好吗?”
“给你省点钱。”刘思影回眸一笑。
张远山一个激灵,心生一股暖意。到底是自己的老婆,如此体贴人。她这么一说,张远山倒不走了,回去,让营业员把刚才刘思影试过的那套衣服包了。刘思影微怨:“你这是干什么?”
张远山笑笑说:“算是我送给你的中秋节礼物。”这句话说完,才想到已经好多年没有送过刘思影中秋节礼物了。
买完单三个人继续往前走。嘟嘟走在两个人前面,手里拿着一个麦当劳甜筒,是在街口买的,所以一路很乖。只是刘思影要不时提醒他注意不要滴在身上,然而白色的汁液仍不时流下来,打在嘟嘟的衣摆和鞋面上,留下一个个白渍。刘思影见了,责怪他:“不是说过让你拿好了,怎么还这么不注意?”说完蹲下帮他擦。嘟嘟听了也不吭声,一边用小勺子挖着冰激凌,一边听任妈妈用纸巾在衣摆上用力地擦。
步行街走到一半,三个人正准备折返,突然看到前面围了一圈人,走近一看,原来是几个动画卡通人物,正在人群中做着各式卖萌的动作,惹得围观的小朋友一阵阵发笑。张远山知道这是商家为了促销,雇人穿了卡通外套,并没有什么稀奇,正要叫了刘思影拉嘟嘟回去,突然听到嘟嘟大叫一声:“小熊维尼!”
小熊维尼是嘟嘟最喜欢的一个动画卡通人物,家里有的几张小熊维尼的影碟都被他看坏了。家里也堆满了小熊维尼造型的玩具,然而他仍然不满足。
张远山顺着嘟嘟拿着小勺子的手看过去,果然看到在那些卡通人物中有一个小熊维尼。他正咧着嘴憨憨地笑着,手笨拙地挥舞出搞笑的动作,引得那些小孩子一个个上去小心地摸他的身子。摸到了,就回过头既欣喜又有些羞涩地看看爸爸妈妈。这个场景让张远山的眼睛突然有点湿润,他也不明白自己怎么会突然这么多愁善感。
嘟嘟已经把甜筒吃完了,把剩下的壳塞到妈妈手里,转身就想往前钻。刘思影一把把他拉住,好不容易用纸巾把他的嘴和手擦干净,刚放手,他就钻过人群窜到前面去了。
“你看看他——”刘思影有点气急地看看张远山说。
张远山没有吭声。他也凑前了一点,透过人群的缝隙,他可以看到嘟嘟。嘟嘟正站在人群前面的孩子群里,他试探着,既想上去,似乎又有点胆怯,就那样犹豫不决地紧盯着小熊维尼。
张远山看着嘟嘟,突然又一阵感动,嘟嘟这个性格太像小时候的自己啦。那时他也像嘟嘟这样怕羞,总是既想要又羞怯,妈妈曾经批评过他,他也暗自懊恼过,甚至恨过自己,但过后仍然如故。后来他知道,一个人想改变自己的性格有多难。性格决定命运,这话他信,如果命运注定如此,他也无可奈何,只好接受。所以他不会批评嘟嘟,他最多善意地提醒他,尽可能地完善,毕竟他也不愿意嘟嘟像他一样吃性格的亏。
他内心有点替嘟嘟着急,他在心里暗自催促着嘟嘟走上去,大胆勇敢地走上去,像其他小朋友那样去摸摸小熊维尼。没什么大不了的,小熊维尼不是真的小熊,他不会吃了你。虽然他的内心如潮水一般汹涌,但表面上他却显得很平静,只是死死地盯着嘟嘟,不让他走出他的视线。
嘟嘟仍然在跃跃欲试。有几次他回头看了看,可能是在找他们。他赶忙把脖子伸长了一点,希望嘟嘟能够看到他。但显然嘟嘟没有看到他。他于是往前挤了挤,但前面的人太多了,挤了两下,没有挤进去,就停住了,继续用眼神保护着嘟嘟。
还是小熊维尼帮嘟嘟解了围。这让他心中对这个小熊维尼产生了好感。小熊维尼突然把手伸向了嘟嘟,嘟嘟惊喜地往前走了一步,他被小熊维尼牵着手往前又走了一步,他走的时候又回了一下头,张远山急忙再次把头抬高,但是嘟嘟似乎仍然没有看到他。他有点失望地把头缩了回来,但是脸上浮现出了一丝笑容。他突然感到手心里多了一双手,一双柔若无骨的手,他转头看了一眼,看到刘思影正深情地凝望着他。
他的心里又是一热。
小熊维尼蹲了下来,像是跟嘟嘟说了句什么话,嘟嘟也张了张嘴,像是在回答。张远山想听清楚一点,可是街上实在太吵闹了,他什么也没有听到。他看到小熊维尼突然把嘟嘟抱了起来,把他举高了,张远山的心一下子悬了起来,然而不久小熊维尼又把嘟嘟放了下来。张远山看到嘟嘟的脸兴奋地涨红了,他下来后转身往圈外跑,“爸爸,妈妈”,他在喊。
“嘟嘟。”张远山和刘思影几乎同声地喊。
人群自觉为嘟嘟让出了一条小路,过后立刻又闭合了。张远山一把把嘟嘟抱在了怀里。嘟嘟的脸仍然红扑扑的。
“我想跟小熊维尼合影。”嘟嘟说。
确实有不少人跟小熊维尼合影,张远山刚才也想过了,但是想了想又作罢了,他并不十分热衷这种形式。但是既然儿子提出来了,那就给他拍几张吧。相机随身带在身上,刚才拍了不少明月的照片。
他们稍等了一会儿,看人群渐渐散了,就上去让嘟嘟站在小熊维尼的身边,小熊维尼很配合,不断地摆出各种各样可爱的姿势。张远山拍了几张,刘思影看得眼热,也走过去,站在小熊维尼的另一边,让张远山给她和嘟嘟、小熊维尼拍合影。最后一张照片,小熊维尼突然把手搭在嘟嘟和刘思影的肩头,三个人轻拥在一起,张远山的心里突然咯噔了一下,但是转瞬他就厌恶起了自己,你竟然吃小熊维尼的醋!
他轻轻按响了快门。镜头里刘思影和嘟嘟,以及小熊维尼的笑容都那么甜美。
B
陈冠生的心突然一阵抽紧,他没有想到他会这么大胆,他竟然搂住了刘思影的肩膀,等他反应过来,照片已经拍完。张远山站在他对面冲他招了招手,他的脸上带着笑,让他猜不透他的想法。他知道张远山是在向他致意,他赶快松开搂着刘思影和嘟嘟的手,继续做出小熊维尼才能做出的夸张动作。嘟嘟又是一阵大笑,这个略显羞涩的小男孩是那么可爱。
其实从嘟嘟站到他面前时他就认出了他。他看出了他的犹豫不决,他内心在鼓励着他,但眼看着他在一步步退却。他抬头在人群里搜索着张远山和刘思影,终于看到了,他们就站在人群后面,仅仅露出了个人头。张远山没有看他,他的目光牢牢拴死在嘟嘟身上,只有刘思影,脸上带着笑,仿佛颇有趣味地注视着他。
他浑身打了个激灵。
这张美丽的脸他曾多次在窗口看到,但从来没有这样近距离看过。那时往往是刘思影带着嘟嘟在小区里散步,有时也有张远山。三口之家经常是嘟嘟跑在前面,张远山和刘思影肩并肩慢慢走在后面,两个人边走边聊,大多数时候是张远山在说,他经常很激动,手不自觉地在空中挥舞。刘思影则总是那么一副淡淡的神情,眼睛含着笑,一语不发,像是在认真聆听,又像是思绪已经飘远。她修长的双手时而在胸前,时而在背后,手指交叉着,不时地相互揉捏。他注意到她的脚尖有时会突然踮起来,像跳芭蕾舞,这时她的胸部就会高高地耸起,让他看了内心一阵狂跳。不时地她还会侧过头,以赞许和欣赏的表情凝视着张远山。这种表情也让陈冠生看得心醉。他曾羡慕过,也嫉妒过,在他心中,这是小区里最幸福的一家。他已经打听清楚,张远山是一个作家,刘思影则在市歌舞剧团工作,这都是在他心目中很神圣的职业。
曾经有很多个晚上,当他无法入眠的时候,刘思影的面孔就自觉闪现在他面前。他曾经靠想念她而自渎过,但是事后他就陷入无休止的自责中,痛骂自己不是人,不该用这种方式来亵渎自己心目中的女神。他因此痛恨过自己那只自渎的手,他用另一只手打它,用嘴咬它,甚至拿它往墙上摔,用打火机烧。但是等伤痛平息,再一个漫长的夜晚来临,他又会忍不住想念她的面孔,她娇美的身材,她丰满的胸部,每当这个时候,他就会觉得浑身酸胀,手不自觉地就又会往下身摸去,从而将那件他觉得龌龊不堪的事情再来一遍,当快感退去,意识清醒过来,他会再次陷入痛苦的漩涡而不能自拔。
这让他觉得无脸见刘思影,他总觉得,一旦他暴露在她的视线里,她就会立刻从他的身上,他的眼神,他的味道看破他内心的龌龊,察觉他思想中的肮脏,甚至会看出他都对她做过了什么,那么他将会羞愧得无地自容。他仿佛已经看到了她憎恶、轻蔑的眼神,在她眼神的逼视下,他感觉自己的身子在逐渐地缩小,刘思影在他的眼中慢慢变成了一个巨人,她居高临下地瞪视着他,而他仍在缩小,终于他变得跟一只蚂蚁一样了。
这种感觉让他自觉躲避着她。与在公开的场合遇到她相比,他更喜欢躲在窗帘后面,在那里他感觉更安全,也更自如,他可以肆无忌惮地盯着她看,直到她的身影走出他的视线。他会仍然等着,等着,直到她转了一圈,身影再次出现。为了看得更清楚些,他甚至买了个高倍数的望远镜,这样刘思影的一颦一笑都完全纳入了他的视野,她的脸是那么近,连眼角细细的皱纹都看得一清二楚,经常,他看着看着,另一只手就会情不自禁地伸出去,直到在应该可以摸到刘思影的地方抓到一把虚空。
躲在窗后看刘思影渐渐变成了他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如果连着有几天看不到她,他就会心慌、焦灼,甚至坐卧不宁、茶饭不思,他会想方设法打听她的去向,甚至伪装过之后悄悄溜进她住的那栋楼房,躲在她家旁边的楼梯间,直到看到刘思影的身影再次出现。
幸而他从没有在公开场合遇到过刘思影,他倒是在小区里碰到过嘟嘟几次,他立刻紧张得无法呼吸,嘟嘟身边并没有看到刘思影的身影,但是他仍贼一样地逃走了。等在房间里坐定,他又开始暗自懊悔。然而下一次,他仍然来不及寻找刘思影的身影,就兔子一样拔腿逃掉了。他还在小区里碰到过张远山,这次他不再逃跑,他强装镇静,甚至在内心里他还有一种要挑衅一下张远山的冲动,他故意挺起了胸膛,但是当张远山的身影越走越近时,他突然感到像有一座大山从头顶压了下来,沉重得让他无法直起腰,他听到了自己粗粗的呼吸声,双脚像灌了铅一样突然沉重地无法迈步,他羞愧极了,感觉脸像火炉一样烫得可怕,简直要把他烤干了。他终于还是不由自主深深埋下了那颗一直低垂着的头颅,他像个走失了方向的游魂一样无力地向前挪动着步子。在与张远山擦身而过的一刹那间,他仿佛看到张远山意味深长地看了他一眼,这一眼让他心惊胆战。
那次之后他有几天不敢再去看刘思影,他陷入巨大的自卑与自责之中。然而很快卑鄙的欲望就压倒了自卑,到了固定的时刻,他不由自主地又开始向窗口张望,急切地寻找那个熟悉的身影。当那个身影终于出现时,他意识到没有什么可以剥夺他这一点点可怜的享受。
他从小到大大部分时间都生活在孤寂里。生活中除了父母再没有别人。他没有朋友,生活展现给他的除了残酷就是敌意,这让他自觉地主动拒绝了别人。唯一的一次,一个同样孤寂的女孩子接纳了他的友情,但是他知道,她之所以接纳他是因为她除了他之外别无选择。他因此自尊而敏感。在对待她时他也有意保持一定的距离。然而就是这样一份友情,不久之后他也失去了。她辍学了。从那以后他主动地封闭了心灵,再也不敢奢望能享受友情或爱情,这些对于他来说都是极其奢侈的东西,就像电视广告里的那些高级轿车,它们对于他来说显得是如此遥远而不可即。但是在父母面前,他却表现得很骄傲,他说他不稀罕,这话说完连他自己都不相信是自己说的。父母察觉了他可怜的自尊是如何脆弱,再也不问这些让他难堪的问题。他们也渐渐习惯了他一个人躲在房间里看书,听音乐,上网。只是偶尔在他们感觉身体不舒服时,他们会忧心忡忡地想到他的将来。
在他中专毕业以后,他父母曾经尝试着给他找工作。但是每次都因为他的长相功败垂成。父母到处托人,了解他的人也对他充满了同情,有几次几乎成功了,他已经开始上班,但总是不久,对方就会找到各种理由通知他不用上班了。一个常见的理由是他不善言辞,甚至呆板、笨,这个理由让他的父母无话可说。他的父母只好苦苦哀求,一再降低待遇标准,甚至痛诉他的不幸,希望借此能打动对方。对方认真地听着,脸上带着抱歉的笑,然而听完,仍然是抱歉的笑。他因此饱受了打击,再也不愿意出去工作。他能理解父母的担忧,但是他别无他法,他唯一能够想到的解脱方法就是死。他自杀过,喝安眠药,割腕,自缢,但都没有成功,他总是在临死那一刻感到恐惧,他无法那么决绝地对自己行刑。
他的优柔寡断挽救了他。每次救活后,他都深深地负疚,他眼看着父母一天天地衰老,而眼神中的不安和恐慌却一日日增多。
直到有一天他无意中在窗口看到刘思影,他突然体验到一种从未有过的宁静。那是一种高贵之美,这让他一时觉得生活竟然是如此的美好。他不再想着自杀,也开始尝试着写点东西,诗歌或小说。他并没有想过发表,这在他是过于遥远的事,他只是想把一些堵在脑中的想法表达出来,仅此而已。直到后来他知道张远山是一个作家,他才开始制造另一个梦,他投过几次稿,但都如石沉大海,渐渐就失去了动力。他曾经幻想过把自己的稿子拿给张远山,以一个文学青年的身份让他给自己指点指点,也许这是一个不错的接近刘思影的机会。但是他知道这只是一个可笑的梦。如果他是一个普通人,即便长得略丑一点,那么也许这仍是一个不错的主意,但是他是一个连自己都害怕看到自己那张脸的怪物。
不过他喜欢写作,在写作中,有时他会忘掉自己的样子,他感觉自己就像不存在了一样,只是一团空气,或者就是一个意识。但当夜深人静,他一个人熄灭了灯孤零零地躺在床上时,意识会突然变得格外清醒,每当这时,那种绝望的感觉就又会笼罩住他,攫紧他的心脏,死命掐住他的脖子,让他喘不过气来。
他无数次偷偷躲在被子里噢噢地哭泣。
生活的转机是因为现在这份工作。这份工作是父亲的一个朋友帮他找的,他本不想去,但不忍心看母亲痛苦哀求的眼神,只好硬着头皮去了。去之前他已经知道了工作的性质,这让他略微有点兴奋,可以不用真面目示人,这让他感觉既有点新奇,也有点心安。父亲带他去见商场的经理时,他明显从经理的眼神里看到了厌恶。这种感觉击垮了他刚刚升起来的渺茫的信心,他几乎扭头就要走,是父亲强行拉住了他。父亲带着近乎谄媚的笑向经理说着好话,手指哆哆嗦嗦地掏出香烟逼迫一样地塞到经理手里。然后他就分到了一个小熊维尼的外套。
小熊维尼他知道,他从童话书里看到过,他也曾经见嘟嘟手里拿过。他知道嘟嘟喜欢小熊维尼,这一点让他暗自兴奋。第一天他的动作明显比别人笨拙,但这正是小熊的特点,倒让他显得是那么地可爱。他突然像发现了一个新的世界,这才知道这个工作是多么适合他,简直就像上帝替他量身定做的。一开始他还羞怯怯的,不知该如何舞动,也不知该如何讨好小孩子,但是很快他就发现,他根本不需要讨好小孩子,他只要站在那里,小孩子们会自觉主动地讨好他,他从他们的眼神中看到了亲近的渴望,那种渴望几乎跟他看到刘思影时一样。他们试探地摸着他的身子,拉他的手,靠拢着他合影,甚至还在他蹲下时亲亲他的脸庞。这是他以前从未经历过的,他从来没有想到自己会这么受人欢迎,他几乎激动得要流下热泪了。但是他又很快沮丧地想到,如果这些孩子们看到他面具下面那张真实的脸,不知会怎样,惊吓地四处逃窜?高声尖叫?
这样的想象让他难过。但是他很快克服着不再去想,他宁可尽情享受这短短几个小时的美妙时光。他似乎根本不知道劳累,也不觉得躲在这样一个厚厚的毛壳子里有多闷热。按照规定,他完全可以在一段时间之后找个地方把毛壳子脱掉透透气,但是他主动放弃了。他像是陷入了癫狂,让跟他一起扮演卡通人物的那些兼职大学生们都觉得诧异。那天晚上他回到家,感觉自己像变了一个人,他甚至开始幻想如果自己就是小熊维尼那该多好。
但是扮演小熊维尼的机会并非每天都有,他要耐心等待,在等待的日子里他焦渴难耐。
除了孩子们,有时大人也会上前摸摸他,拉拉他的手,经常是些年轻漂亮的女孩,他已经学会了跟她们交流,故意做出些夸张滑稽的动作逗她们发笑。看着她们那么紧地贴着他的身子,冲着镜头摆出各种各样的造型,他心里一边发笑,一边快乐地战栗。
这在以前是他做梦也不敢想象的事情。
有时他也梦想过要是这些女孩子是刘思影就好了。他在大脑里预演过无数次刘思影跟他合影的场景。他的目光一次次热切地期盼过,但又总是一次次地失望。他甚至想过刘思影是否从来没有来过这条步行街,但是那是不可能的。最大的可能是刘思影逛街时他恰好没有上班,或者刘思影从他面前经过时,他没有发觉。后一种想象让他痛恨自己。但是他立刻又想到了另一种最糟糕的情况,假如他发觉了,而刘思影并没有像其他那些女孩子们那样停留驻足,他该怎么办呢?他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她的身影远去,而无可奈何。想到这里,他的心里立刻开始阵阵发冷。
所以当嘟嘟突然出现在人群前面时,他的心因为兴奋而突然停止了心跳,他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他不知道该如何去做。他期盼着嘟嘟能像其他的孩子那样主动,但是看到嘟嘟越来越往后退缩时,他不由得向前走了一步,仿佛很自然地扯住了他的小手。
这只小手他曾经在想象中握过很多遍,现在虽然隔着小熊维尼那厚厚的熊掌,他仍然感觉到了它的柔软和温热。他情不自禁地就把嘟嘟抱了起来,几乎是下意识地就问了他妈妈有没有来。嘟嘟说有,还回头示意了一下。他知道刘思影在哪里,但是接下来他不知道该如何办了。他不敢把嘟嘟抱太长时间,他故作自然地把嘟嘟放下,然而他没有想到嘟嘟突然挣脱了他的怀抱,跑走了。这让他一刹那感觉伤心失望,他几乎要心碎了。然而接下来的事情却是那么神奇。他看到嘟嘟和张远山、刘思影站在一起并没有走,他几乎是焦躁地等着跟他合影的人快快结束,他已经预感到了要发生什么。终于刘思影也走到了他的身边,他的手试探着,想触及她的身体,但是试了几次都停住了,他不敢,终于最后一次,他鬼使神差般地把手搭在了刘思影的肩膀上,然后看着张远山按下了快门。
刘思影没有一点的异样,她仍然微笑着,仿佛根本不知道他曾经把手搭在她的肩膀上。或者她根本不介意,因为那不是一个男人的手,而是小熊维尼——一个可爱的卡通动画人物——的手。他意识到这些时,刘思影他们已经走远。他突然感到身心俱疲,虽然仍有小孩子过来逗他,却再也提不起兴致。
在以后的几天里他渴盼着刘思影的身影能再次出现,但是每次他都失望了,他苦苦地等待,因而显得有点魂不守舍。他一遍又一遍地重温手搭在刘思影肩膀上感受到的那种战栗,这种感觉经过想象的放大变得越来越强烈,然而也越来越不真实,到后来,他感觉那就是一个幻觉,一场梦。他不敢相信也无法证实那一幕真实发生过。这种想法让他陷入巨大的痛苦,他试图说服自己刘思影确实来过,他的手真实地在她肩膀上停留过。为了证实这一点,他在冲动之下几乎找上刘思影的家门,张远山不是有拍照片吗?照片是最好的证明。但是当他已经走进刘思影家的过道时,勇气突然如潮水一般消退了。
他失魂落魄的样子终于被经理发现,虽然隔着一层毛皮,经理仍然准确地断定他心思没在工作上。这时中秋节的热潮已退,国庆节也已经过去好几天了,街上的人流明显少了下来。经理起初错以为他是因为双节已经过去,所以不再卖力,这刚好顺应了他的想法,所以在那天的工作结束之后,经理很直截了当地告诉他第二天不用来了。陈冠生当时就愣住了,那时小熊维尼的头还套在他的头上,脸上仍然露出一副憨憨的傻笑。因为他没有说什么,所以经理想当然地认为头套里面的那个表情跟头套的表情一样,也是一副憨憨的傻笑,这让他既疑惑又感到满意。
C
那天晚上是小马值班。小马那天感觉极其不佳,走起路来头重脚轻,大脑一片混沌,眼皮老想耷拉下来。他知道这是连着几天加班的结果。本来四天一个班,因为所里一个老同志生病,一个新同志结婚,一个领导学习,两个民警出差,就被调整为三天一个班,结果上个班的案件还没消化,这个班又来了。前两天刚好又碰上一起杀人案,虽然是刑警队负责,所里也跟着忙得够呛,连轴转了两天,人人疲惫不堪,但是班还是要值。他只期盼着这天晚上的运气能够好一点,最好电话一个不响,让他安然睡上一觉。
吃过晚饭,他到派出所旁边的妈祖庙拜了拜,恰好被下来吃饭的教导员看到了。教导员打了一下他的头,笑骂道你还搞迷信!小马笑笑,说不搞不行啊,实在累得不行。
拜了果然有效,上半夜电话少了不少,十点之后更是清静,几乎一个电话没有。小马暗自高兴。看看手头没事,就跑到备勤室躺下了。头刚挨到枕头,人就开始迷糊了,睡了不知多久,突然听到刺耳的铃声,小马一惊,但仍闭着眼,感觉那声音仿佛来自梦中。又等了会儿,就有人踹他的屁股,赶忙睁开眼爬起,原来是教导员。教导员骂他,电话响几遍了,没听到?
小马不好意思地笑笑,说睡得太死了。
不来还好,一来就是三个。第一个是报失踪,一个叫陈树林的老人报称其儿子陈冠生到现在还没有回家。
多大了?小马问。
二十八。
失踪多长时间了?
他平时十点就回家了,今天到现在还没有回来……
小马抬头看了看墙上的钟表,忍不住捂着嘴打了个呵欠,嘴里有了不高兴:一个二十多岁的成年人,才不见两个多小时就报失踪……
不是,你不知道,那个叫陈树林的老人抢过话头解释,他平时从来没有这么晚回家过……
有没有给他朋友打打电话?
……电话那边沉默了一下,然后说他没有朋友。
一个都没有?
一个都没有。
第二个报警电话是一个自称是商场经理的人打来的。他说的那个商场他去过,就在不远的步行街上。他报警说商场被盗了。
都丢了什么东西?小马心里一紧,这估计是个大案。
那人却吭吭哧哧了半天,像是不好意思说,然而最后还是说了:也没丢什么,就一个小熊维尼套子,就是那种人套在里面……他还想解释,但是越说越说不清,最后干脆闭嘴了。
小马知道他要说的是什么。他截断了他的话头,那个东西值多少钱?
钱倒不值多少,只是……那个经理又吭吭哧哧起来。
他提供了一个嫌疑人,名叫陈冠生。
陈冠生?小马感觉这个名字很熟悉。放下电话之后他突然想起刚才那个报失踪的人说的那个名字就叫陈冠生。
第三个电话是一个不肯说名字的群众打过来的,他用惊恐的腔调说他刚才在市府大道上看到一只奔跑的熊,熊跑得很快,因为距离有点远,看不清,但是可以肯定那是一只熊。他这辈子只在电视和动物园里看到过熊,所以熊出没在城市的中心让他感觉惊恐不安。幸亏他是在车里,也幸亏路上行人不多,要不可以想见这只熊会对城市造成多大的恐慌。他怀疑这只熊是从动物园里跑出来的,他刚跟动物园打过电话,但没人接。所以他才打到这边。他希望警察赶快把那只熊抓起来,要是晚一点,只怕会出大事。
你确定那是一只熊?小马问。
我当然确定,那人说,不过……看起来是有一点点怪。
怎么怪?
叫声有点怪,那人沉默了片刻说。
它是怎么叫的?小马有点好奇。
怎么叫的?那人似乎不知该如何回答,突然把话筒往空中一伸,大声说:你听,它还在叫——
小马立刻屏住了呼吸,等了半晌,终于听到“噢”一声的似熊非熊的叫声,叫声那么响亮,连话筒似乎都被震动得颤动了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