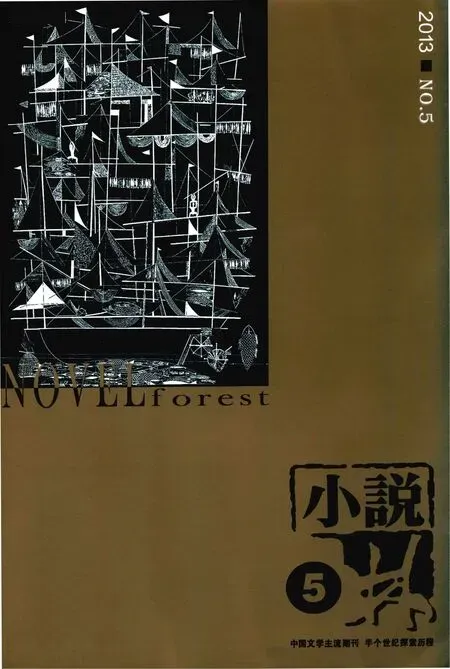从开始到最后
◎老 长
从当年的视角看起来,我爸已经不很年轻了,尽管比现在的我还要小上十多岁,仅仅三十出头。
那是我唯一一次见我爸说了那么多的话,讲自己小时候的经历。不是跟我,是跟一个年龄与他相仿的男人——阚叔。阚叔的长相现在已没了一丝印象,可以确定的是他跟我爸是非常好的朋友。后来,也就是在我家喝了一顿酒以后,他就走了,去了辽西一个叫三线的地方。此后,我爸就再也没有过那样的朋友。
当日应该是个礼拜天,因为我家的晚饭吃得比平时早很多。通常,都是全家人围在炕桌上吃饭。那天没有,炕桌上只有我爸和阚叔两个,我妈我姐还有我都守在外屋地热烘烘的灶台前。我弟弟那时还没出生,还在我妈的肚子里。灶台上的盘子里有难得一见的荤腥,是我妈从我爸他们的下酒菜里可怜巴巴拨出来的。对我和我姐来说,已经算作是赏赐了。尤其是我,——我姐比我大,乐不乐意也得让着我点儿。
正时至夏季,家里的屋门和窗户一律大敞四开的,不时有穿堂风越过窗根下几棵开花的姜不辣吹进里屋,再灌到外屋地来,掠过我们三人,沿外屋地的门飘散到当院里去。家里养的几只半大的鸡正一边咕咕地叫,一边画圈儿地在当院来回转,仿佛监狱里的犯人放风似的。我爸的话自是随着风一起来到外屋地的,不过,没有散出去,飘进我的耳朵里了。
一开始,我更关心的还是盘子里的荤腥,所以听得囫囵半片的,直到盘子清澈见底后,我才推开饭碗倚在里屋的门框上专注起来。那期间,我奶奶已经死了半天了,到了我爷爷带着我爸四处寻找他唯一的哥哥,也就是我大爷的当儿。
我爸说那个哥哥比他大好多,一天夜里偷偷跑了。起因是不务正业,不肯跟我爷爷学熟皮子手艺,只知道整天捧着家里的一把胡琴吱吱嘎嘎拉个没完,挨了我爷爷的一顿揍。
我大爷的出走令我爷爷又气又悔,就带上我爸去寻他。几天后,还真的在镇上寻到了他。当时,我爷爷正牵着我爸在镇子里四下转,就听见一串吱嘎吱嘎胡琴声,是从一家客栈的当院里传出来的。他们赶紧沿着琴声过去了……
我爷爷苦苦相劝,我大爷终于答应跟他一起回家。随后,他牵着我爸的手到街上买了些吃食回来。走到客栈门口时,我大爷把吃食递到我爸手上让他先进去,说自己去上趟便所。
我爷爷跟我爸一边吃,一边等我大爷。结果,始终没有等回他的人影。为此,我爸的脸上还挨了我爷爷狠狠的一巴掌。
这一回的逃离,我大爷没来得及带上他钟情的那把胡琴,再找的话可不那么容易了。况且,我爷爷已伤透了心,拉着我爸回了家,发誓说今后绝不再找他了。所以,我那个大爷后来始终下落不明。
我爸黑黑的面皮在酒液的涂抹下早已涨红起来,眼睛也一样,还浮动出晶莹的泪迹,不过没有哽咽,继续讲着说:后来不久,我爷爷就被日本人抓了劳工,押到矿上去挖煤。我爸年纪小没人照顾,只能带上他,我爷爷每天下井挖煤时,他就独自在工棚周围玩儿。
我爸没有描述工棚周围的样子。不过,可以想象一定被密实的铁丝网圈着,门口还设有岗楼,岗楼前始终立着日本兵,端着一支带刺刀的三八大盖,或许手里还牵着一条虎视眈眈的大狼狗。
年幼的我爸并不关心身为劳工的我爷爷,每天究竟是怎样一种境遇,也不觉得荷枪实弹的日本兵多可怕,说他们其中还有人给过他糖块吃。
听到这里时,我很是诧异。在我懵懂意识里,日本兵只是一个单一的概念,他们都是恶魔,杀人不眨眼的刽子手,怎么会对我爸如此友善呢?
当然,我现在完全可以理解日本兵的这种举动,还由此做了进一步的联想。我想象那个给我爸糖块吃的日本兵或许有一个跟我爸一般大小的儿子,或者是侄儿外甥什么的。他很喜欢他,看见我爸,心里便涌起一片温情。
我还陷在日本兵甜滋滋的糖块里的期间,我爸已然开始讲我爷爷带着他随一大帮劳工逃跑的事情了。说那天夜里,他正睡得迷迷瞪瞪的,就被我爷爷夹在胳肢窝里开跑了。先是和大家一起聚堆地跑,当身后投来探照灯光和响起噼噼啪啪的枪声时,劳工们才四散开来,下草棵的下草棵,钻树林的钻树林。我爷爷和我爸钻了树林。日本兵不肯放过他们,随枪声一起逼近了。情急之下,我爷爷就先将我爸举到一棵树上,自己紧跟着爬了上来。
我爷爷始终一只胳膊搂着树干,另一只胳膊紧紧护着我爸。他们在树上躲了几个小时,直到远近的枪声平息之后才爬下来继续逃。我爸说,我爷爷和他是那天为数不多的幸免遇难的人,其他人多半被乱枪打死和抓了回去。
也不知道我爷爷是在逃命时受了惊吓,还是因为下井挖煤疲累过度,逃回家来就一病不起,没多久便死了。临死之前,他声音微弱地喊我爸过去,应该是有话对他说。可我爸只惦记到外头去玩儿,没理会,说等他玩儿够了回来时,我爷爷已经凉了。
我爸是这时候才开始哽咽的,揉着眼睛说他那年才七岁,就成了一个没爹没娘的孩子,后来被邻村的舅舅收养了。我爸先说舅舅一家人待他不好,随后又有改口说其实人家也没怎么虐待他。舅舅自己本来就养了一大窝孩子,再添个他,无疑又多了负担。
我爸和阚叔一直喝到窗外折射着橙红色晚霞的时候才算结束。下地时,两人都有点儿离了歪斜的,先在屋里握了一通手,半天不撒开。
大哥你不用送我!出了当院的门,阚叔朝回推我爸,没推动,因为我爸也在推他,说啥也要执意送他一程。
我家住的那趟平房是南北向的,那趟房子东侧的把头儿和上一趟房子之间夹着一条土道,那条道向北端伸展没多远就转向西边,沿着一个斜坡滑落下去。从我家的门前看不见那条坡路,只能依稀看见远处的一些楼房,浸泡在傍晚红彤彤的霞光里。我爸沿那条路去送阚叔,不多时,两个侧侧歪歪的身影便被晚霞淹没了。
当然,在两人下地之前,我爸的过去在我这就结束了。或许接下来,他还会在送阚叔的路上继续讲,讲他寄人篱下的日子是如何熬过来的,以及后来又是怎么从那个叫哈达河的地方来到哈尔滨的。不过,无论如何也飘不进我的耳朵里了。
从朦胧地认识我爸的时候开始,我就没觉得他年轻,我妈也一样。这绝不是他们面相比较老的缘故,其他的孩子看父母也都是这样。在我们的眼里,父母们的起始基本人届中年,之后便在我们日益的成长中开始一天天变老……
转年,我家就搬到跃进街的一栋楼里。跃进街距我爸他们厂子和市区都更近一些,周围坐落了许多当时名声显赫的大企业。
搬家那天,我家全部家当装在一辆马车上,由一棕一白两匹马拉着。它们身形十分高大,屁股上分别烙有一串阿拉伯数字,据说曾是部队里的战马,到了和平年代,无需再到战场上冲锋陷阵了,就转业到了地方。那时,地方企业里多半都有马车,应该是汽车不够用,只能由马车补充。
我家的家当不多,一张一头沉的桌子和两个松木箱子以及一台缝纫机算是大件了,剩下的便是锅碗瓢盆一类的零碎,被一根长长的麻绳子结实地捆着。除了家当,车上还坐着我妈,怀里抱着包裹得严严实实的我弟弟。我也很想坐马车,可车上已没了空地儿,只好和我姐跟着马车走。
跃进街那栋楼的屋子并不比原来住的那间平房大,还是两家合厨。不过优势倒显而易见,可以享用上下水和暖气,拉屎撒尿也不用去外面臭烘烘的茅楼。
合厨的两家人彼此都称对方为对面屋。和我家住对面屋那家男的姓卢,比我爸小几岁,可我爸一直习惯叫他老卢,两口子都是转业军人。老卢是厂俱乐部主任,他老婆是厂卫生科化验室的。因为是双职工家庭,孩子也没有我家多,生活状况比我家要好一些。以至于刚刚搬过来的一段期间,我们全家人始终有一种低人一等的感觉。我妈更是如此,最初下厨房做饭总要和人家错开时间,目的是不愿看到自家案板和灶台间明显的落差。
也就是搬到跃进街的那年,我上了学。按理,原本可以到楼后百米开外的那所学校,因为它曾是我爸他们厂的子弟校。没成想就在之前一年,厂子竟发生了变故,由一家分为两家,子弟校还划给了那一家。虽分了家,最初两边职工的子弟还是照收不误。但我爸他们这边觉得毕竟不是长久之计,就在距离跃进街近两公里的厂大门对面重新建了一所,是一趟像我家先前住的那种平房。这样,我就成了那个学校的第一批学生。
学校刚建立的时候,设施十分简陋,桌椅和板凳只是钉在木箱子上带毛刺的一块块六零板子。那些木箱子在别处根本见不到,它们原本是用来装炮弹的。因为,我爸他们厂子是一家归属国家兵器工业部,专门生产炮弹的兵工厂。这是一个秘密,只有厂子内部人知道。
那期间的我爸已经不用下车间干活了。不是做了领导,而是被安排看厂子的大门。看大门是大家的说法,我爸自己不这么说。有生人问起他的工作时,他一向回答说在厂警卫排。
既是一家兵工厂,当然不允许外人擅自进入了。我爸的工作就是看好厂大门,要想进去,必须亮出本厂的工作证才行。
我爸的秉性有点儿闷,好听点儿说叫不爱说话,难听点儿就是一杠子压不出个屁来的那种人。这性格应该是与生俱来的,也可能是小时候的经历使然。不爱说话,便不善与人沟通和交往,也就没人跟他走得很近,除了当年的那个阚叔,而他已然远在天边了。
看大门的活儿相对下车间毕竟不是太累,对喜欢享受轻快的人来说也是求之不得的。想想我爸,既然不善与人沟通,是怎么得到这个好差事的呐?
后来,我发现另外几个看大门的人都和我爸的秉性差不多,隐约明白了,恰恰是他们的性格,让他们打心里将更多人拒于千里之外。这似乎更容易做到铁面无私。确实有人在这方面给予过我爸相关的评价,说他很死性,看大门时只认证不认人。
可令我不解的是,我爸自己是这样的性格,却不希望我也像他一样。其实,我根本没有他那么闷,比他爱说多了,只是要看什么场合和在什么人的跟前。比如我在跟玩伴讲看过的电影或者小儿书的时候是挺能白话的,甚至有时还不识时务地跟一些大人讲。对象从不会是我爸和我妈,他们根本不给我面子,会满眼不屑地说我就白话没用的的时候有能耐。他们说的没错,我确实到了公共场合就变得蔫巴下来了,上学以后尤为明显,一被老师提问,就满脸通红吭哧瘪肚的。老师跟我爸说这孩子有点儿苶。我爸回家后就骂我,说,妈了个屄地竟让人说你苶。知道啥叫苶吗?就是傻的意思!
我不可能傻,只是相对内向罢了。我爸应该懂得,这和他的遗传基因是有关系的,哪能怨我呐。不过,被骂以后,我倒是暗自发誓说今后一定不能再让人说我像傻子,并就此强迫自己朝着和内心相悖的方向行事,课堂上经常举手发言,还主动报名参加了校文艺宣传队,渐渐地成了一个看上去不那么苶的人。
我得承认,我爸身为男人还是非常能干的,家里所有体力方面的活儿,一概由他自己承担,比如挖菜窖。那时各家各户都得有菜窖,主要用来储存越冬的白菜和土豆。我爸是在楼东侧其他人家菜窖的空隙间选的一块地方,他先朝手里啐两口唾沫,接着便抄起从厂子里借来筒锹吭吭挖起来。其间被对面屋老卢经过时看见了,寻到跟前来问用他帮忙吗。我爸知道老卢只是客气地做一番姿态罢了,一连说了好几个不用。老卢赶紧就坡下驴地走掉了。
最一开始,我爸完全能应付得了。就是挖了一人多深,他也能一锹一锹地把土扬上来。可到了两米左右时就不行了,得有人帮着用绳子拴着土篮子把土一篮篮地拽上来,我爸就令我和我姐干这事儿。我和我姐加一块也没有多大劲儿,连半篮子土拽起来都吭哧吭哧的满脑袋流汗。有时候刚一拽上来就泄了力气,只能把土朝就近的地方倒,结果一多半又哗啦啦地滑落了下去。气得我爸在底下直骂,说养你们有他妈了屄用。
老卢家挖菜窖时就不用这么费劲,动手前已找好了帮手,中间阶段也有人主动过来帮忙。人缘好是一方面,主要的还是那些人愿意巴结他,希望俱乐部有新电影的时候从他那儿得到一些施舍。
我当然很羡慕老卢家在这方面的优势,可我更羡慕其他一些人家。那些人家干这等事情从不用大人动手,孩子就行了。那些孩子都比我大,有的是同胞兄弟,有的不是,完全是出于哥们儿情意拔刀相助来了。他们总是干得热火朝天,其乐融融的。我那时就想,自己将来也要交一些这样的朋友。
我爸虽然不善于与外人交往,却很会经营自己家的日子。看厂大门的工作是两班倒,就是说两天里有一天是歇着的。歇着的时间,我爸很少会用来睡觉。当班儿总是两个人,晚上是可以轮流睡觉。不睡觉干什么呐?厂子里地方大,除了稀落分布的厂房外,剩下的基本都是大片的树林及荒地,我爸就选择了一处开垦出来。他开垦的那片地位于靶场旁边。靶场是用来打炮的地方,不是朝空地上打,而是朝一个混凝土筑成的拱形洞穴里,目的是要检验生产出来的炮弹是否合格。我爸就在叮叮咣咣的爆炸声里春种秋收,果实是茄子、豆角、白菜、土豆一类的菜。我家当时吃菜基本不用花钱买。
我家是由我爸撑起来的,这便奠定了他在家里举足轻重的地位。所有人,包括我妈在内,都敬着他,怕着他,更让着他。他自己更是将当年苦难经历作为资本,心安理得地享用着全家人的尊敬。
我妈是经人介绍嫁给我爸的。她是呼兰人,算是那个历尽坎坷和生命短暂的女作家萧红的同乡。她没有像萧红那样与命运相抗衡的精神,不过也没有那么多凄苦的遭遇。她是俗人,嫁给一个俗人,也认同自己过的这种平淡而又平静的生活。
我出生的时候,那场所谓的自然灾害已经过去了。不过人们的日子还是过得很清苦,除了过年,平常基本享用不到什么好油水。我爸胃不好,一吃硬食就闹肚子,以至于粮店每月供应的细粮基本归了他。不光是细粮,能与细致贴上边儿的其他吃食也多半是属于他的。后来,也就是人们的日子过得好一些的时候,他的盘子里更多的都是鱼,各种鱼。虽不是什么上等货色,但还是让我暗自垂涎而又装出一副视而不见的样子。起初,我爸多少也会觉得过意不去,说你们也尝一口吧。却没人敢伸筷子。大家都清楚如果谁真的尝了,无疑是在侵占不属于自己的东西。一旦我爸由于鱼不够吃而叨了一口我们的粗劣的菜,并因此导致了他的跑肚拉稀,那我们可就罪该万死了。
再后来,我长大了。我爸也已变成我现在的年纪,鬓发间可以寻见了几分秋天的颜色。成长让我获得了不少知识,同时也让我对凡庸心生厌恶之情。于是,对我爸再不像以前那么敬着怕着了,开始蔑视起他来,觉得他是个怯懦而又自私的人。正是因为他的怯懦和自私,让人都疏远了他,连一个朋友都没有。
我家又一次搬家了。先前那次是朝市区靠近,这一次则是向远处偏离。因为,厂子新落成的一大片家属楼位于南端的近郊。虽然相对远了一些,房子的尺寸却增大了不少,两屋一厨,还是独门独户的。对我家来说,应该算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一次迁徙。
本来,我爸在厂运输队排到的是第二天的班儿,当天要做的只是把一些零碎的家当统统打包。谁知后来有一辆车因为前一家人搬得比较迅速,提前大功告成了,司机就问我爸是否当天要搬。按理,我爸应该不用那么急,打包的事情才只进行到一半。可他看有机可乘,当即便对司机点了头。结果,搞得全家人措手不及,乱了阵脚。最终,还是由我出马收拾了残局。当时,正有我的几个哥们儿给另一家帮完忙,刚一身臭汗地坐下来准备享用一顿好酒好菜的时候,就被我寻上门来薅出来。他们心里虽有些不愿意,却也不好说什么。等到搬完了家,已经傍晚时分了,我妈也没腾出机会做好吃食,按理应该找个饭店对人家给予答谢。我爸没那么做,只是买回一瓶劣质白酒和几样熟食和罐头应付他们。这我也没办法,尽管算是长大了,但还没就业,兜里根本没有银两,只能带着对几个哥们儿的歉疚之情将自己灌了个酩酊大醉。迷蒙之中,我爸叨咕着骂我,把我骂恼了,冲他立起了眼睛,含混地嚷嚷着说,你还骂我,要不是我,就是哭,你的家今天也搬不完!
我当时是因为喝醉了,才说出这样的话来。可那却不是醉话,而是宣泄出了内心里对我爸的蔑视。
应该是被我伤及到了痛处,我爸哑口无言了,好半天才骂了我一句滚你妈了个屄的。虽透着气急败坏,却没有多少底气……
我爸自然不可能因为我酒后一句对他的批判发生任何的改变,反而随着头上秋天的颜色日渐加重变得更加闷了。他现今还跟我妈住在那套房子里,只他们两个。每天,他除了吃饭睡觉之外,剩下的就是像一只羸弱而又孤独的猫一样楼前楼后来回游荡。见人也不吱声,最多只是龇着残缺的牙跟人笑笑。
我妈呐,作为我爸此生这出戏里一个配角,当然也跟我爸一起老了。她从不随我爸一起出来,喜欢待在家里绣十字绣,已经绣了好多的牡丹和红鲤鱼,统统镶在木框里挂在墙上。几十年来,任何时兴事情我妈都没落下过。早年,兴刺绣时,我家就四下鲜花绽放。随后,又兴过钩针,我家便又到处银装素裹。再后来,还兴过只有本厂家属中独有的一种事情,将装炮弹的塑料桶改装成花瓶。那种塑料桶有大有小,有粗有细,是根据炮弹的型号而定的。最初,人们只是把它偷偷带回家做储藏罐。小孩儿们则更喜欢用其演绎自己心目中的大炮。将盖子扣紧,然后放在地上用脚猛踩。脚落在塑料桶上的一瞬,随着一声砰然的巨响,盖子就狠狠地被射了出去。
后来,也不知是谁,应该是女人吧,灵机一动地生出用它做花瓶的念头。用塑料桶做花瓶的方法有两种,一种是剪子活儿,和许多年后人们用易拉罐儿做烟灰缸的方式很接近;另一种做法则更像加工玻璃花瓶的工艺,得先将塑料桶用火烤,烤软后对着桶口使劲吹,吹起一个圆圆的肚子来。接着,将桶口剪成花瓣儿形状,还得经火烤,烤完了再用手捏出花瓣儿的凸凹。就这样,由于只是一时时兴,这种东西现在已经见不到了,就像我爸他们厂子永远没了形影一样,早已改头换面地盖起了一片新派的商品住宅楼。
现在的我妈时而也会出门,多半都是礼拜天的时候,徒步去几公里之外的一个天主教堂。多年前,她就成为了主的一个信徒。我始终不清楚她是真的想要那个西方的主解救什么,还是又在赶时兴。
如果将视点拉回从前的某个角度,现在的我理当也已老了。到了这个时候,我开始像当年审视我爸一样审视起我自己,从开始到最后地审视。当然,我的最后还没有到。不过,却从我爸形影间依稀地寻到了一些迹象。我不再像从前那样有意甚至强行纠正自己,竭力朝着与原本秉性相反的方向努力,而是开始适应顺从。除了工作不得不应付,再不愿于芸芸众生中抛头露面,即便露面,也一概是能保持缄默就不轻易开口。我还在日复一日的生活里看不出任何新意,渐渐的心灰意冷起来。以前的一些朋友相继疏远了,觉得彼此间的往来也无非一种重复,何况时而还会感觉到一些看似亲密无间的友情背后,晃动的令人眼花缭乱的利益呐。当然,没有利益关系的朋友也有几个,只是到一起时已不再像从前那般其乐融融。既然如此,不见也罢了。
——我原本不想沿我爸的路径走,一直引以为戒。现在看来一切努力都是白费,最终还是走到他颤巍巍的阴影里了……
眼下又是一个傍晚,霞光不像当年,也就是我爸送阚叔的那天那么完整,被割成了一些碎片,掩映在高低错落的楼群的夹缝间。尽管如此,我却还是见景生情地想起了那天的景象,并渐渐将那些霞光的碎片拼凑起来,还原成那天的样子。于是,就又看见了我爸和阚叔的身影,正栽栽歪歪地迎着那片霞光而去。
接下来,我又一次和我爸一起沿着他的人生轨迹平行地走起来,时而井然有序;时而枝蔓纵横。不过,走来走去,那片晚霞一直没有散去,始终笼罩在头顶上……
其实,那天当我爸执意要去送阚叔时,我妈说我爸有点儿喝多了,让我跟他一起去看着点儿。
我爸说自己没事儿,用不着我,我就没敢动,守在门口和我妈一起目送他们。等到两人的身影淹没在霞光中的时候,我妈再次不放心地对我说,不行,你还是跟着点儿他吧!我就放开两腿追了过去。我没有追到我爸和阚叔的近前,怕他朝回撵我,始终保持一定距离地尾随在后边……